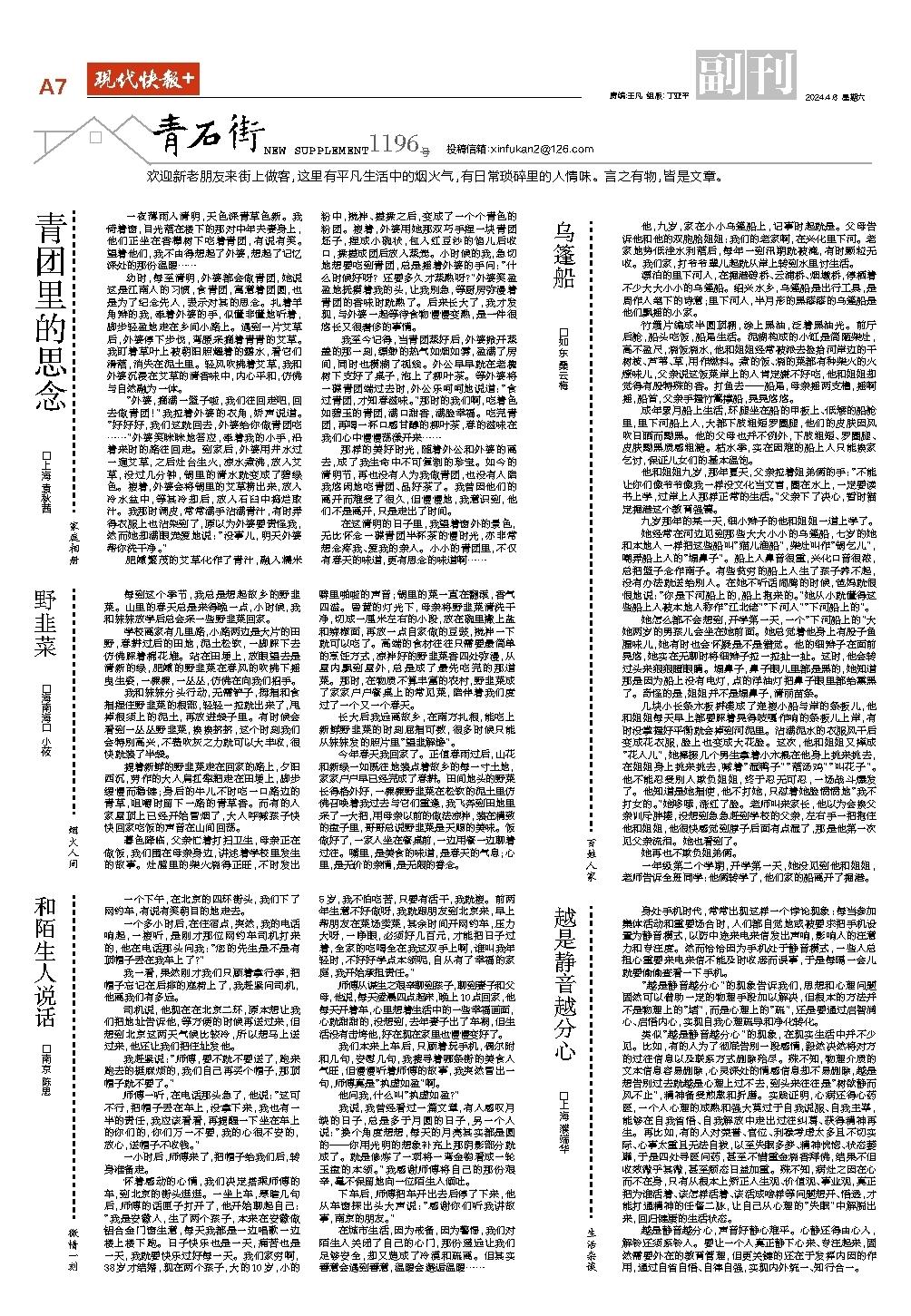□如东 桑云梅
他,九岁,家在小小乌篷船上,记事时起就是。父母告诉他和他的双胞胎姐姐:我们的老家啊,在兴化里下河。老家地势低洼水利落后,每年一到汛期就被淹,有时颗粒无收。我们家,打爷爷辈儿起就从岸上转到水里讨生活。
漂泊的里下河人,在掘港砖桥、云浦桥、烟墩桥,停栖着不少大大小小的乌篷船。绍兴水乡,乌篷船是出行工具,是周作人笔下的诗意;里下河人,半月形的黑漆漆的乌篷船是他们飘摇的小家。
竹篾片编成半圆顶棚,涂上黑油,泛着黑油光。前厅后舱,船头吃饭,船尾生活。泥糊构成的小缸是简陋柴灶,高不盈尺,烧饭烧水,他和姐姐经常被派去捡拾河岸边的干树枝、芦苇、草,用作燃料。煮的饭、烧的菜都有种柴火的火燎味儿,父亲说这饭菜岸上的人肯定嫌不好吃,他和姐姐却觉得有股特殊的香。打鱼去——船尾,母亲摇两支橹,摇啊摇,船首,父亲手握竹篙撑船,晃晃悠悠。
成年累月船上生活,环腿坐在船的甲板上、低矮的船舱里,里下河船上人,大都下肢粗短罗圈腿,他们的皮肤因风吹日晒而黝黑。他的父母也并不例外,下肢粗短、罗圈腿、皮肤黝黑质感粗糙。枯水季,实在困难的船上人只能挨家乞讨,保证儿女们的基本温饱。
他和姐姐九岁,那年夏天,父亲拉着姐弟俩的手:“不能让你们像爷爷像我一样没文化当文盲,圈在水上,一定要读书上学,过岸上人那样正常的生活。”父亲下了决心,暂时锚定掘港这个教育强镇。
九岁那年的某一天,细小辫子的他和姐姐一道上学了。
她经常在河边见到那些大大小小的乌篷船,七岁的她和本地人一样把这些船叫“猫儿渔船”,柴灶叫作“锅乞儿”,嘲弄船上人的“塌鼻子”。船上人鼻音很重,兴化口音很浓,总把篮子念作南子。有些贫穷的船上人生了孩子养不起,没有办法就送给别人。在她不听话闹腾的时候,爸妈就恨恨地说:“你是下河船上的,船上抱来的。”她从小就懂得这些船上人被本地人称作“江北佬”“下河人”“下河船上的”。
她怎么都不会想到,开学第一天,一个“下河船上的”大她两岁的男孩儿会坐在她前面。她总觉着他身上有股子鱼腥味儿,她有时也会怀疑是不是错觉。他的细辫子在面前晃悠,她实在无聊时将细辫子拉一拉扯一扯。这时,他会转过头来狠狠瞪眼睛。塌鼻子,鼻子眼儿里都是黑的,她知道那是因为船上没有电灯,点的洋油灯把鼻子眼里都给熏黑了。奇怪的是,姐姐并不是塌鼻子,清丽苗条。
几块小长条木板拼凑成了连接小船与岸的条板儿,他和姐姐每天早上都要踩着晃得吱嘎作响的条板儿上岸,有时没掌握好平衡就会掉到河泥里。沾满泥水的衣服风干后变成花衣服,脸上也变成大花脸。这次,他和姐姐又摔成“花人儿”,她撺掇几个男生拿着小木棍在他身上挑来挑去,在姐姐身上挑来挑去,喊着“湿鸭子”“落汤鸡”“叫花子”。他不能忍受别人欺负姐姐,终于忍无可忍,一场战斗爆发了。他知道是她指使,他不打她,只怼着她脸愤愤地“我不打女的。”她哆嗦,涨红了脸。老师叫来家长,他以为会挨父亲训斥胖揍,没想到急急赶到学校的父亲,左右手一把抱住他和姐姐,他很快感觉到脖子后面有点湿了,那是他第一次见父亲流泪。她也看到了。
她再也不欺负姐弟俩。
一年级第二个学期,开学第一天,她没见到他和姐姐,老师告诉全班同学:他俩转学了,他们家的船离开了掘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