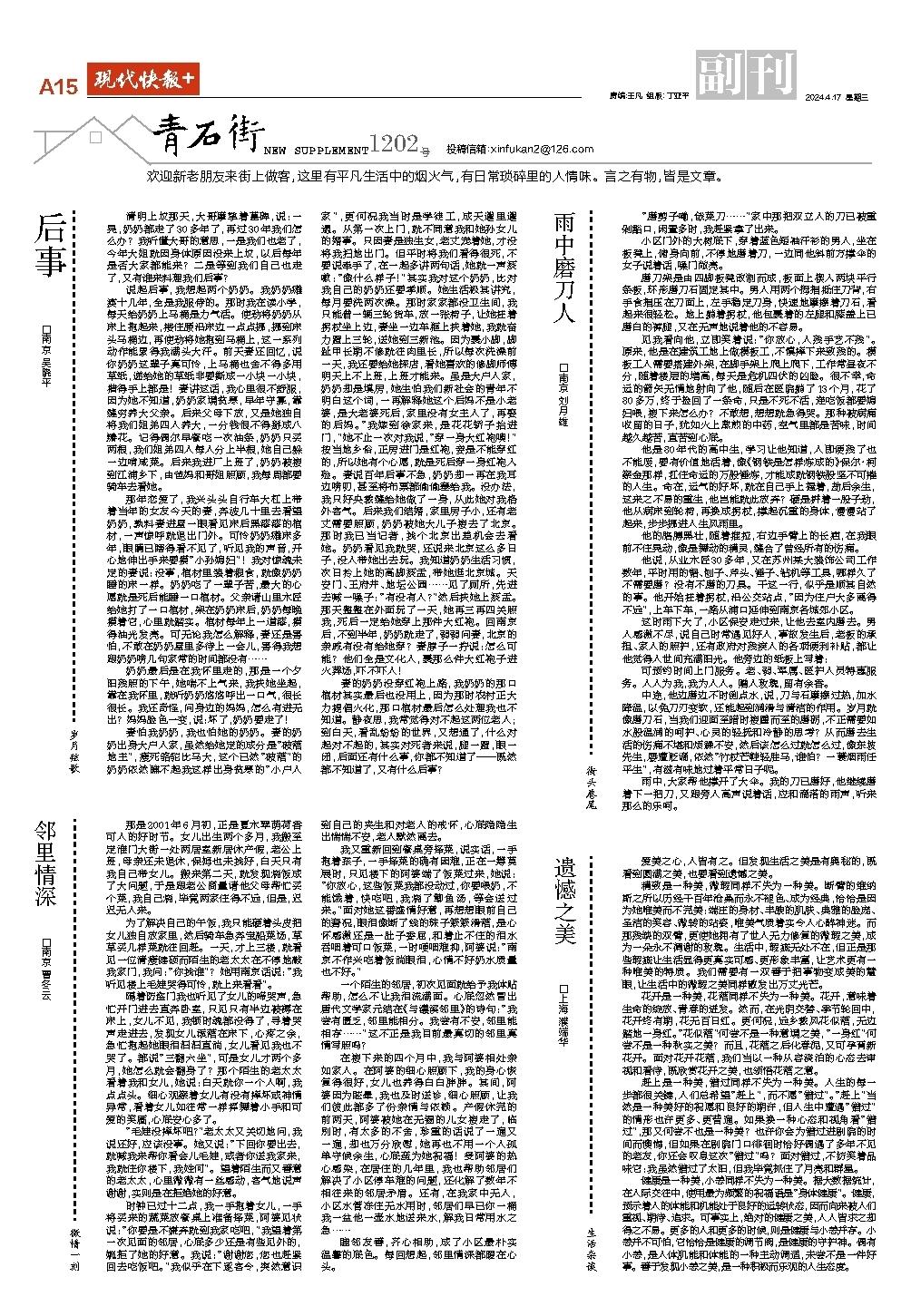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清明上坟那天,大哥摩挲着墓碑,说:一晃,奶奶都走了30多年了,再过30年我们怎么办?我听懂大哥的意思,一是我们也老了,今年大姐就因身体原因没来上坟,以后每年是否大家都能来?二是等到我们自己也走了,又有谁来料理我们后事?
说起后事,我想起两个奶奶。我奶奶瘫痪十几年,全是我服侍的。那时我在读小学,每天给奶奶上马桶是力气活。使劲将奶奶从床上抱起来,搂住腰沿床边一点点挪,挪到床头马桶边,再使劲将她抱到马桶上,这一系列动作能累得我满头大汗。前天妻还回忆,说你奶奶这辈子真可怜,上马桶也舍不得多用草纸,递给她的草纸非要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揩得手上都是!妻讲这话,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她不知道,奶奶家境贫寒,早年守寡,靠缝穷养大父亲。后来父母下放,又是她独自将我们姐弟四人养大,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记得偶尔早餐吃一次油条,奶奶只买两根,我们姐弟四人每人分上半根,她自己躲一边啃咸菜。后来我进厂上班了,奶奶被接到江浦乡下,由爸妈和哥姐照顾,我每周都要骑车去看她。
那年恋爱了,我兴头头自行车大杠上带着当年的女友今天的妻,奔波几十里去看望奶奶,孰料妻进屋一眼看见床后黑漆漆的棺材,一声惊呼就退出门外。可怜奶奶瘫床多年,眼睛已瞎得看不见了,听见我的声音,开心地伸出手来要摸“小孙媳妇”!我对惊魂未定的妻说:没事,棺材里装着粮食,就像奶奶睡的床一样。奶奶吃了一辈子苦,最大的心愿就是死后能睡一口棺材。父亲请山里木匠给她打了一口棺材,架在奶奶床后,奶奶每晚摸着它,心里就踏实。棺材每年上一道漆,摸得油光发亮。可无论我怎么解释,妻还是害怕,不敢在奶奶屋里多待上一会儿,害得我想跟奶奶唠几句家常的时间都没有……
奶奶最后是在我怀里走的,那是一个夕阳残照的下午,她喘不上气来,我扶她坐起,靠在我怀里,就听奶奶悠悠呼出一口气,很长很长。我还奇怪,问身边的妈妈,怎么有进无出?妈妈脸色一变,说:坏了,奶奶要走了!
妻怕我奶奶,我也怕她的奶奶。妻的奶奶出身大户人家,虽然给她定的成分是“破落地主”,瘦死骆驼比马大,这个已然“破落”的奶奶依然瞧不起我这样出身贫寒的“小户人家”,更何况我当时是学徒工,成天邋里邋遢。从第一次上门,就不同意我和她孙女儿的婚事。只因妻是独生女,老丈宠着她,才没将我扫地出门。但平时将我们看得很死,不要说牵手了,在一起多讲两句话,她就一声痰嗽:“像什么样子!”其实我对这个奶奶,比对我自己的奶奶还要孝顺。她生活极其讲究,每月要洗两次澡。那时家家都没卫生间,我只能借一辆三轮货车,放一张椅子,让她拄着拐杖坐上边,妻坐一边车框上扶着她,我就奋力蹬上三轮,送她到三新池。因为裹小脚,脚趾甲长期不修就往肉里长,所以每次洗澡前一天,我还要给她探店,看她喜欢的修脚师傅明天上不上班,上班才能来。虽是大户人家,奶奶却是填房,她生怕我们新社会的青年不明白这个词,一再解释她这个后妈不是小老婆,是大老婆死后,家里没有女主人了,再娶的后妈。“我嫁到徐家来,是花花轿子抬进门,”她不止一次对我说,“穿一身大红袍噢!”按当地乡俗,正房进门是红袍,妾是不能穿红的,所以她有个心愿,就是死后穿一身红袍入殓。妻说百年后事不急,奶奶却一再在我耳边唠叨,甚至将布票都偷偷塞给我。没办法,我只好央裁缝给她做了一身,从此她对我格外客气。后来我们结婚,家里房子小,还有老丈需要照顾,奶奶被她大儿子接去了北京。那时我已当记者,找个北京出差机会去看她。奶奶看见我就哭,还说来北京这么多日子,没人带她出去玩。我知道奶奶生活习惯,次日拎上她的高脚痰盂,带她逛北京城。天安门、王府井、地坛公园……见了厕所,先进去喊一嗓子:“有没有人?”然后扶她上痰盂。那天整整在外面玩了一天,她再三再四关照我,死后一定给她穿上那件大红袍。回南京后,不到半年,奶奶就走了,弱弱问妻,北京的亲戚有没有给她穿?妻脖子一拧说:怎么可能?他们全是文化人,裹那么件大红袍子进火葬场,吓不吓人!
妻的奶奶没穿红袍上路,我奶奶的那口棺材其实最后也没用上,因为那时农村正大力提倡火化,那口棺材最后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静夜思,我常觉得对不起这两位老人;到白天,看乱纷纷的世界,又想通了,什么对起对不起的,其实对死者来说,腿一蹬,眼一闭,后面还有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了——既然都不知道了,又有什么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