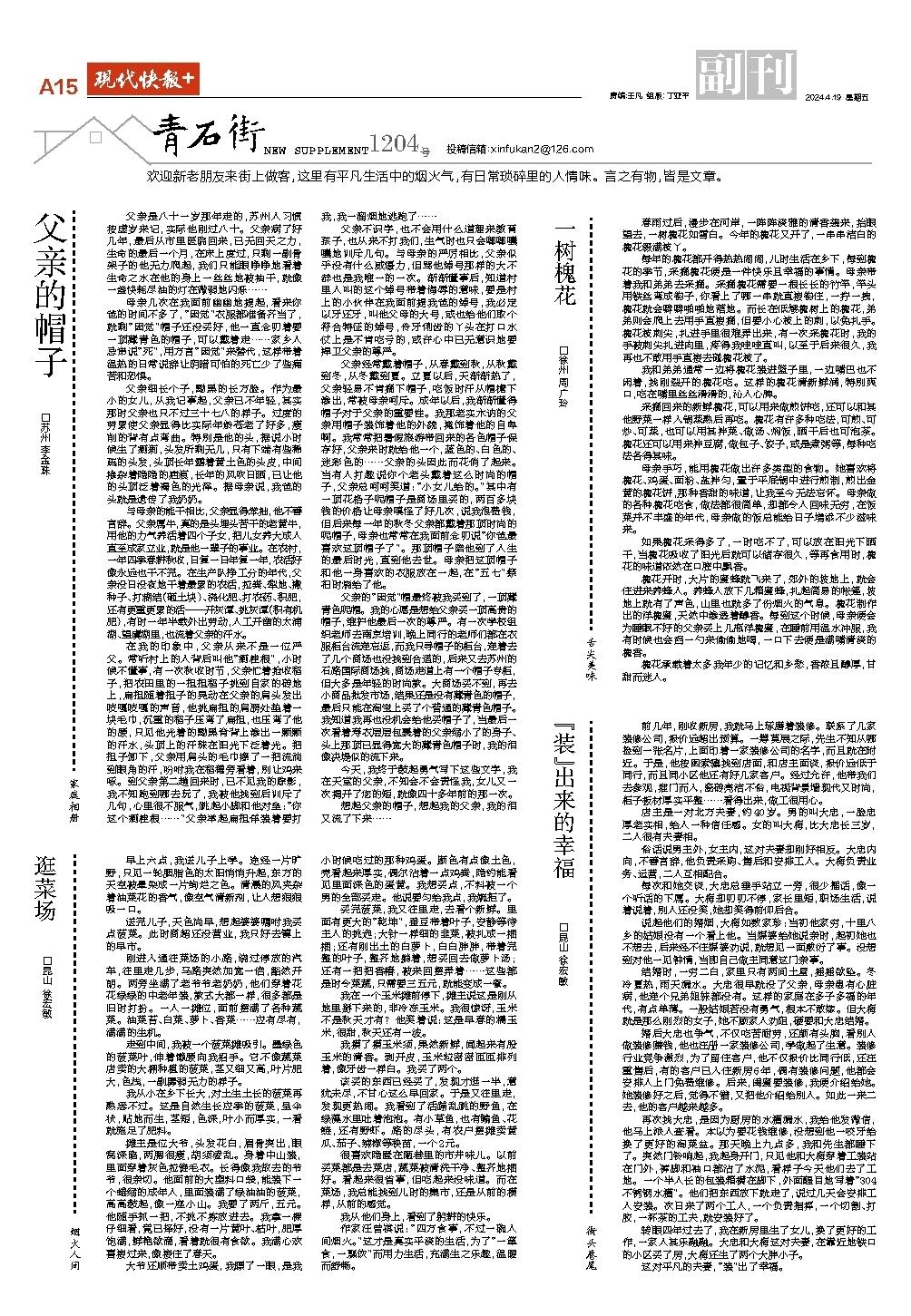□苏州 李金珠
父亲是八十一岁那年走的,苏州人习惯按虚岁来记,实际他刚过八十。父亲病了好几年,最后从市里医院回来,已无回天之力,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在床上度过,只剩一副骨架子的他无力爬起,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命之水在他的身上一丝丝地被抽干,就像一盏快耗尽油的灯在微弱地闪烁……
母亲几次在我面前幽幽地提起,看来你爸的时间不多了,“困觉”衣服都准备齐当了,就剩“困觉”帽子还没买好,他一直念叨着要一顶藏青色的帽子,可以戴着走……家乡人忌讳说“死”,用方言“困觉”来替代,这样带着温热的日常说辞让阴暗可怕的死亡少了些痛苦和恐惧。
父亲细长个子,黝黑的长方脸。作为最小的女儿,从我记事起,父亲已不年轻,其实那时父亲也只不过三十七八的样子。过度的劳累使父亲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好多,瘦削的背有点弯曲。特别是他的头,据说小时候生了瘌痢,头发所剩无几,只有下端有些稀疏的头发,头顶长年露着黄土色的头皮,中间掺杂着隐隐的疤痕,长年的风吹日晒,已让他的头顶泛着褐色的光泽。据母亲说,我爸的头就是遗传了我奶奶。
与母亲的能干相比,父亲显得笨拙,他不善言辞。父亲属牛,真的是头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用他的力气养活着四个子女,把儿女养大成人直至成家立业,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在农村,一年四季春耕秋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活好像永远也干不完。在生产队挣工分的年代,父亲没日没夜地干着最累的农活,拉粪、犁地、撒种子、打糊结(砸土块)、浇化肥、打农药、积肥,还有更重更累的活——开灰潭、挑灰潭(积有机肥),有时一年半载外出劳动,人工开凿的太浦湖、望虞湖里,也流着父亲的汗水。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不是一位严父。常听村上的人背后叫他“瘌桂根”,小时候不懂事,有一次秋收时节,父亲忙着抢收稻子,把农田里的一担担稻子挑到自家的砖地上,扁担随着担子的晃动在父亲的肩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他挑扁担的肩膀处垫着一块毛巾,沉重的稻子压弯了扁担,也压弯了他的腰,只见他光着的黝黑脊背上渗出一颗颗的汗水,头顶上的汗珠在阳光下泛着光。把担子卸下,父亲用肩头的毛巾擦了一把流淌到眼角的汗,吩咐我在稻穗旁看着,别让鸡来啄。到父亲第二趟回来时,已不见我的踪影,我不知跑到哪去玩了,我被他找到后训斥了几句,心里很不服气,跳起小脚和他对垒:“你这个瘌桂根……”父亲举起扁担佯装着要打我,我一溜烟地逃跑了……
父亲不识字,也不会用什么道理来教育孩子,也从来不打我们,生气时也只会嘟嘟囔囔地训斥几句。与母亲的严厉相比,父亲似乎没有什么威慑力,但骂他绰号那样的大不恭也是我唯一的一次。渐渐懂事后,知道村里人叫的这个绰号带着侮辱的意味,要是村上的小伙伴在我面前提我爸的绰号,我必定以牙还牙,叫他父母的大号,或也给他们取个符合特征的绰号,伶牙俐齿的丫头在打口水仗上是不肯吃亏的,或许心中已无意识地要捍卫父亲的尊严。
父亲经常戴着帽子,从春戴到秋,从秋戴到冬,从冬戴到夏。立夏以后,天渐渐热了,父亲轻易不肯摘下帽子,吃饭时汗从帽檐下渗出,常被母亲呵斥。成年以后,我渐渐懂得帽子对于父亲的重要性。我那老实木讷的父亲用帽子装饰着他的外貌,掩饰着他的自卑啊。我常常把暑假旅游带回来的各色帽子保存好,父亲来时就给他一个,蓝色的、白色的、迷彩色的……父亲的头因此而花俏了起来。当有人打趣说你个老头戴着这么时尚的帽子,父亲总呵呵笑道:“小女儿给的。”其中有一顶花格子呢帽子是商场里买的,两百多块钱的价格让母亲嗔怪了好几次,说我浪费钱,但后来每一年的秋冬父亲都戴着那顶时尚的呢帽子,母亲也常常在我面前念叨说“你爸最喜欢这顶帽子了”。那顶帽子陪他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光,直到他去世。母亲把这顶帽子和他一身喜欢的衣服放在一起,在“五七”祭祀时烧给了他。
父亲的“困觉”帽最终被我买到了,一顶藏青色呢帽。我的心愿是想给父亲买一顶高贵的帽子,维护他最后一次的尊严。有一次学校组织老师去南京培训,晚上同行的老师们都在衣服柜台流连忘返,而我只寻帽子的柜台,连着去了几个商场也没找到合适的,后来又去苏州的石路国际商场找,商场走道上有一个帽子专柜,但大多是年轻的时尚款。大商场买不到,再去小商品批发市场,结果还是没有藏青色的帽子,最后只能在淘宝上买了个普通的藏青色帽子。我知道我再也没机会给他买帽子了,当最后一次看着寿衣层层包裹着的父亲缩小了的身子、头上那顶已显得宽大的藏青色帽子时,我的泪像决堤似的流下来。
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下这些文字,我在天堂的父亲,不知会不会责怪我,女儿又一次揭开了您的短,就像四十多年前的那一次。
想起父亲的帽子,想起我的父亲,我的泪又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