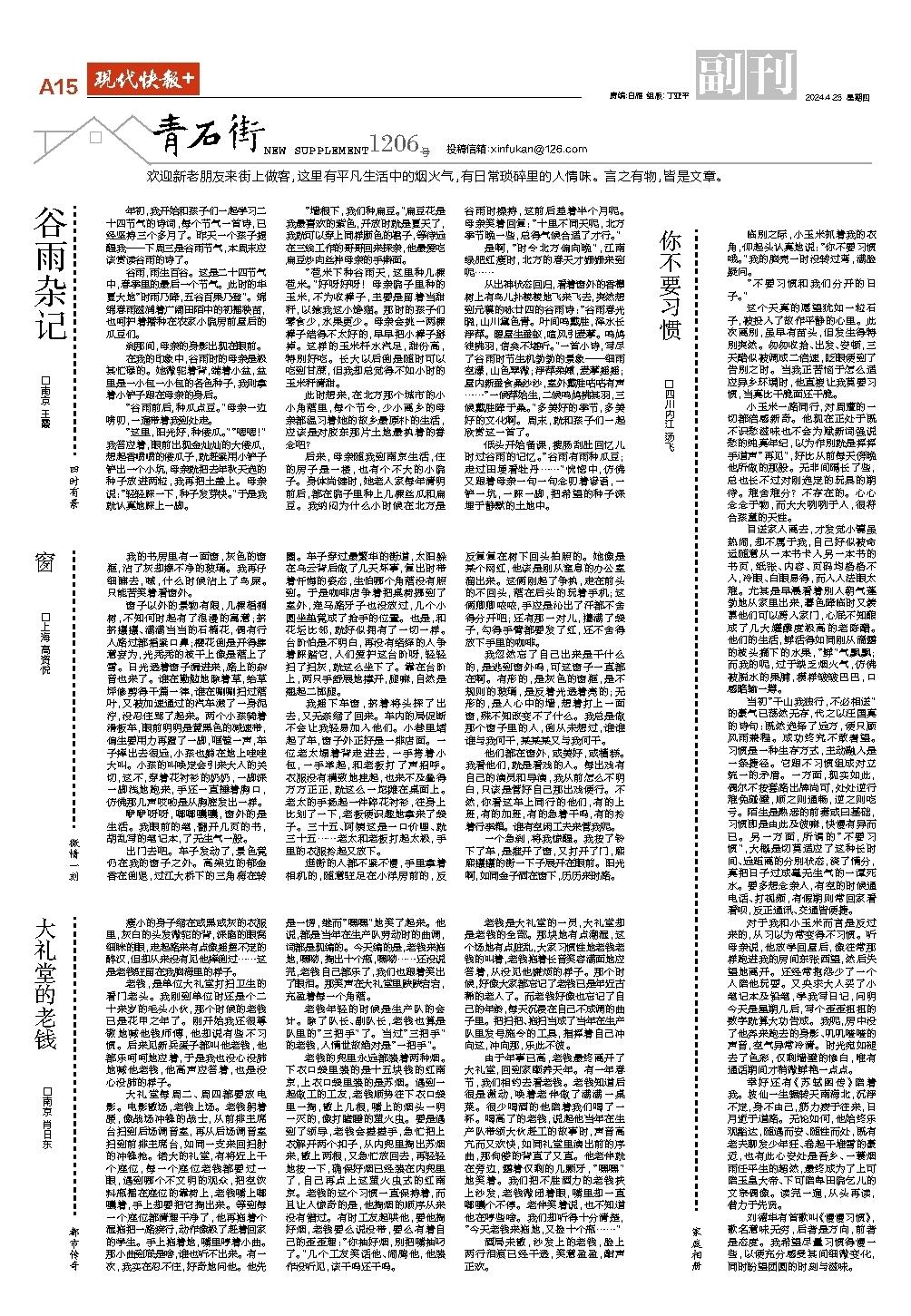□上海 高资悦
我的书房里有一面窗,灰色的窗框,沾了灰却擦不净的玻璃。我再仔细瞧去,嘁,什么时候沾上了鸟屎。只能苦笑着看窗外。
窗子以外的景物有限,几棵梧桐树,不知何时起有了浪漫的寓意;挤挤攘攘、满满当当的石楠花,偶有行人路过都捂紧口鼻;樱花倒是开得肆意妄为,光秃秃的枝干上像是落上了雪。日光透着窗子漏进来,路上的杂音也来了。谁在勤勉地除着草,给草坪修剪得千篇一律,谁在唰唰扫过落叶,又被加速通过的汽车溅了一身泥泞,没忍住骂了起来。两个小孩骑着滑板车,眼前明明是黄黑色的减速带,偏生要用力再蹬了一脚,哐镗一声,车子摔出去很远,小孩也躺在地上哇哇大叫。小孩的叫唤定会引来大人的关切,这不,穿着花衬衫的奶奶,一脚深一脚浅地跑来,手还一直捶着胸口,仿佛那几声哎哟是从胸腔发出一样。
咿咿呀呀,嘟嘟囔囔,窗外的是生活。我眼前的笔,翻开几页的书,胡乱写的笔记本,了无生气一般。
出门去吧。车子发动了,景色竟仍在我的窗子之外。高架边的郁金香在倒退,过江大桥下的三角梅在转圈。车子穿过最繁华的街道,太阳躲在乌云背后做了几天坏事,复出时带着忏悔的姿态,生怕哪个角落没有照到。于是咖啡店争着把桌椅挪到了室外,连马路牙子也没放过,几个小圆坐垫竟成了抢手的位置。也是,和花坛比邻,就好似拥有了一切一样。台阶怕是不明白,再没有络绎的人争着踩踏它,人们爱护这台阶呀,轻轻扫了扫灰,就这么坐下了。靠在台阶上,两只手舒展地撑开,腿嘛,自然是翘起二郎腿。
我摇下车窗,挤着将头探了出去,又无奈缩了回来。车内的局促断不会让我轻易加入他们。小巷里堵起了车,窗子外正好是一排店面。一位老太塌着背走进去,一手挎着小包,一手举起,和老板打了声招呼。衣服没有精致地挂起,也来不及叠得方方正正,就这么一坨摊在桌面上。老太的手扬起一件碎花衬衫,往身上比划了一下,老板便识趣地拿来了袋子。三十五、阿姨这是一口价哩、就三十五……老太和老板打起太极,手里的衣服拎起又放下。
逛街的人都不紧不慢,手里拿着相机的,随意驻足在小洋房前的,反反复复在树下回头拍照的。她像是某个网红,他该是刚从窒息的办公室溜出来。这俩刚起了争执,走在前头的不回头,落在后头的玩着手机;这俩卿卿哝哝,手应是沁出了汗都不舍得分开吧;还有那一对儿,攥满了袋子,勾得手臂都要发了红,还不舍得放下手里的咖啡。
我忽然忘了自己出来是干什么的,是逃到窗外吗,可这窗子一直都在啊。有形的,是灰色的窗框,是不规则的玻璃,是反着光透着亮的;无形的,是人心中的墙,想着打上一面窗,殊不知改变不了什么。我总是做那个窗子里的人,倒从未想过,谁谁谁与我何干,某某某又与我何干。
他们都在窗外,或美好,或糟糕。我看他们,就是看戏的人。每出戏有自己的演员和导演,我从前怎么不明白,只该是管好自己那出戏便行。不然,你看这车上同行的他们,有的上班,有的加班,有的急着干吗,有的拎着行李箱。谁有空闲工夫来管我呢。
一个急刹,将我惊醒。我按了铃下了车,是推开了窗,又打开了门,熙熙攘攘的街一下子展开在眼前。阳光啊,如同金子洒在窗下,历历来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