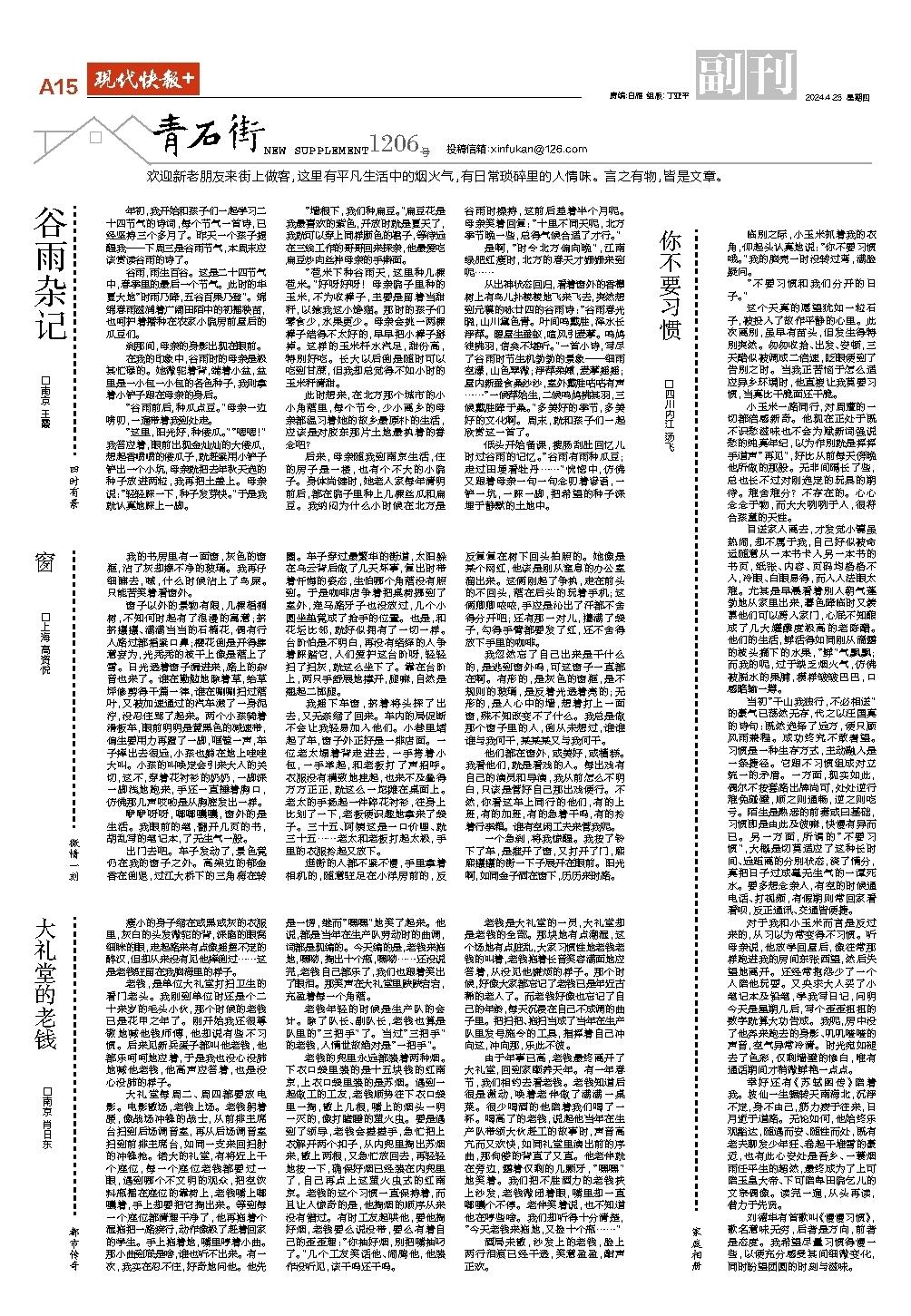□南京 肖日东
瘦小的身子缩在或黑或灰的衣服里,灰白的头发微驼的背,深陷的眼窝细眯的眼,走起路来有点像摇摆不定的醉汉,但却从来没有见他摔倒过……这是老钱驻留在我脑海里的样子。
老钱,是单位大礼堂打扫卫生的看门老头。我刚到单位时还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那个时候的老钱已是花甲之年了。刚开始我还很尊敬地喊他钱师傅,他却说有些不习惯。后来见新兵蛋子都叫他老钱,他都乐呵呵地应着,于是我也没心没肺地喊他老钱,他高声应答着,也是没心没肺的样子。
大礼堂每周二、周四都要放电影。电影散场,老钱上场。老钱躬着腰,像战场冲锋的战士,从前排主席台扫到后场调音室,再从后场调音室扫到前排主席台,如同一支来回扫射的冲锋枪。偌大的礼堂,有将近上千个座位,每一个座位老钱都要过一眼,遇到哪个不文明的观众,把空饮料瓶插在座位的靠椅上,老钱嘴上嘟囔着,手上却要把它掏出来。等到每一个座位都清理干净了,他再拖着个湿拖把一路疾行,动作像极了赶着回家的学生。手上拖着地,嘴里哼着小曲。那小曲到底是啥,谁也听不出来。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他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了起来。他说,都是当年在生产队劳动时的曲调,词都是现编的。今天编的是,老钱来拖地,嘿呦,掏出十个瓶,嘿呦……还没说完,老钱自己都乐了,我们也跟着笑出了眼泪。那笑声在大礼堂里跌跌宕宕,充盈着每一个角落。
老钱年轻的时候是生产队的会计。除了队长、副队长,老钱也算是队里的“三把手”了。当过“三把手”的老钱,人情世故绝对是“一把手”。
老钱的兜里永远都装着两种烟。下衣口袋里装的是十五块钱的红南京,上衣口袋里装的是苏烟。遇到一起做工的工友,老钱顺势往下衣口袋里一掏,散上几根,嘴上的烟头一明一灭的,像打瞌睡的萤火虫。要是遇到了领导,老钱会搓搓手,急忙把上衣解开两个扣子,从内兜里掏出苏烟来,散上两根,又急忙放回去,再轻轻地按一下,确保好烟已经装在内兜里了,自己再点上这萤火虫式的红南京。老钱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着,而且让人惊奇的是,他掏烟的顺序从来没有错过。有时工友起哄他,要他掏好烟,老钱要么说没带,要么有着自己的歪歪理:“你抽好烟,别把嘴抽叼了。”几个工友笑话他、闹腾他,他装作没听见,该干吗还干吗。
老钱是大礼堂的一员,大礼堂却是老钱的全部。那块地有点潮湿,这个场地有点脏乱,大家习惯性地老钱老钱的叫着,老钱拖着长音笑容满面地应答着,从没见他嫌烦的样子。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忘记了老钱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而老钱好像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每天沉浸在自己不成调的曲子里。把扫把、拖扫当成了当年在生产队里发号施令的工具,指挥着自己冲向这,冲向那,乐此不彼。
由于年事已高,老钱最终离开了大礼堂,回到家颐养天年。有一年春节,我们相约去看老钱。老钱知道后很是激动,唤着老伴做了满满一桌菜。很少喝酒的他陪着我们喝了一杯。喝高了的老钱,说起他当年在生产队带领大伙赶工的故事时,声音高亢而又欢快,如同礼堂里演出前的序曲,那佝偻的背直了又直。他老伴就在旁边,露着仅剩的几颗牙,“嘿嘿”地笑着。我们把不胜酒力的老钱扶上沙发,老钱微闭着眼,嘴里却一直嘟囔个不停。老伴笑着说,也不知道他在哼些啥。我们却听得十分清楚,“今天老钱来拖地,又捡十个瓶……”
酒局未散,沙发上的老钱,脸上两行泪痕已经干透,笑意盈盈,酣声正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