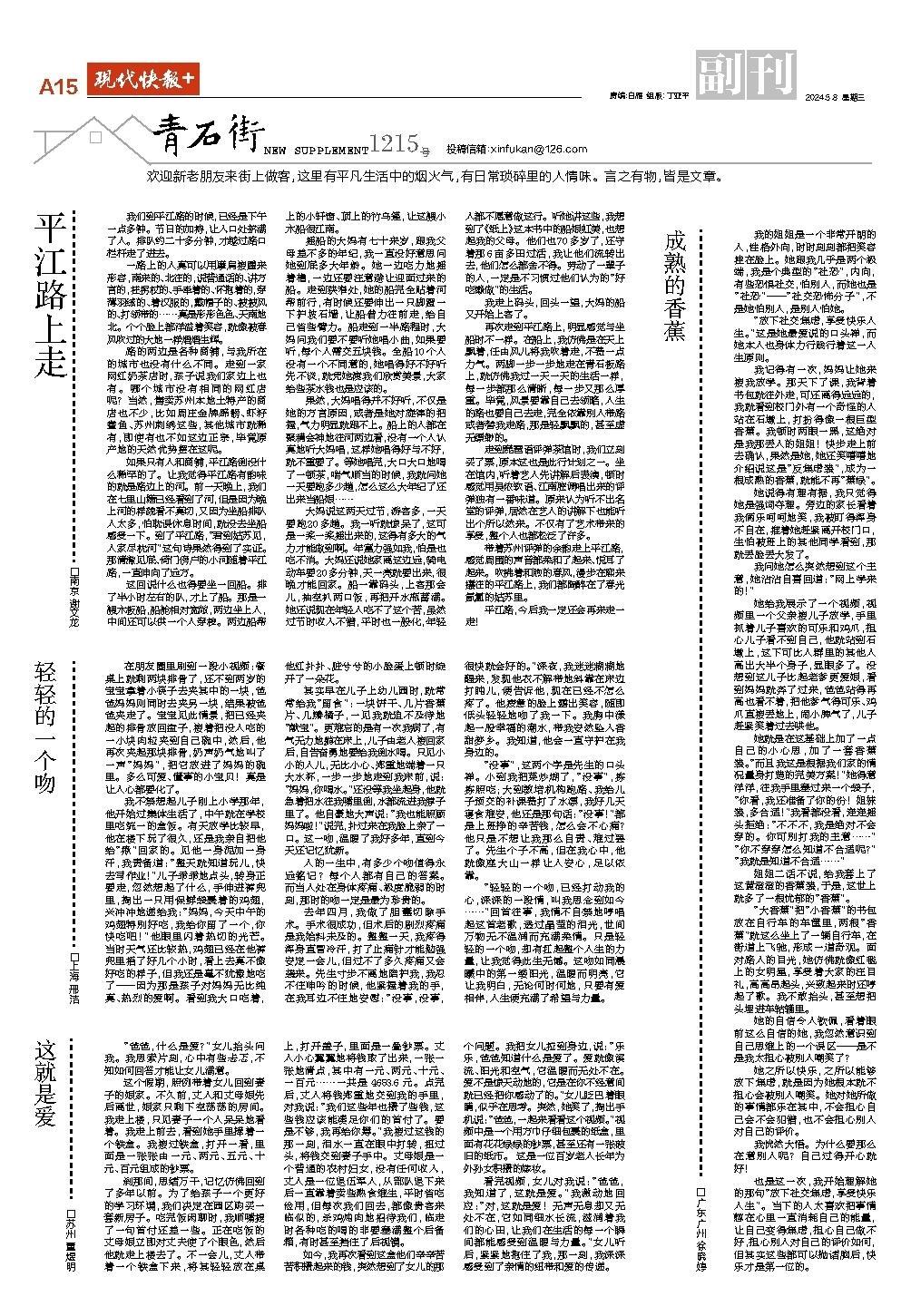□南京 谢文龙
我们到平江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节日的加持,让入口处挤满了人。排队约二十多分钟,才越过路口栏杆走了进去。
一路上的人真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南来的、北往的,说普通话的、讲方言的,拄拐杖的、手牵着的、怀抱着的,穿薄羽绒的、着汉服的,戴帽子的、披披风的、打领带的……真是形形色色、天南地北。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就像被春风吹过的大地一样熠熠生辉。
路的两边是各种商铺,与我所在的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同。走到一家网红奶茶店时,孩子说我们家边上也有。哪个城市没有相同的网红店呢?当然,售卖苏州本地土特产的商店也不少,比如周庄金牌蹄髈、虾籽鲞鱼、苏州刺绣这些,其他城市就稀有,即使有也不如这边正宗,毕竟原产地的天然优势摆在这呢。
如果只有人和商铺,平江路倒没什么稀罕的了。让我觉得平江路有韵味的就是路边上的河。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七里山塘已经看到了河,但是因为晚上河的样貌看不真切,又因为坐船排队人太多,怕耽误休息时间,就没去坐船感受一下。到了平江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这句诗果然得到了实证。那清澈见底、倚门傍户的小河随着平江路,一直伸向了远方。
这回说什么也得要坐一回船。排了半小时左右的队,才上了船。那是一艘木板船,船舱相对宽敞,两边坐上人,中间还可以供一个人穿梭。两边船帮上的小轩窗、顶上的竹乌篷,让这艘小木船很江南。
摇船的大妈有七十来岁,跟我父母差不多的年纪,我一直没好意思问她到底多大年龄。她一边吃力地摇着橹,一边还要注意避让迎面过来的船。走到狭窄处,她的船完全贴着河帮前行,有时候还要伸出一只脚蹬一下护坡石墙,让船借力往前走,给自己省些臂力。船走到一半路程时,大妈问我们要不要听她唱小曲,如果要听,每个人需交五块钱。全船10个人没有一个不同意的,她唱得好不好听先不谈,就凭她渡我们欣赏美景,大家给些茶水钱也是应该的。
果然,大妈唱得并不好听,不仅是她的方言原因,或者是她对旋律的把握,气力明显就跟不上。船上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往河两边看,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听大妈唱,这样她唱得好与不好,就不重要了。等她唱完,大口大口地喝了一顿茶,喘气顺当的时候,我就问她一天要跑多少趟,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当船娘……
大妈说这两天过节,游客多,一天要跑20多趟。我一听就惊呆了,这可是一桨一桨摇出来的,这得有多大的气力才能做到啊。年富力强如我,怕是也吃不消。大妈还说她家离这边远,骑电动车要20多分钟,天一亮就要出来,很晚才能回家。船一靠码头,上客那会儿,抽空扒两口饭,再把开水瓶蓄满。她还说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虽然过节时收入不错,平时也一般化,年轻人都不愿意做这行。听她讲这些,我想到了《纸上》这本书中的船娘虹美,也想起我的父母。他们也70多岁了,还守着那6亩多田过活,我让他们流转出去,他们怎么都舍不得。劳动了一辈子的人,一定是不习惯过他们认为的“好吃懒做”的生活。
我走上码头,回头一望,大妈的船又开始上客了。
再次走到平江路上,明显感觉与坐船时不一样。在船上,我仿佛是在天上飘着,任由风儿将我吹着走,不费一点力气。两脚一步一步地走在青石板路上,就仿佛我过一天一天的生活一样,每一步都那么清晰,每一步又那么厚重。毕竟,风景要靠自己去领略,人生的路也要自己去走,完全依靠别人带路或者替我走路,那是轻飘飘的,甚至虚无缥缈的。
走到琵琶语评弹茶馆时,我们立刻买了票,原本这也是此行计划之一。坐在馆内,听着艺人先讲解后表演,顿时感觉用吴侬软语、江南腔调唱出来的评弹独有一番味道。原来认为听不出名堂的评弹,居然在艺人的讲解下也能听出个所以然来。不仅有了艺术带来的享受,整个人也都松泛了许多。
带着苏州评弹的余韵走上平江路,感觉周围的声音都柔和了起来、悦耳了起来。吹拂着和煦的春风,漫步在熙来攘往的平江路上,我们都陶醉在了春光氤氲的姑苏里。
平江路,今后我一定还会再来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