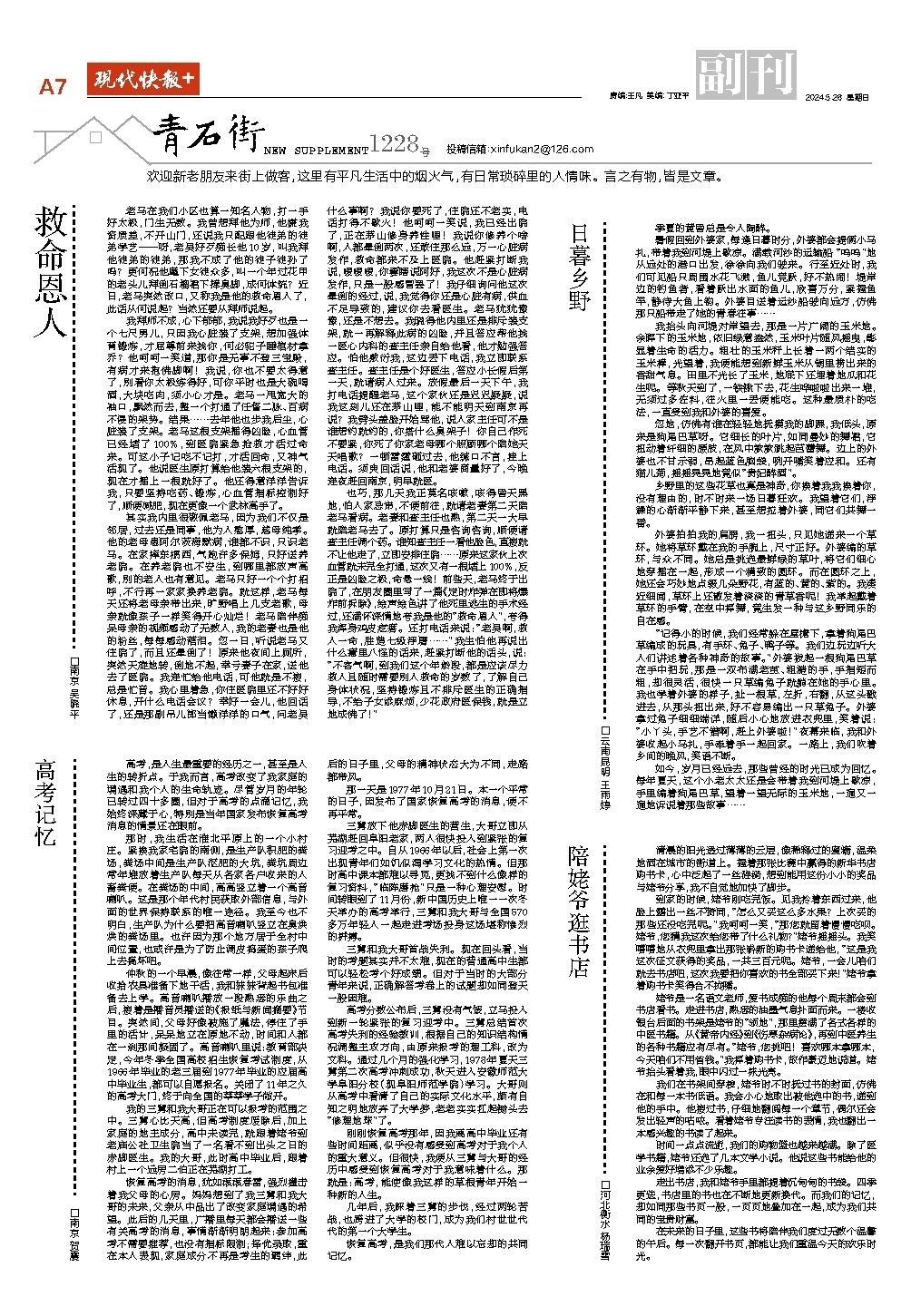□南京 贺震
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经历之一,甚至是人生的转折点。于我而言,高考改变了我家庭的境遇和我个人的生命轨迹。尽管岁月的年轮已转过四十多圈,但对于高考的点滴记忆,我始终深藏于心,特别是当年国家发布恢复高考消息的情景还在眼前。
那时,我生活在淮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紧挨我家宅院的南侧,是生产队积肥的粪场,粪场中间是生产队沤肥的大坑,粪坑周边常年堆放着生产队每天从各家各户收来的人畜粪便。在粪场的中间,高高竖立着一个高音喇叭。这是那个年代村民获取外部信息,与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我至今也不明白,生产队为什么要把高音喇叭竖立在臭烘烘的粪场里。也许因为那个地方居于全村中间位置,也或许是为了防止调皮捣蛋的孩子爬上去搞坏吧。
仲秋的一个早晨,像往常一样,父母起床后收拾农具准备下地干活,我和妹妹背起书包准备去上学。高音喇叭播放一段熟悉的乐曲之后,接着是播音员播送的《报纸与新闻摘要》节目。突然间,父母好像被施了魔法,停住了手里的活计,呆呆地立在原地不动,时间和人都在一刹那间凝固了。高音喇叭里说:教育部决定,今年冬季全国高校招生恢复考试制度,从1966年毕业的老三届到1977年毕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自愿报名。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向全国的莘莘学子敞开。
我的三舅和我大哥正在可以报考的范围之中。三舅心比天高,但高考制度废除后,加上家庭的地主成分,高中未读完,就跟着姥爷到老庙公社卫生院当了一名看不到出头之日的赤脚医生。我的大哥,此时高中毕业后,跟着村上一个远房二伯正在芜湖打工。
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滚滚春雷,强烈撞击着我父母的心房。妈妈想到了我三舅和我大哥的未来,父亲从中品出了改变家庭境遇的希望。此后的几天里,广播里每天都会播送一些有关高考的消息,事情渐渐明朗起来:参加高考不需要推荐,也没有指标限制;择优录取,重在本人表现,家庭成分不再是考生的羁绊,此后的日子里,父母的精神状态大为不同,走路都带风。
那一天是1977年10月21日。本一个平常的日子,因发布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便不再平常。
三舅放下他赤脚医生的营生,大哥立即从芜湖赶回阜阳老家,两人很快投入到紧张的复习迎考之中。自从1966年以后,社会上第一次出现青年们如饥似渴学习文化的热情。但那时高中课本都难以寻觅,更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复习资料,“临阵磨枪”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时间转眼到了11月份,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天举办的高考举行,三舅和我大哥与全国570多万年轻人一起走进考场投身这场堪称惨烈的拼搏。
三舅和我大哥首战失利。现在回头看,当时的考题其实并不太难,现在的普通高中生都可以轻松考个好成绩。但对于当时的大部分青年来说,正确解答考卷上的试题却如同登天一般困难。
高考分数公布后,三舅没有气馁,立马投入到新一轮紧张的复习迎考中。三舅总结首次高考失利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情况调整主攻方向,由原来报考的理工科,改为文科。通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1978年夏天三舅第二次高考冲刺成功,秋天进入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现阜阳师范学院)学习。大哥则从高考中看清了自己的实际文化水平,颇有自知之明地放弃了大学梦,老老实实扛起锄头去“修理地球”了。
刚刚恢复高考那年,因我离高中毕业还有些时间距离,似乎没有感受到高考对于我个人的重大意义。但很快,我便从三舅与大哥的经历中感受到恢复高考对于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高考,能使像我这样的草根青年开始一种新的人生。
几年后,我踩着三舅的步伐,经过两轮苦战,也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成为我们村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
恢复高考,是我们那代人难以忘却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