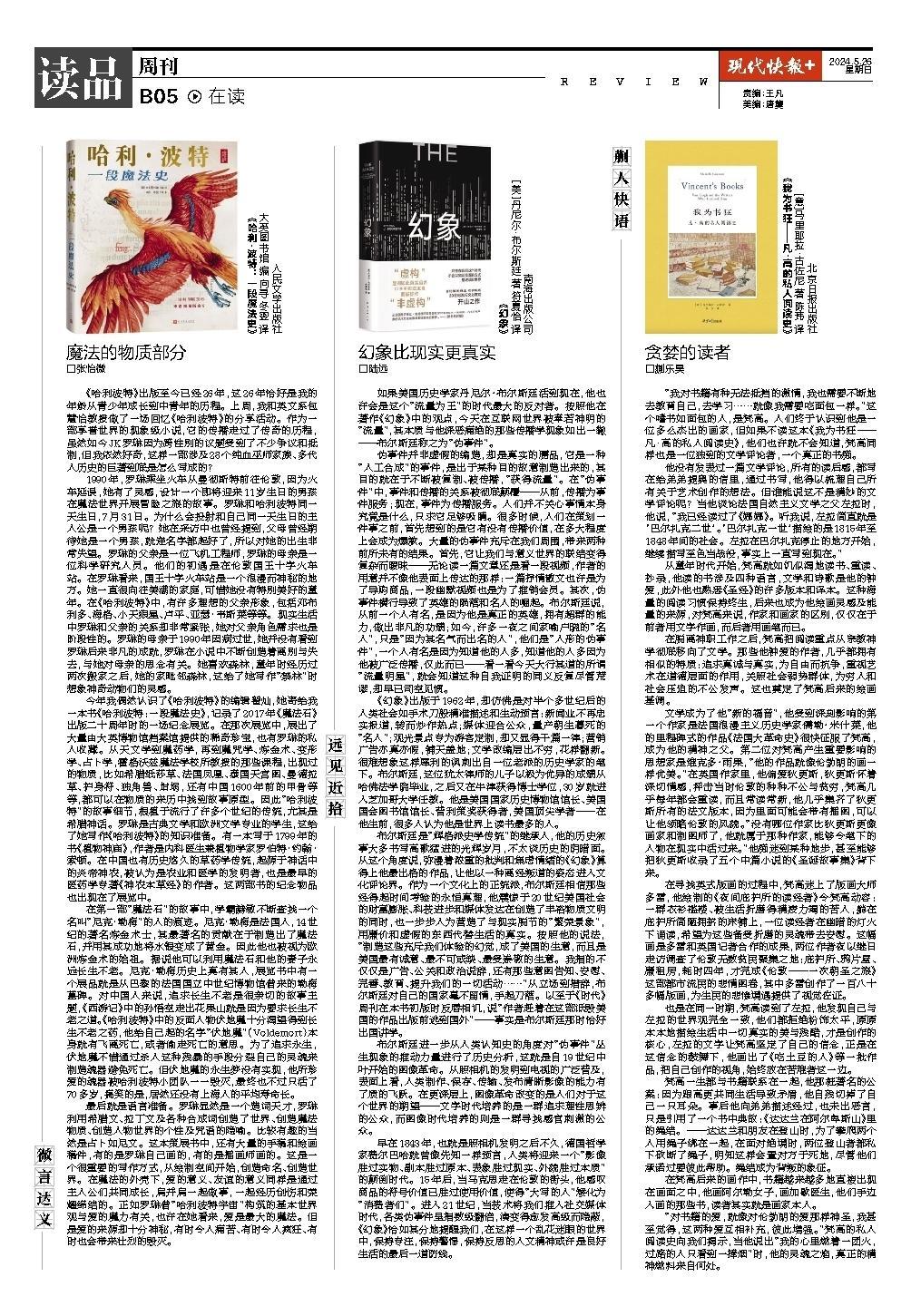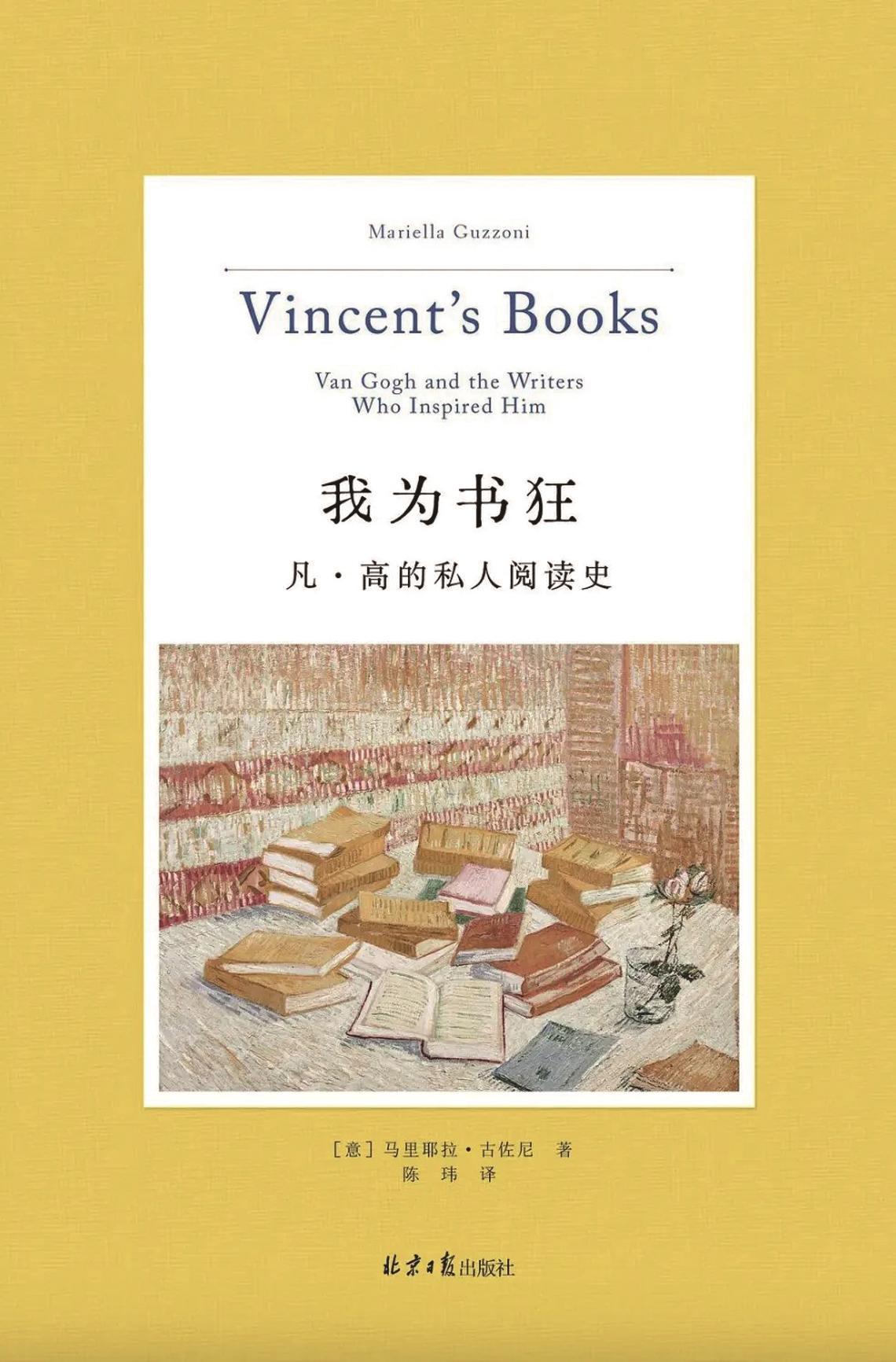□蒯乐昊
“我对书籍有种无法抵挡的激情,我也需要不断地去教育自己,去学习……就像我需要吃面包一样。”这个嗜书如面包的人,是梵高。人们终于认识到他是一位多么杰出的画家,但如果不读这本《我为书狂——凡·高的私人阅读史》,他们也许就不会知道,梵高同样也是一位独到的文学评论者,一个真正的书痴。
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学评论,所有的读后感,都写在给弟弟提奥的信里,通过书写,他得以梳理自己所有关于艺术创作的想法。但谁能说这不是精妙的文学评论呢?当他谈论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之父左拉时,他说,“我已经读过了《娜娜》。听我说,左拉简直就是‘巴尔扎克二世’。‘巴尔扎克一世’描绘的是1815年至1848年间的社会。左拉在巴尔扎克停止的地方开始,继续描写至色当战役,事实上一直写到现在。”
从童年时代开始,梵高就如饥似渴地读书、重读、抄录,他读的书涉及四种语言,文学和诗歌是他的钟爱,此外他也熟悉《圣经》的许多版本和译本。这种海量的阅读习惯保持终生,后来也成为他绘画灵感及能量的来源,对梵高来说,作家和画家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用文字作画,而后者用画笔而已。
在脱离神职工作之后,梵高把阅读重点从宗教神学彻底移向了文学。那些他钟爱的作者,几乎都拥有相似的特质:追求真诚与真实,为自由而抗争,重视艺术在道德层面的作用,关照社会弱势群体,为穷人和社会压迫的不公发声。这也奠定了梵高后来的绘画基调。
文学成为了他“新的福音”,他受到深刻影响的第一个作家是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史》很快征服了梵高,成为他的精神之父。第二位对梵高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是维克多·雨果,“他的作品就像伦勃朗的画一样优美。”在英国作家里,他偏爱狄更斯,狄更斯怀着深切情感,抨击当时伦敦的种种不公与贫穷,梵高几乎每年都会重读,而且常读常新,他几乎集齐了狄更斯所有的法文版本,因为里面可能会带有插图,可以让他领略伦敦的风貌。“没有哪位作家比狄更斯更像画家和制图师了,他就属于那种作家,能够令笔下的人物在现实中活过来。”他痴迷到某种地步,甚至能够把狄更斯收录了五个中篇小说的《圣诞故事集》背下来。
在寻找英式版画的过程中,梵高迷上了版画大师多雷,他绘制的《夜间庇护所的读经者》令梵高动容:一群衣衫褴褛、被生活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苦人,躺在庇护所简陋拥挤的床铺上,一位读经者在幽暗的灯火下诵读,希望为这些备受折磨的灵魂带去安慰。这幅画是多雷和英国记者合作的成果,两位作者夜以继日走访调查了伦敦无数贫民聚集之地:庇护所、鸦片屋、廉租房,耗时四年,才完成《伦敦——一次朝圣之旅》这部都市流民的悲情图卷,其中多雷创作了一百八十多幅版画,为生民的悲惨境遇提供了视觉佐证。
也是在同一时期,梵高读到了左拉,他发现自己与左拉的世界观完全一致,他们都拒绝粉饰太平,原原本本地描绘生活中一切真实的美与残酷,才是创作的核心,左拉的文字让梵高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正是在这信念的鼓舞下,他画出了《吃土豆的人》等一批作品,把自己创作的视角,始终放在苦难者这一边。
梵高一生都与书籍联系在一起,他那桩著名的公案:因为跟高更共同生活导致矛盾,他自残切掉了自己一只耳朵。事后他向弟弟描述经过,也未出恶言,只是引用了一个书中典故:《达达兰在阿尔卑斯山》里的绳结。——达达兰和朋友在登山时,为了攀爬两个人用绳子绑在一起,在面对绝境时,两位登山者都私下砍断了绳子,明知这样会置对方于死地,尽管他们承诺过要彼此帮助。绳结成为背叛的象征。
在梵高后来的画作中,书籍越来越多地直接出现在画面之中,他画阿尔勒女子,画加歇医生,他们手边入画的那些书,读者其实就是画家本人。
“对书籍的爱,就像对伦勃朗的爱那样神圣,我甚至觉得,这两种爱互相补充,彼此增强。”梵高的私人阅读史向我们揭示,当他说出“我的心里燃着一团火,过路的人只看到一捧烟”时,他的灵魂之焰,真正的精神燃料来自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