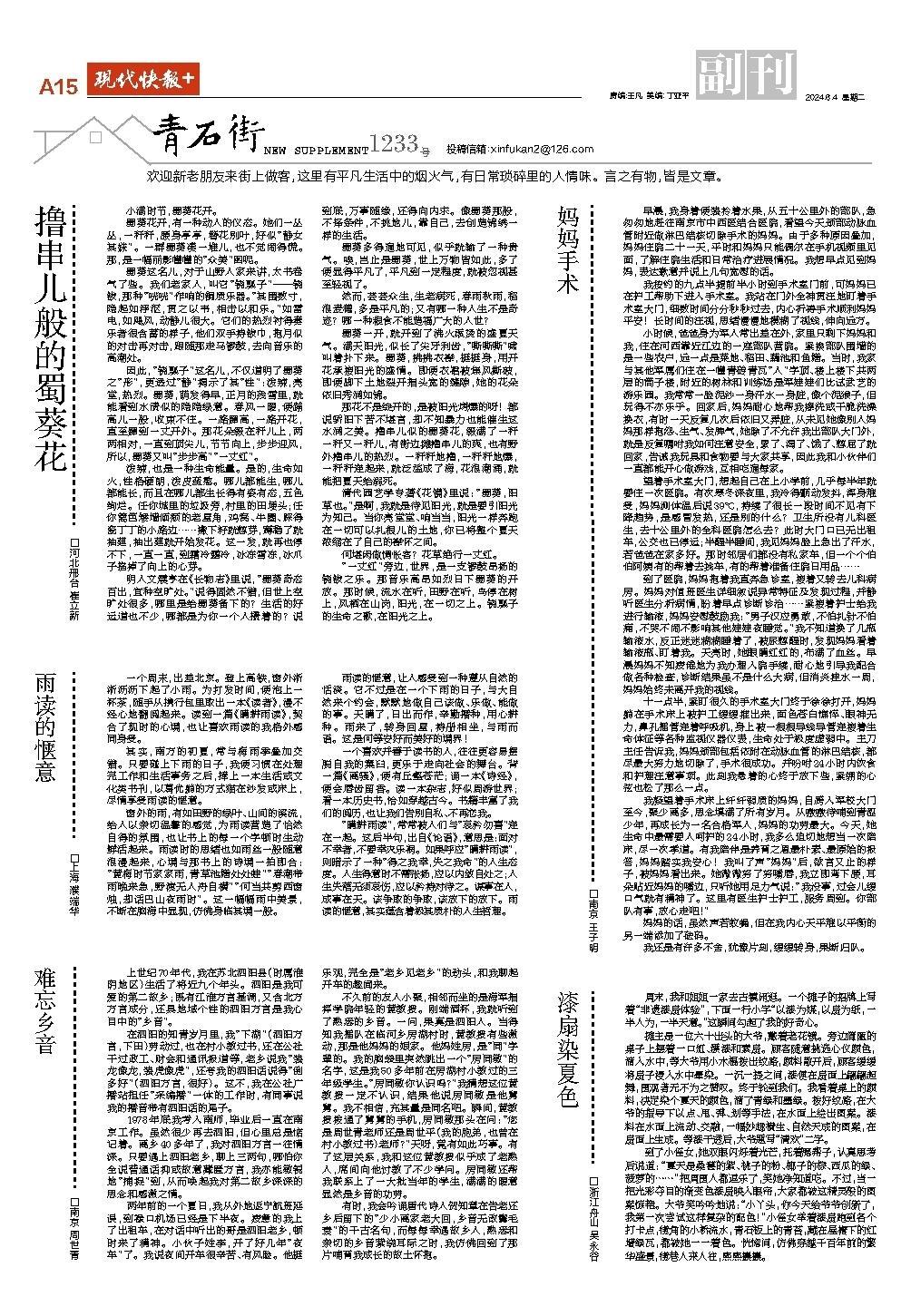□河北邢台 崔立新
小满时节,蜀葵花开。
蜀葵花开,有一种动人的仪态。她们一丛丛,一秆秆,腰身亭亭,簪花别叶,好似“静女其姝”。一群蜀葵凑一堆儿,也不觉闹得慌。那,是一幅丽影幢幢的“众美”图呢。
蜀葵这名儿,对于山野人家来讲,太书卷气了些。我们老家人,叫它“铙瓢子”——铙钹,那种“咣咣”作响的铜质乐器。“其围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如雷电,如飓风,动静儿很大。它们的热烈衬得奏乐者很含蓄的样子,他们双手持钹巾,抱月似的对击再对击,跟随那走马锣鼓,去向音乐的高潮处。
因此,“铙瓢子”这名儿,不仅道明了蜀葵之“形”,更透过“静”揭示了其“性”:泼辣,亮堂,热烈。蜀葵,萌发得早,正月的残雪里,就能看到水渍似的隐隐绿意。春风一暖,便蹦高儿一般,收束不住。一路蹿高,一路开花,直至蹿到一丈开外。那花朵缀在秆儿上,两两相对,一直到顶尖儿,节节向上,步步迎风,所以,蜀葵又叫“步步高”“一丈红”。
泼辣,也是一种生命能量。是的,生命如火,性格硬朗,泼皮蛮憨。哪儿都能生,哪儿都能长,而且在哪儿都生长得有姿有态,五色绚烂。任你城里的垃圾旁,村里的田埂头;任你篱笆矮墙倾颓的老屋角,鸡窝、牛圈、踩得瓷丁丁的小路边……撒下籽就憋芽,蹲稳了就抽莛,抽出莛就开始发花。这一发,就再也停不下,一直一直,到霜冷露冷,冰冻雪冻,冰爪子掐掉了向上的心芽。
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说,“蜀葵奇态百出,宜种空旷处。”说得固然不错,但世上空旷处很多,哪里是给蜀葵备下的?生活的好运道也不少,哪都是为你一个人攒着的?说到底,万事随缘,还得向内求。像蜀葵那般,不择条件,不挑地儿,靠自己,去创造锦绣一样的生活。
蜀葵多得遍地可见,似乎就输了一种贵气。唉,岂止是蜀葵,世上万物皆如此,多了便显得平凡了,平凡到一定程度,就被忽视甚至轻视了。
然而,芸芸众生,生老病死,春雨秋雨,稻浪麦穗,多是平凡的;又有哪一种人生不是奇迹?哪一种粮食不能造福广大的人世?
蜀葵一开,就开到了沸火滚烫的盛夏天气。满天阳光,似长了尖牙利齿,“嘶嘶嘶”啸叫着扑下来。蜀葵,拂拂衣襟,挺挺身,用开花承接阳光的盛情。即便衣裙被焦风撕破,即便脚下土地裂开指头宽的缝隙,她的花朵依旧秀润如锦。
那花不是绽开的,是被阳光烤爆的呀!都说骄阳下苦不堪言,却不知暴力也能催生这水润之美。撸串儿似的蜀葵花,缀满了一秆一秆又一秆儿,有街边摊撸串儿的爽,也有野外撸串儿的热烈。一秆秆地撸,一秆秆地爆,一秆秆连起来,就泛滥成了海,花浪潮涌,就能把夏天给溺死。
清代园艺学专著《花镜》里说:“蜀葵,阳草也。”是啊,我就是待见阳光,就是要引阳光为知己。当你亮堂堂、响当当,阳光一样奔跑在一切可以扎根儿的土地,你已将整个夏天浓缩在了自己的襟怀之间。
何堪闲做惆怅客?花草绝行一丈红。
“一丈红”旁边,世界,是一支锣鼓昂扬的铙钹之乐。那音乐高昂如烈日下蜀葵的开放。那时候,流水在听,田野在听,鸟停在树上,风栖在山岗,阳光,在一切之上。铙瓢子的生命之歌,在阳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