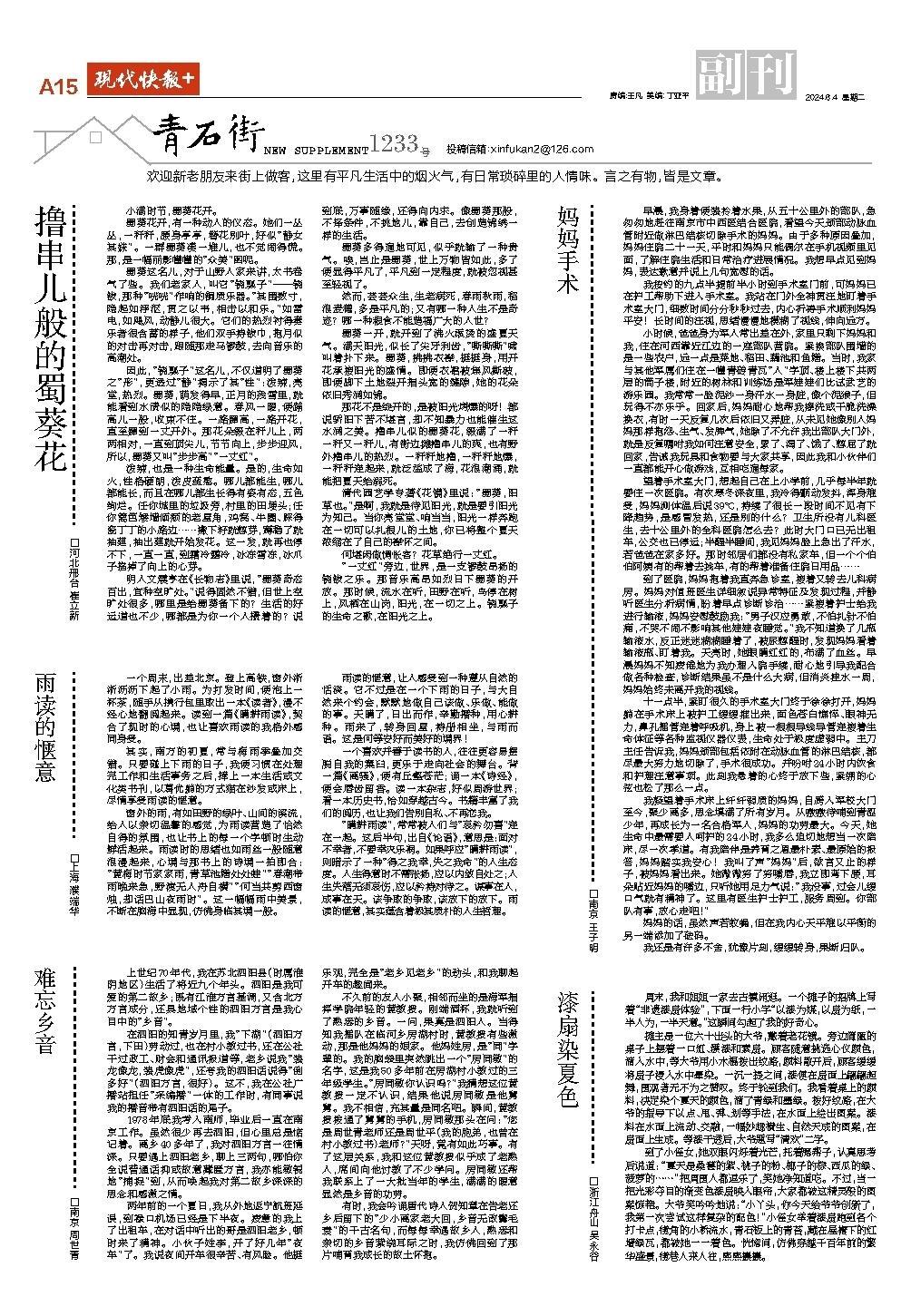□南京 周世青
上世纪70年代,我在苏北泗阳县(时属淮阴地区)生活了将近九个年头。泗阳是我可爱的第二故乡;既有江淮方言基调,又含北方方言成分,还具地域个性的泗阳方言是我心目中的“乡音”。
在泗阳的知青岁月里,我“下湖”(泗阳方言,下田)劳动过,也在村小教过书,还在公社干过政工、财会和通讯报道等,老乡说我“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还夸我的泗阳话说得“倒多好”(泗阳方言,很好)。这不,我在公社广播站担任“采编播”一体的工作时,有同事说我的播音带有泗阳话的尾子。
1978年底我考入南师,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工作。虽然很少再去泗阳,但心里总是惦记着。离乡40多年了,我对泗阳方言一往情深。只要遇上泗阳老乡,聊上三两句,哪怕你全说普通话抑或故意藏匿方言,我亦能敏锐地“捕捉”到,从而唤起我对第二故乡深深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两年前的一个夏日,我从外地返宁航班延误,到禄口机场已经是下半夜。疲惫的我上了出租车,在对话中听出的哥是泗阳老乡,顿时来了精神。小伙子姓李,开了好几年“夜车”了。我说夜间开车很辛苦、有风险。他挺乐观,完全是“老乡见老乡”的劲头,和我聊起开车的趣闻来。
不久前的友人小聚,相邻而坐的是海军指挥学院年轻的黄教授。刚端酒杯,我就听到了熟悉的乡音。一问,果真是泗阳人。当得知我插队在临河乡房湖村时,黄教授有些激动,那是他妈妈的娘家。他妈姓房,是“同”字辈的。我的脑袋里突然跳出一个“房同敏”的名字,这是我50多年前在房湖村小教过的三年级学生。“房同敏你认识吗?”我猜想这位黄教授一定不认识,结果他说房同敏是他舅舅。我不相信,充其量是同名吧。瞬间,黄教授拨通了舅舅的手机,房同敏那头在问:“您是周世青老师还是周世平(我的胞弟,也曾在村小教过书)老师?”天呀,竟有如此巧事。有了这层关系,我和这位黄教授似乎成了老熟人,席间向他讨教了不少学问。房同敏还帮我联系上了一大批当年的学生,满满的暖意显然是乡音的功劳。
有时,我会吟诵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告老还乡后留下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千古名句,而每每幸遇故乡人,熟悉和亲切的乡音萦绕耳际之时,我仿佛回到了那片哺育我成长的故土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