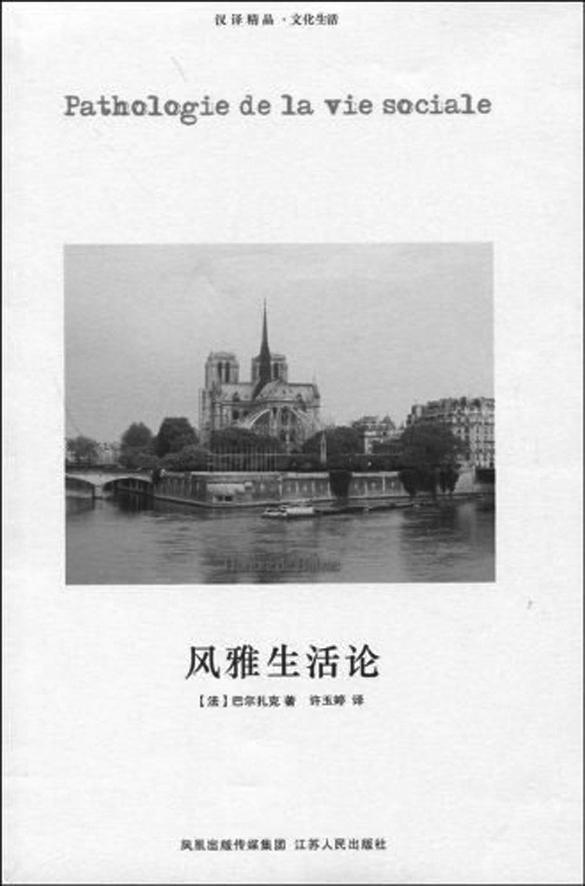□蒯乐昊
如今,在生活的压力面前吐槽自己满身“班味”的年轻人,读到巴尔扎克的《风雅生活论》,应该会心有戚戚焉,“劳碌生活的主题没有变体。人用双手劳作,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变成一种手段……由劳动组编起来的人,和蒸汽机一样,全都是一个模子生产出来的,毫无个性。工具人是一种社会零,如果前面没有数字,再多的零加在一起,都得不出一个数目。”
在巴尔扎克的连珠妙语里面,生活,无论是文明的生活,还是野蛮的生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休息,为了摆脱劳作,但绝对的休息又容易导致忧郁,于是有钱有闲有资本休息的人,就过起了“风雅生活”——所谓风雅生活,从本质上来说,即一种活跃休息的艺术。自己欠了一屁股债的巴尔扎克得出令人心碎的结论:习惯劳动的人,就不能理解风雅生活。要时髦,就必须不劳动而直接享受休息,也就是说,应该中个四合彩,或者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或亲王,捞个闲差或兼差。
巴尔扎克在两百年前就代厌恶上班的年轻人道出了心声。1821年,巴尔扎克还是个22岁的毛头小伙,他写信给他情义甚笃的妹妹劳尔,信中激动地写道:如果我有个职位,我就会疯掉,而马卡尔先生却要找一个活儿。我或许会成为一名职员,一台机器,一匹每天跑上三四十圈的畜力马,按时喝水、吃饭和睡觉;我将和其他人毫无两样。如此围着磨盘转,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事情,人们居然把这叫作生活?
很可惜,巴尔扎克出生于中产家庭,没有世袭的富贵,也不是贵族后代。父母希望他学习法律,但在巴尔扎克认知的阶级序列里,法官、律师和公证人虽然比普通劳工强一些,但也不过是仪器上的抛了光上了油的齿轮链条而已,貌似体面,但思想不自由,又缺乏创造力。从法律学校毕业后,他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为了早日暴富,实现阶层跃升,过上可以活跃休息的风雅生活,他写流行小说,自做出版、办印刷厂、铸字厂,出版名著丛书……事实证明,他不是经商的料,他所有创业梦统统宣告失败,从此债台高筑,被拖累了一生。
《风雅生活论》最初是具时效性的报纸文章,应《时尚报》约稿而写,其目的是让读者一窥名流生活。但巴尔扎克在这种风尚论文里塞进了他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一系列社会变革的观察,“尽管1789年运动明显地改善了社会秩序,而财产不平等必然造成的弊端却以各种新形式死灰复燃。在可笑的衰落的领主阶级之后,我们不是迎来了具备金钱、权力和才能的三重贵族吗?这个贵族阶级,尽管完全合法,民众受到的压迫却并未因此而减少,因为金融贵族、官僚机构以及作为能人们进身之阶的报纸和法院的网络还压在民众头上呢。这样,法国通过恢复君主立宪制,肯定了政治平等的谎言,结果不过是使罪恶更为普及而已;因为我们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才刚刚过去三个月,但这种批判性的洞察,直到今天仍没有过时——巴尔扎克对社会阶层性不公的反击方式是,过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他一生极其高产,在他看来,只有艺术家才可能同时兼顾劳作与风雅,艺术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按自己的才能来生活。
讽刺的是,1883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为纪念巴尔扎克,决定出资为他雕刻纪念像。第一位雕刻家忙活了8年,还没来得及完成任务就去世了,接盘侠是雕塑大师罗丹,罗丹为这尊雕像又忙活了7年,前后做了近20尊巴尔扎克像,几易其稿,最后定版,是一尊青铜巴尔扎克,头发凌乱,身上裹一件潦草邋遢的睡袍,罗丹想表现《人间喜剧》的作者因躲债而隐居,夜深人静时被文思激发的场景,完全不顾这位《风雅生活论》的作者是如何鼓吹羊绒、丝绸,上好衣料和考究服饰是如何烘托出一个人的灵魂。巴尔扎克本人可能极不愿意以这副衣衫不整的面目示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风雅是时代的产物。罗丹完成巴尔扎克雕像的时候,距离巴尔扎克《风雅生活论》发表,已过去了70年;距离巴尔扎克辞世,也过去了半个世纪。1900年前后的法国,已经是现代主义的天下,落拓不羁正在成为新的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