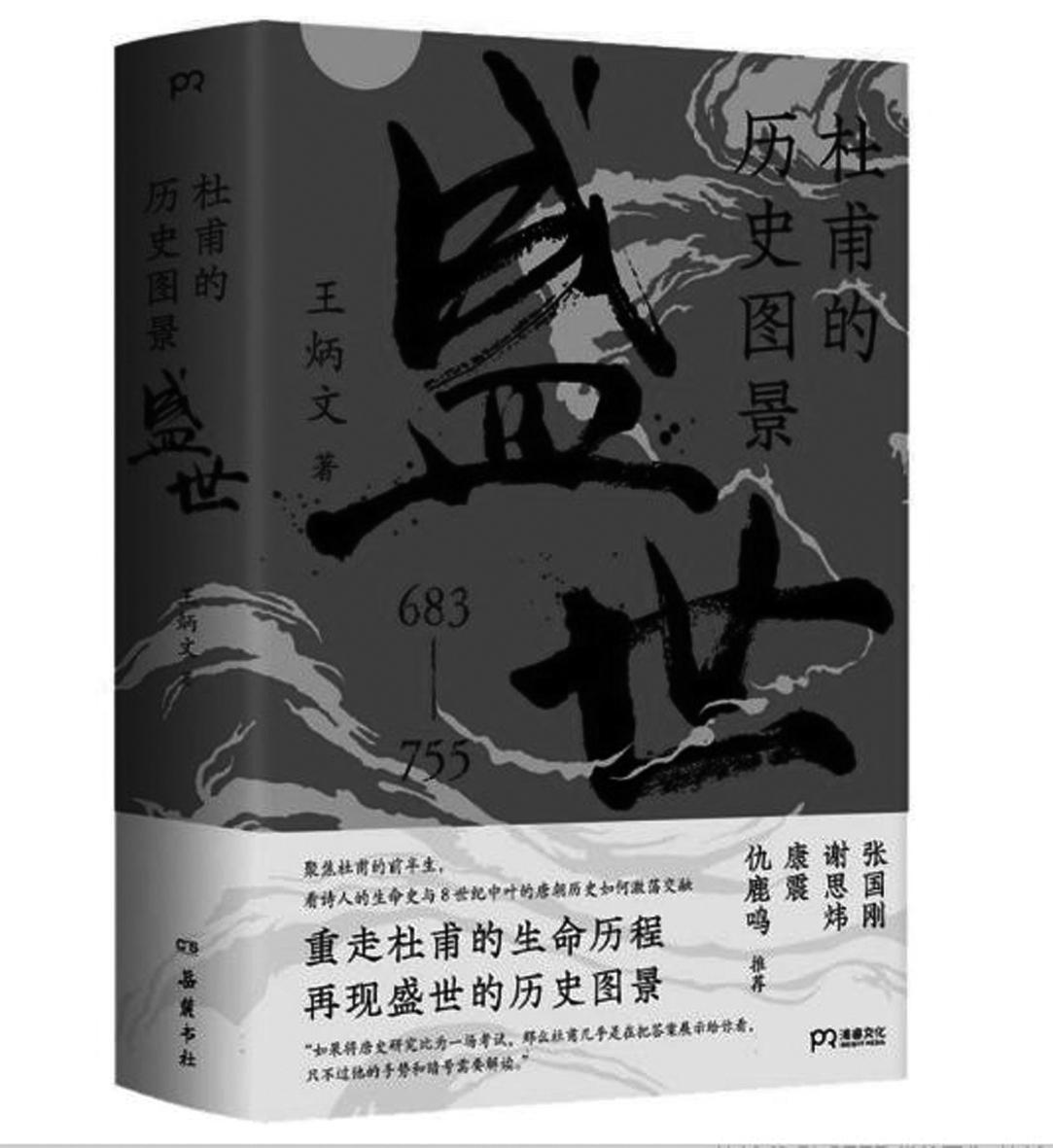□赵昱华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写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生于公元712年,他前四十四年的生命史,与玄宗朝的统治盛世是紧密相连的。
这部作品不仅是杜甫前半生的传记,王炳文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公元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以杜甫的视角,去考证、去还原他所见的历史图景。杜甫出身世家,早期生活安定富足,亲身经历盛唐的繁华,而安史之乱,则将其人生割裂成两半,这对杜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线。
研究杜甫的生平,家庭背景是绕不开的话题。杜甫自述,杜家世代“奉儒守官”,做官是其家族“素业”。王炳文尤为重视的,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杜审言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作者却给了他一个“政治上晚熟”的评价,杜审言任职著作佐郎,这一职位,让其得以接触大量书籍,但屡次被放逐的经历,竟牵连子孙,难以入仕。作者借杜审言之眼,揭示了“开元盛世”之前武周、李唐王朝核心内部的权力之争。
杜甫的首次科举,按公认的说法,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但据王炳文的考证,这一时间可能提前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此处存疑,待商榷。据王炳文说,这时的杜甫年仅十七岁,胸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踏入考场。然而,现实给了杜甫一记重击,他的初试身手,撞上了唐中期铨选制度的大变革,加之文学、政务两派的斗争,让他尚未入仕,便身不由己地如同他的祖父一般卷入漩涡。
或许,这样的遭遇,让他深感不忿,落第以后,杜甫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壮游”,此时的他,心高气傲,结交了一批好友,遍走全国各地,登泰山、游齐赵,裘马轻狂,快意人生。我们不知,青年杜甫是否用这轻狂的生活,掩盖那心中的压抑,但无论如何,早期的杜甫诗句所表达出的,是一种强烈而自我的浪漫主义。
壮游打开了杜甫的视野,让他更加明确地感觉到了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或许,这正是杜甫视李白为偶像的原因所在。李白身上那股不羁的“仙气”,让杜甫得以把精神的追求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杜甫对于李白近乎狂热的推崇与爱戴,多少有对昔日自我的追忆。可以说,杜甫将自己的精神分为了两半,将那份归隐山林的出世情结投射到了李白身上,而自己则保留了那份属于现实的入世。自此以后,属于旧日的那个骄傲而浪漫的杜甫随李白踏舟而去;而属于当下的现实而冷静的杜甫,则前往长安,开始了十年的困居。
盛世时期的壮游,后来,终究成了乱世时期的飘零。晚年的杜甫,遥想往事,写下《遣怀·昔我游宋中》,感叹“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杜甫,如今白发苍苍满目悲戚,他用诗歌不断书写、记录历史的变迁、黎民的苦难。而我们展卷阅览这部杜甫传记,又何尝不怀想诗人们把臂共饮、翱翔天地的肆意不羁呢?又何尝不怀想开元全盛时期的辉煌与壮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