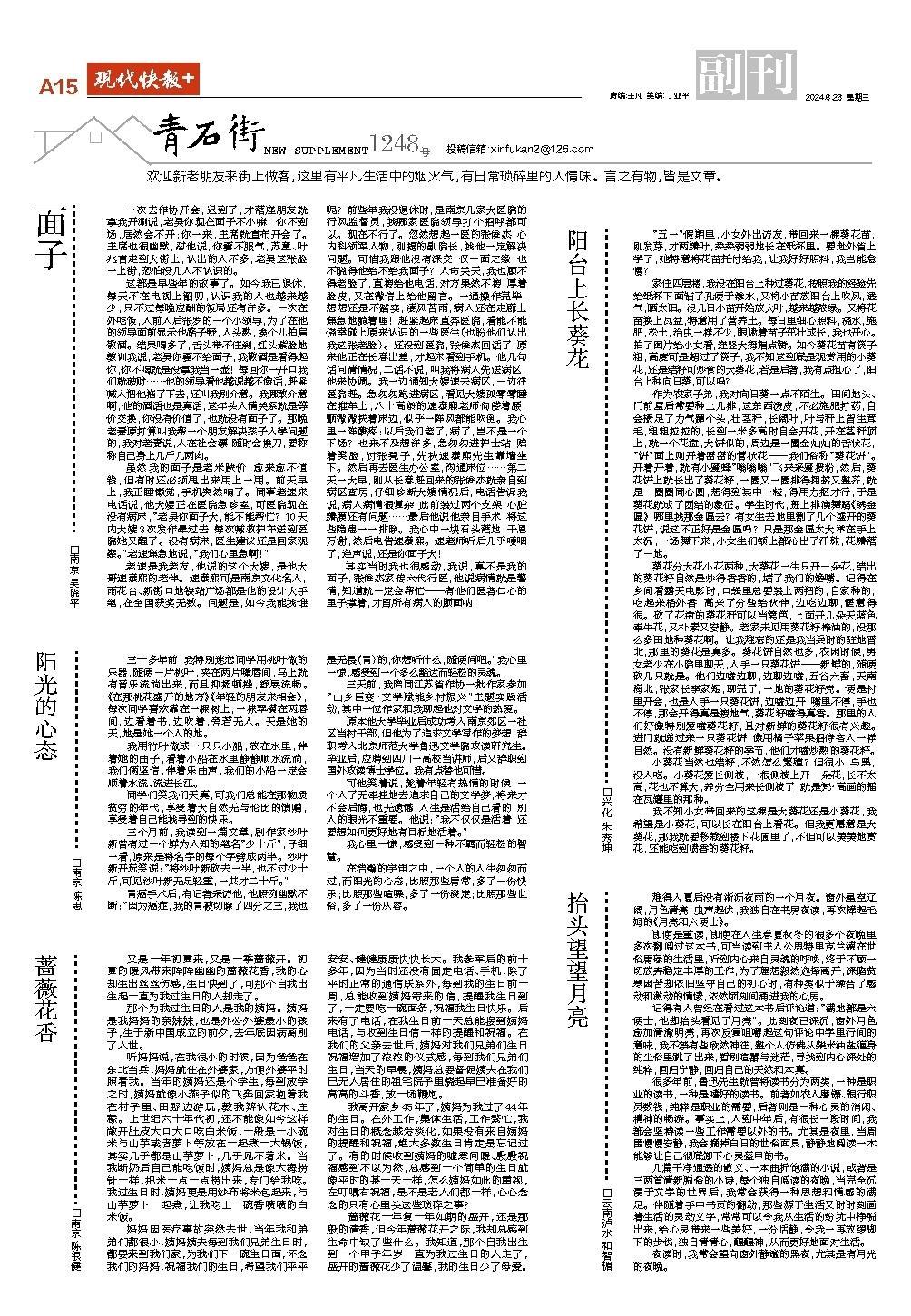□南京 陈银健
又是一年初夏来,又是一季蔷薇开。初夏的暖风带来阵阵幽幽的蔷薇花香,我的心却生出丝丝伤感,生日快到了,可那个自我出生起一直为我过生日的人却走了。
那个为我过生日的人是我的姨妈。姨妈是我妈妈的亲妹妹,也是外公外婆最小的孩子,生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去年底因病离别了人世。
听妈妈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爸爸在东北当兵,妈妈就住在外婆家,方便外婆平时照看我。当年的姨妈还是个学生,每到放学之时,姨妈就像小燕子似的飞奔回家抱着我在村子里、田野边游玩,教我辨认花木、庄稼。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还不能像如今这样敞开肚皮大口大口吃白米饭,一般是一小碗米与山芋或者萝卜等放在一起煮一大锅饭,其实几乎都是山芋萝卜,几乎见不着米。当我断奶后自己能吃饭时,姨妈总是像大海捞针一样,把米一点一点捞出来,专门给我吃。我过生日时,姨妈更是用纱布将米包起来,与山芋萝卜一起煮,让我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
妈妈因医疗事故突然去世,当年我和弟弟们都很小,姨妈姨夫每到我们兄弟生日时,都要来到我们家,为我们下一碗生日面,怀念我们的妈妈,祝福我们的生日,希望我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长大。我参军后的前十多年,因为当时还没有固定电话、手机,除了平时正常的通信联系外,每到我的生日前一周,总能收到姨妈寄来的信,提醒我生日到了,一定要吃一碗面条,祝福我生日快乐。后来有了电话,在我生日前一天总能接到姨妈电话,与收到生日信一样的提醒和祝福。在我们的父亲去世后,姨妈对我们兄弟们生日祝福增加了浓浓的仪式感,每到我们兄弟们生日,当天的早晨,姨妈总要督促姨夫在我们已无人居住的祖宅院子里烧起早已准备好的高高的斗香,放一场鞭炮。
我离开家乡45年了,姨妈为我过了44年的生日。在外工作,集体生活,工作繁忙,我对生日的概念越发淡化,如果没有来自姨妈的提醒和祝福,绝大多数生日肯定是忘记过了。有的时候收到姨妈的嘘寒问暖、殷殷祝福感到不以为然,总感到一个简单的生日就像平时的某一天一样,怎么姨妈如此的重视,左叮嘱右祝福,是不是老人们都一样,心心念念的只有心里头这些琐碎之事?
蔷薇花一年复一年如期的盛开,还是那般的清香,但今年蔷薇花开之际,我却总感到生命中缺了些什么。我知道,那个自我出生到一个甲子年岁一直为我过生日的人走了,盛开的蔷薇花少了温馨,我的生日少了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