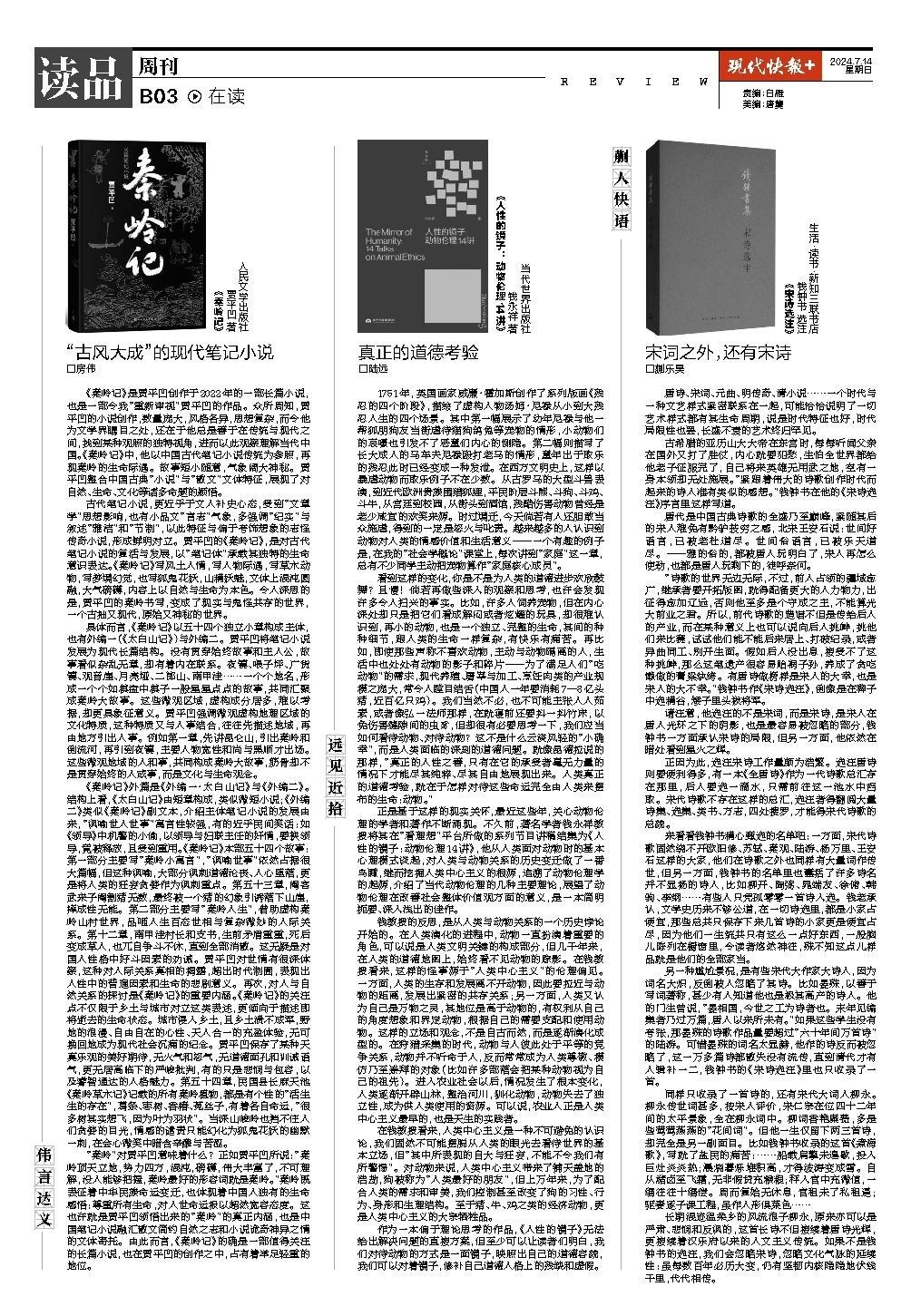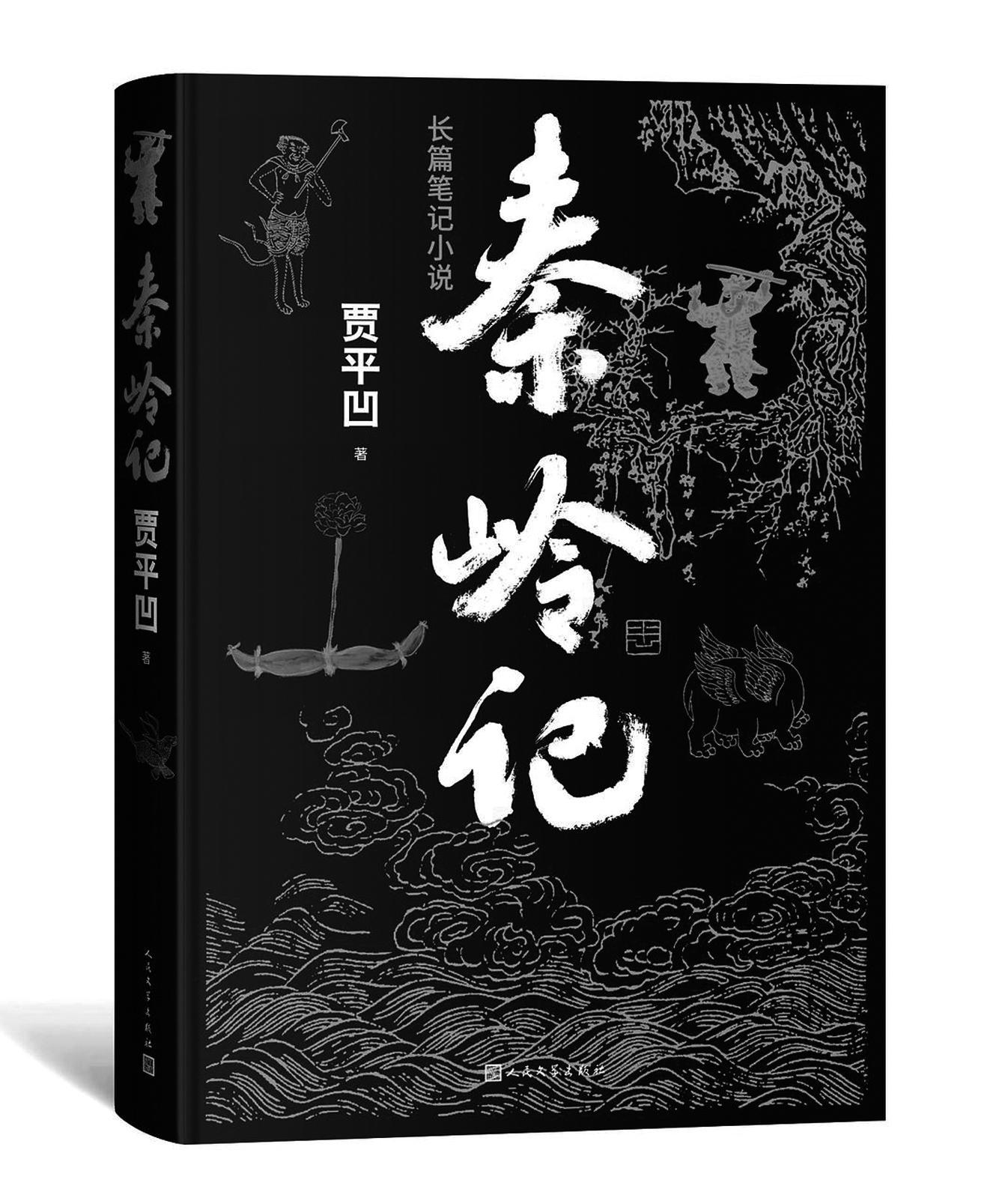□房伟
《秦岭记》是贾平凹创作于202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令我“重新审视”贾平凹的作品。众所周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数量庞大,风格各异,思想复杂,而令他为文学界瞩目之处,还在于他总是善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某种观照的独特视角,进而以此观察理解当代中国。《秦岭记》中,他以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传统为参照,再现秦岭的生命际遇。故事短小随意,气象阔大神秘。贾平凹整合中国古典“小说”与“散文”文体特征,展现了对自然、生命、文化等诸多命题的颖悟。
古代笔记小说,更近乎于文人补史心态,受到“文章学”思想影响,也有小品文“言志”气象,多强调“纪实”与叙述“雅洁”和“节制”,以此特征与偏于夸饰想象的志怪传奇小说,形成鲜明对立。贾平凹的《秦岭记》,是对古代笔记小说的复活与发展,以“笔记体”承载其独特的生命意识表达。《秦岭记》写风土人情,写人物际遇,写草木动物,写梦境幻觉,也写狐鬼花妖,山精妖魅,文体上混沌圆融,大气磅礴,内容上以自然与生命为本色。令人深思的是,贾平凹的秦岭书写,变成了现实与鬼怪共存的世界,一个古拙又现代,原始又神秘的世界。
具体而言,《秦岭记》以五十四个独立小章构成主体,也有外编一(《太白山记》)与外编二。贾平凹将笔记小说发展为现代长篇结构。没有贯穿始终故事和主人公,故事看似杂乱无章,却有着内在联系。夜镇、喂子坪、广货镇、观音崖、月亮垭、二郎山、南甲洼……一个个地名,形成一个个如棋盘中棋子一般星星点点的故事,共同汇聚成秦岭大故事。这些微观区域,虚构成分居多,难以考据,却更具象征意义。贾平凹强调微观虚构地理区域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又与人事结合,往往先描述地域,再由地方引出人事。例如第一章,先讲昆仑山,引出秦岭和倒流河,再引到夜镇,主要人物宽性和尚与黑顺才出场。这些微观地域的人和事,共同构成秦岭大故事,筋骨却不是贯穿始终的人或事,而是文化与生命观念。
《秦岭记》外篇是《外编一·太白山记》与《外编二》。结构上看,《太白山记》由短章构成,类似微短小说;《外编二》类似《秦岭记》副文本,介绍主体笔记小说的发展由来,“讽喻世人世事”寓言性较强,有的近乎民间笑话:如《领导》中机警的小偷,以领导与妇联主任的奸情,要挟领导,竟被释放,且受到重用。《秦岭记》本部五十四个故事:第一部分主要写“秦岭小寓言”,“讽喻世事”依然占据很大篇幅,但这种讽喻,大部分讽刺道德沦丧、人心堕落,更是将人类的狂妄贪婪作为讽刺重点。第五十三章,阉客武来子阉割猪无数,最终被一个猪的幻象引诱落下山崖,摔成性无能。第二部分主要写“秦岭人生”,借助虚构秦岭山村世界,品咂人生百态世相与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第十二章,南甲洼村长和支书,生前矛盾重重,死后变成草人,也兀自争斗不休,直到全部消散。这无疑是对国人性格中好斗因素的劝诫。贾平凹对世情有很深体察,这种对人际关系真相的揭露,超出时代制囿,表现出人性中的普遍因素和生命的悲剧意义。再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是《秦岭记》的重要内涵。《秦岭记》的关注点不仅限于乡土与城市对立这类表述,更倾向于描述即将逝去的生命状态。城市侵入乡土,且乡土溃不成军,野地的浪漫、自由自在的心性、天人合一的充盈体验,无可挽回地成为现代社会沉痛的纪念。贾平凹保存了某种天真乐观的美好期待,无火气和怒气,无道德面孔和训诫语气,更无居高临下的严峻批判,有的只是悲悯与包容,以及睿智通达的人格魅力。第五十四章,民国县长麻天池《秦岭草木记》记载的所有秦岭植物,都是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存在”,葛条、枣树、香椿、菟丝子,有着各自命运,“很多树其实想飞,因为叶为羽状”。当深山峻岭也挡不住人们贪婪的目光,情感的谴责只能幻化为狐鬼花妖的幽默一刺,在会心微笑中暗含辛酸与苦涩。
“秦岭”对贾平凹意味着什么?正如贾平凹所说:“秦岭顶天立地,势力四方,混沌,磅礴,伟大丰富了,不可理解,没人能够把握,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秦岭既表征着中华民族命运变迁,也体现着中国人独有的生命感悟:尊重所有生命,对人世命运报以超然宽容态度。这也许就是贾平凹领悟出来的“秦岭”的真正内涵,也是中国笔记小说融汇散文简约自然之志和小说诡奇神异之情的文体寄托。由此而言,《秦岭记》的确是一部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也在贾平凹的创作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