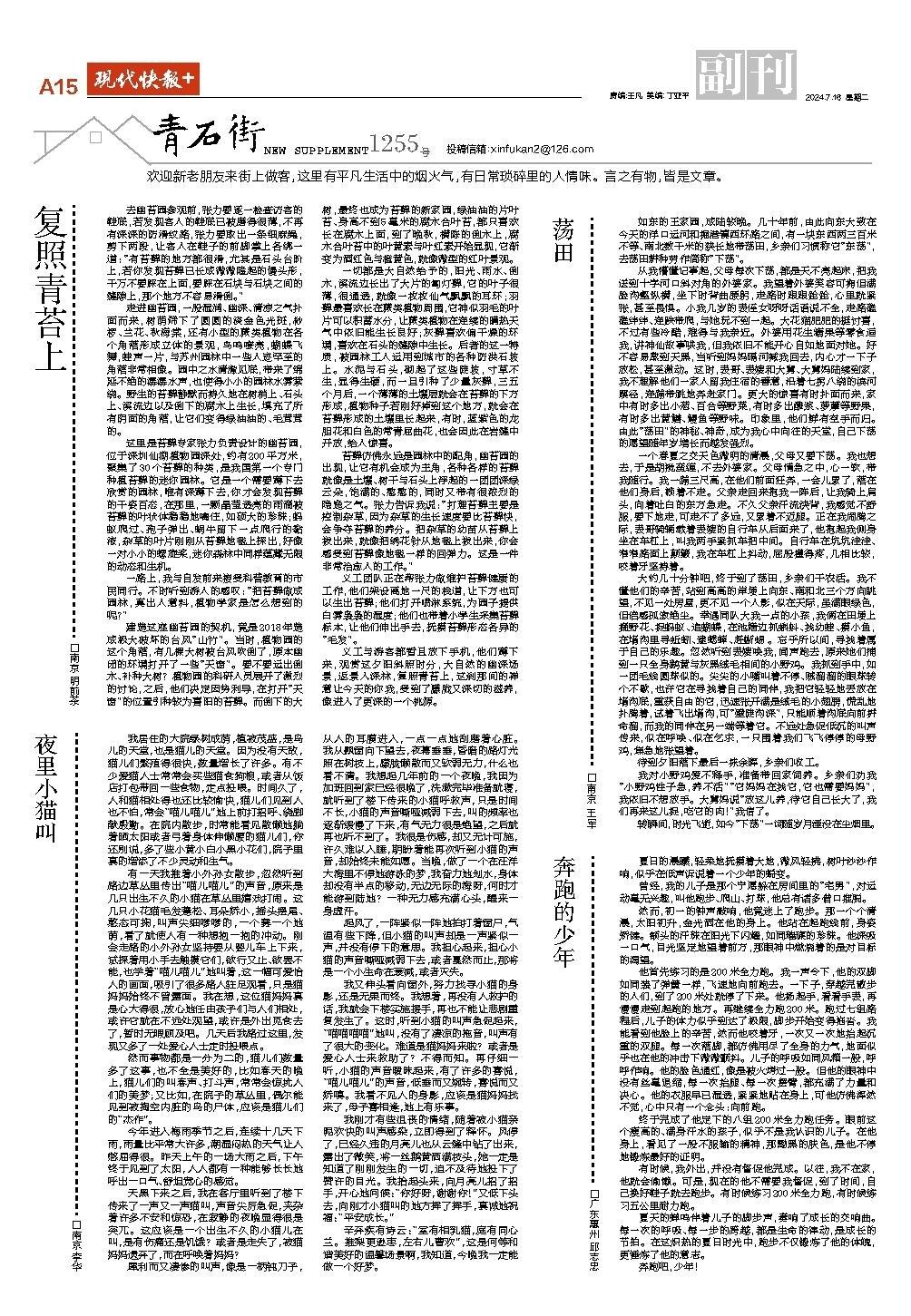□南京 王军
如东的王家园,成陆较晚。几十年前,由此向东大致在今天的洋口运河和掘港镇西环路之间,有一块东西两三百米不等、南北数千米的狭长地带荡田,乡亲们习惯称它“东荡”,去荡田耕种劳作简称“下荡”。
从我懵懂记事起,父母每次下荡,都是天不亮起床,把我送到十字河口斜对角的外婆家。我望着外婆笑容可掬但满脸沟壑纵横,坐下时背曲腰躬,走路时踉踉跄跄,心里就紧张,甚至畏惧。小我几岁的表侄女呀呀话语说不全,走路磕磕绊绊、连跌带爬,与她玩不到一起。大花猫肥肥的挺讨喜,不过有些冷酷,难得与我亲近。外婆用花生糖果等零食逗我,讲神仙故事哄我,但我依旧不能开心自如地面对她。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当听到妈妈隔河喊我回去,内心才一下子放松,甚至激动。这时,表哥、表嫂和大舅、大舅妈陆续到家,我不理解他们一家人留我住宿的善意,沿着七拐八绕的滨河蹊径,连蹦带跳地奔赴家门。更大的惊喜有时扑面而来,家中有时多出小葱、百合等野菜,有时多出酸浆、萝藦等野果,有时多出黄鳝、鳗鱼等野味。印象里,他们鲜有空手而归。由此“荡田”的神秘、神奇,成为我心中向往的天堂,自己下荡的愿望随年岁增长而越发强烈。
一个春夏之交天色微明的清晨,父母又要下荡。我也想去,于是胡搅蛮缠,不去外婆家。父母情急之中,心一软,带我随行。我一蹦三尺高,在他们前面狂奔,一会儿累了,落在他们身后,赖着不走。父亲走回来抱我一阵后,让我骑上肩头,向着吐白的东方急走。不久父亲汗流浃背,我感觉不舒服,要下地走,可走不了多远,又累着不迈腿。正在我闹腾之际,表哥骑辆载着表嫂的自行车从后面来了,他抱起我侧身坐在车杠上,叫我两手紧抓车把中间。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窄窄路面上颠簸,我在车杠上抖动,屁股撞得疼,几相比较,咬着牙坚持着。
大约几十分钟吧,终于到了荡田,乡亲们干农活。我不懂他们的辛苦,站到高高的岸埂上向东、南和北三个方向眺望,不见一处房屋,更不见一个人影,似在天际,虽满眼绿色,但倍感孤寂绝尘。幸遇同队大我一点的小孩,我俩在田埂上摘野花、捉蚂蚁、追蝴蝶,在池塘边抓蝌蚪、找幼蛙、摸小鱼,在墒沟里寻蚯蚓、逮蟋蟀、赶蜥蜴 。忘乎所以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乐趣。忽然听到表嫂唤我,闻声跑去,原来她们捕到一只全身鹅黄与灰黑绒毛相间的小野鸡。我抓到手中,如一团毛线圆球似的。尖尖的小嘴叫着不停、贼溜溜的眼球转个不歇,也许它在寻找着自己的同伴,我把它轻轻地丟放在墒沟底,重获自由的它,迅速张开满是绒毛的小翅膀,慌乱地扑腾着,试着飞出墒沟,可“壁陡沟深”,只能顺着沟底向前拼命溜,而我的同伴在另一端等着它。不远处急促低沉的叫声传来,似在呼唤、似在乞求,一只围着我们飞飞停停的母野鸡,焦急地张望着。
待到夕阳落下最后一抹余晖,乡亲们收工。
我对小野鸡爱不释手,准备带回家饲养。乡亲们劝我“小野鸡性子急,养不活”“它妈妈在找它,它也需要妈妈”,我依旧不想放手。大舅妈说“放这儿养,待它自己长大了,我们再来这儿捉,吃它的肉!”我信了。
转瞬间,时光飞逝,如今“下荡”一词随岁月湮没在尘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