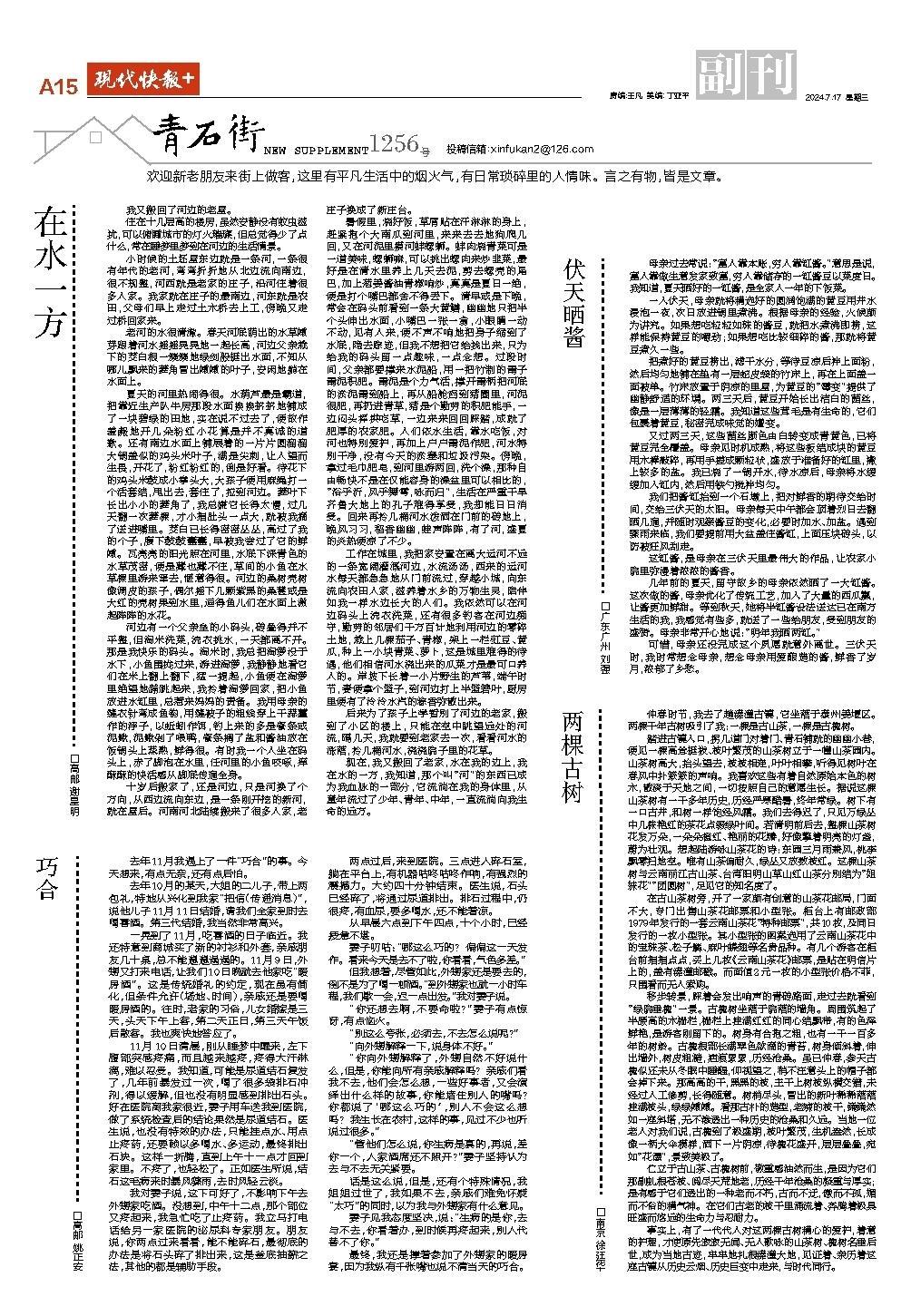□高邮 谢星明
我又搬回了河边的老屋。
住在十几层高的楼房,虽然安静没有蚊虫滋扰,可以俯瞰城市的灯火璀璨,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常在睡梦里梦到在河边的生活情景。
小时候的土坯屋东边就是一条河,一条很有年代的老河,弯弯折折地从北边流向南边,很不规整,河西就是老家的庄子,沿河住着很多人家。我家就在庄子的最南边,河东就是农田,父母们早上走过土木桥去上工,傍晚又走过桥回家来。
老河的水很清澈。春天河底萌出的水草嫩芽跟着河水摇摇晃晃地一起长高,河边父亲栽下的茭白根一簇簇地绿剑般挺出水面,不知从哪儿飘来的菱角冒出嫩嫩的叶子,安闲地躺在水面上。
夏天的河里热闹得很。水葫芦最是霸道,把靠近生产队牛房那段水面挨挨挤挤地铺成了一块碧绿的田地,实在说不过去了,便故作羞赧地开几朵粉红小花算是并不真诚的道歉。还有南边水面上铺展着的一片片圆溜溜大锅盖似的鸡头米叶子,满是尖刺,让人望而生畏,开花了,粉红粉红的,倒是好看。待花下的鸡头米鼓成小拳头大,大孩子便用麻绳打一个活套结,甩出去,套住了,拉到河边。菱叶下长出小小的菱角了,我总嫌它长得太慢,过几天翻一次菱棵,才小指肚头一点大,就被我摘了送进嘴里。茭白已长得密密丛丛,高过了我的个子,腹下鼓鼓囊囊,早被我尝过了它的鲜嫩。瓦亮亮的阳光照在河里,水底下深青色的水草茂密,便是藏也藏不住,草间的小鱼在水草棵里游来窜去,惬意得很。河边的桑树壳树像调皮的孩子,偶尔摇下几颗紫黑的桑葚或是大红的壳树果到水里,逗得鱼儿们在水面上激起阵阵的水花。
河边有一个父亲垒的小码头,砖叠得并不平整,但淘米洗菜,浣衣挑水,一天都离不开。那是我快乐的码头。淘米时,我总把淘箩没于水下,小鱼围拢过来,游进淘箩,我静静地看它们在米上翻上翻下,猛一提起,小鱼便在淘箩里绝望地蹦跳起来,我拎着淘箩回家,把小鱼放进水缸里,总惹来妈妈的责备。我用母亲的缝衣针弯成鱼钩,用缝被子的粗线穿上干蒜薹作的浮子,以蚯蚓作饵,钓上来的多是餐条或泥鳅,泥鳅剁了喂鸭,餐条搁了盐和酱油放在饭锅头上蒸熟,鲜得很。有时我一个人坐在码头上,赤了脚泡在水里,任河里的小鱼咬啄,痒酥酥的快活感从脚底传遍全身。
十岁后搬家了,还是河边,只是河换了个方向,从西边流向东边,是一条刚开挖的新河,就在屋后。河南河北陆续搬来了很多人家,老庄子换成了新庄台。
暑假里,烧好饭,草屑贴在汗淋淋的身上,赶紧抱个大南瓜到河里,来来去去地狗爬几回,又在河泥里摸河蚌螺蛳。蚌肉烧青菜可是一道美味,螺蛳嘛,可以挑出螺肉来炒韭菜,最好是在清水里养上几天去泥,剪去螺壳的尾巴,加上葱姜酱油青椒响炒,真真是夏日一绝,便是打个嘴巴都舍不得丢下。清早或是下晚,常会在码头前看到一条大黄鳝,幽幽地只把半个头伸出水面,小嘴巴一张一翕,小眼睛一动不动,见有人来,便不声不响地把身子缩到了水底,隐去踪迹,但我不想把它给找出来,只为给我的码头留一点趣味,一点念想。过段时间,父亲都要撑来水泥船,用一把竹制的罱子罱泥积肥。罱泥是个力气活,撑开罱柄把河底的淤泥罱到船上,再从船舱舀到猪圈里,河泥很肥,再扔进青草,猪是个勤劳的积肥能手,一边闷头挥拱吃草,一边来来回回踩踏,成就了肥厚的农家肥。人们依水生活,靠水吃饭,对河也特别爱护,再加上户户罱泥作肥,河水特别干净,没有今天的淤塞和垃圾污染。傍晚,拿过毛巾肥皂,到河里游两回,洗个澡,那种自由畅快不是在仅能容身的澡盆里可以相比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生活在严重干旱齐鲁大地上的孔子难得享受,我却能日日消受。回来再拎几桶河水泼洒在门前的砖地上,晚风习习,稻香幽幽,蛙声阵阵,有了河,盛夏的炎热便凉了不少。
工作在城里,我把家安置在离大运河不远的一条宽阔灌溉河边,水流汤汤,西来的运河水每天都急急地从门前流过,穿越小城,向东流向农田人家,滋养着水乡的万物生灵,陪伴如我一样水边长大的人们。我依然可以在河边码头上浣衣洗菜,还有很多钓客在河边痴守,勤劳的邻居们千方百计地利用河边的零碎土地,栽上几棵茄子、青椒,架上一栏豇豆、黄瓜,种上一小块青菜、萝卜,这是城里难得的待遇,他们相信河水浇出来的瓜菜才是最可口养人的。岸坡下长着一小片野生的芦苇,端午时节,妻便拿个篮子,到河边打上半篮箬叶,厨房里便有了泠泠水汽的粽香弥散出来。
后来为了孩子上学暂别了河边的老家,搬到了小区的楼上,只能在空中眺望远处的河流,隔几天,我就要到老家去一次,看看河水的涨落,拎几桶河水,浇浇院子里的花草。
现在,我又搬回了老家,水在我的边上,我在水的一方,我知道,那个叫“河”的东西已成为我血脉的一部分,它流淌在我的身体里,从童年流过了少年、青年、中年,一直流淌向我生命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