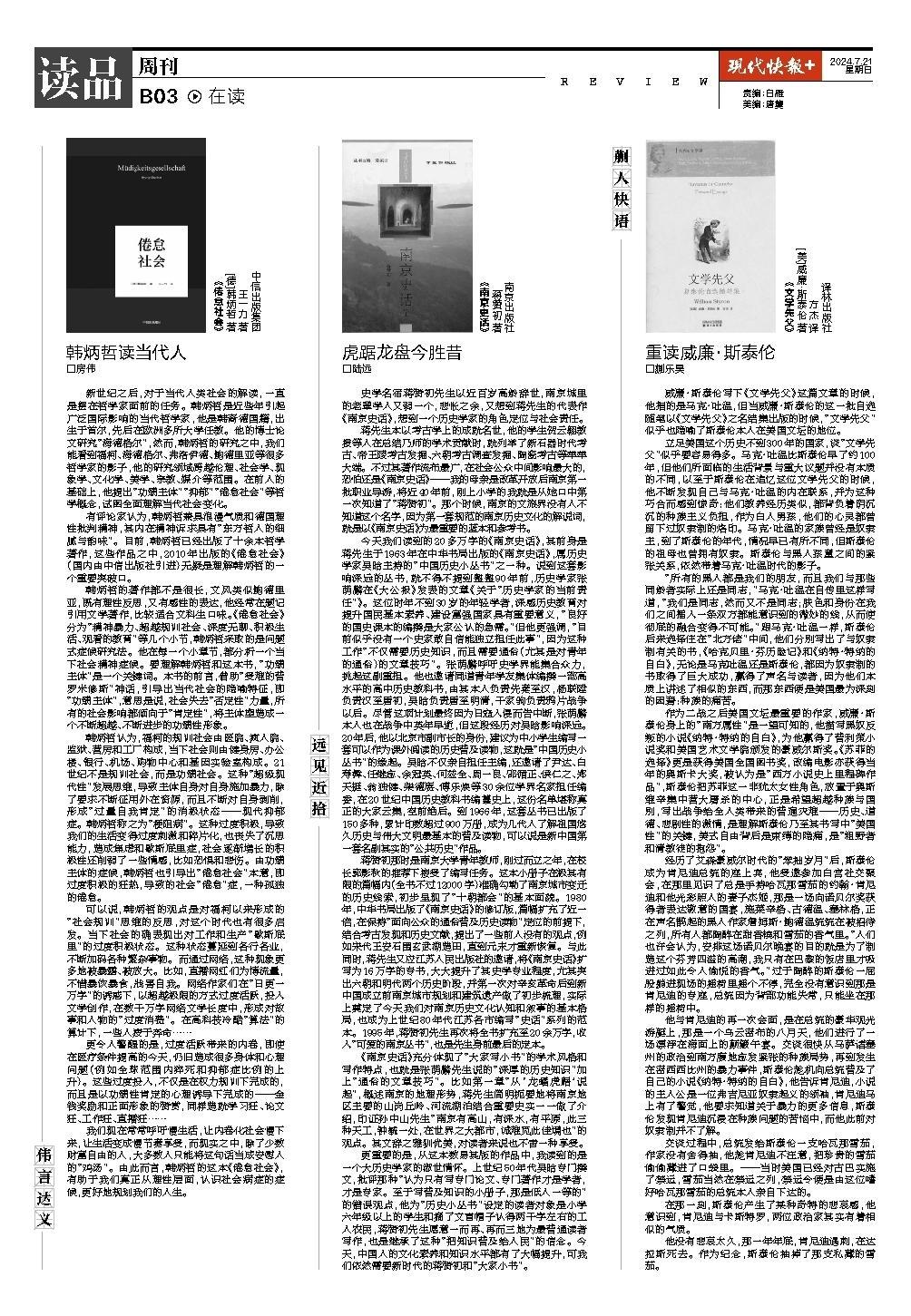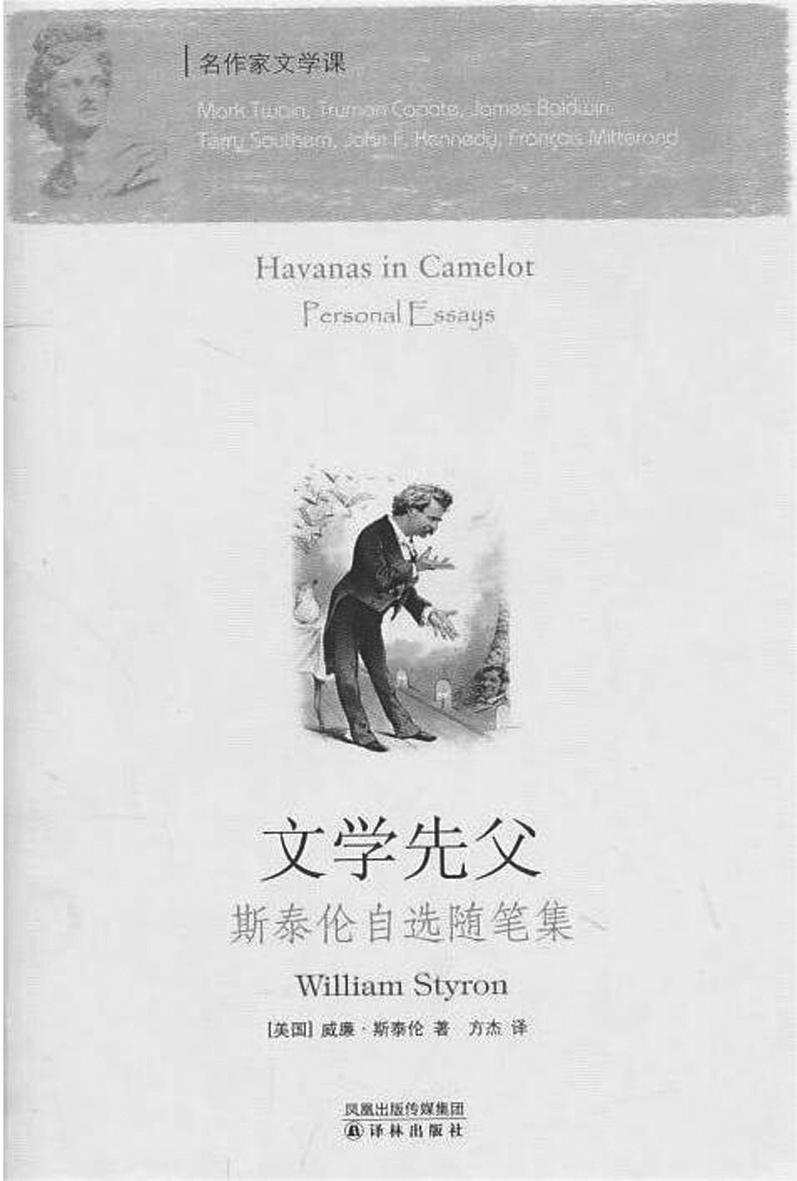□蒯乐昊
威廉·斯泰伦写下《文学先父》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指的是马克·吐温,但当威廉·斯泰伦的这一批自选随笔以《文学先父》之名结集出版的时候,“文学先父”似乎也隐喻了斯泰伦本人在美国文坛的地位。
立足美国这个历史不到300年的国家,谈“文学先父”似乎要容易得多。马克·吐温比斯泰伦早了约100年,但他们所面临的生活背景与重大议题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以至于斯泰伦在追忆这位文学先父的时候,他不断发现自己与马克·吐温的内在联系,并为这种巧合而感到惊奇:他们教养经历类似,都背负着阴沉沉的种族主义负担,作为白人男孩,他们的心灵都曾留下过奴隶制的烙印。马克·吐温的家族曾经是奴隶主,到了斯泰伦的年代,情况早已有所不同,但斯泰伦的祖母也曾拥有奴隶。斯泰伦与黑人孩童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带着马克·吐温时代的影子。
“所有的黑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我们与那些同龄者实际上还是同志,”马克·吐温在自传里这样写道,“我们是同志,然而又不是同志;肤色和身份在我们之间插入一条双方都能意识到的微妙的线,从而使彻底的融合变得不可能。”跟马克·吐温一样,斯泰伦后来选择住在“北方佬”中间,他们分别写出了与奴隶制有关的书,《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纳特·特纳的自白》,无论是马克吐温还是斯泰伦,都因为奴隶制的书取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声名与读者,因为他们本质上讲述了相似的东西,而那东西便是美国最为深刻的困窘:种族的痛苦。
作为二战之后美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威廉·斯泰伦身上的“南方属性”是一望可知的,他描写黑奴反叛的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豪威尔斯奖。《苏菲的选择》更是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改编电影亦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大奖,被认为是“西方小说史上里程碑作品”,斯泰伦把苏菲这一非犹太女性角色,放置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中心,正是希望超越种族与国别,写出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普遍灾难——历史、道德、悲剧性的激情,是理解斯泰伦乃至其书写中“美国性”的关键,美式自由背后是束缚的隐痛,是“粗野者和清教徒的抱怨”。
经历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笨拙岁月”后,斯泰伦成为肯尼迪总统的座上宾,他受邀参加白宫社交聚会,在那里见识了总是手持哈瓦那雪茄的约翰·肯尼迪和他光彩照人的妻子杰姬,那是一场向诺贝尔奖获得者表达敬意的国宴,施莱辛格、古德温、塞林格,正在声名鹊起的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统统在被招待之列,所有人都陶醉在甜香槟和雪茄的香气里。“人们也许会认为,安排这场诺贝尔晚宴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这个芬芳四溢的高潮,我只有在巴黎的饭店里才吸进过如此令人愉悦的香气。”过于陶醉的斯泰伦一屁股躺进现场的摇椅里摇个不停,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肯尼迪的专座,总统因为背部功能失常,只能坐在那样的摇椅中。
他与肯尼迪的再一次会面,是在总统的豪华观光游艇上,那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八月天,他们进行了一场漂浮在海面上的颠簸午宴。交谈很快从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到南方腹地愈发紧张的种族局势,再到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暴力事件,斯泰伦趁机向总统普及了自己的小说《纳特·特纳的自白》,他告诉肯尼迪,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弗吉尼亚奴隶起义的领袖,肯尼迪马上有了警觉,他要求知道关于暴力的更多信息,斯泰伦发现肯尼迪沉浸在种族问题的苦恼中,而他此前对奴隶制并不了解。
交谈过程中,总统发给斯泰伦一支哈瓦那雪茄,作家没有舍得抽,他趁肯尼迪不注意,把珍贵的雪茄偷偷藏进了口袋里。——当时美国已经对古巴实施了禁运,雪茄当然在禁运之列,禁运令便是由这位嗜好哈瓦那雪茄的总统本人亲自下达的。
在那一刻,斯泰伦产生了某种奇特的悲哀感,他意识到,肯尼迪与卡斯特罗,两位政治家其实有着相似的气质。
他没有悲哀太久,那一年年底,肯尼迪遇刺,在达拉斯死去。作为纪念,斯泰伦抽掉了那支私藏的雪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