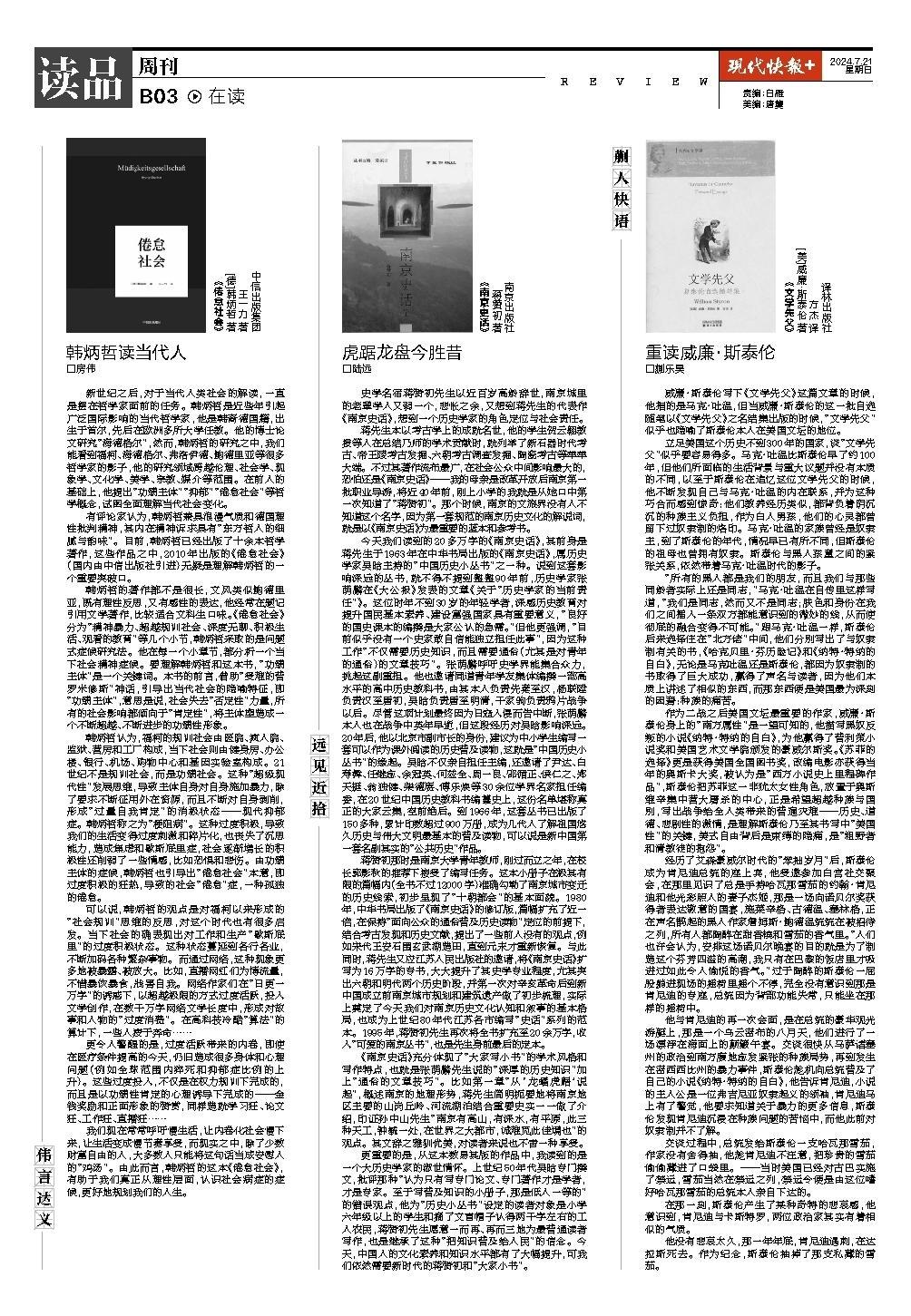□陆远
史学名宿蒋赞初先生以近百岁高龄辞世,南京城里的老辈学人又弱一个,悲怅之余,又想到蒋先生的代表作《南京史话》,想到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定位与社会责任。
蒋先生本以考古学上的成就名世,他的学生贺云翱教授等人在总结乃师的学术贡献时,就列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帝王陵考古发掘、六朝考古调查发掘、陶瓷考古等荦荦大端。不过其著作流布最广,在社会公众中间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南京史话》——我的母亲是改革开放后南京第一批职业导游,将近40年前,刚上小学的我就是从她口中第一次知道了“蒋赞初”。那个时候,南京的文旅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第一套规范的南京历史文化的解说词,就是以《南京史话》为最重要的蓝本和参考书。
今天我们读到的20多万字的《南京史话》,其前身是蒋先生于196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南京史话》,属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种。说到这套影响深远的丛书,就不得不提到整整90年前,历史学家张荫麟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这位时年不到30岁的年轻学者,深感历史教育对提升国民基本素养、建设富强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国史课本的编撰是大家公认的急需。”但他更强调,“目前似乎没有一个史家敢自信能独立担任此事”,因为这种工作“不仅需要历史知识,而且需要通俗(尤其是对青年的通俗)的文章技巧”。张荫麟呼吁史学界能集合众力,挑起这副重担。他也邀请同道青年学友集体编撰一部高水平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由其本人负责先秦至汉,杨联陞负责汉至唐初,吴晗负责唐至明清,千家驹负责鸦片战争以后。尽管这项计划最终因为日寇入侵而告中断,张荫麟本人也在战争中英年早逝,但这段经历对吴晗影响深远。20年后,他以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建议为中小学生编写一套可以作为课外阅读的历史普及读物,这就是“中国历史小丛书”的缘起。吴晗不仅亲自担任主编,还邀请了尹达、白寿彝、任继愈、余冠英、何兹全、周一良、邵循正、侯仁之、郑天挺、翁独健、柴德赓、傅乐焕等30余位学界名家担任编委,在20世纪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史上,这份名单堪称真正的大家云集,空前绝后。到1966年,这套丛书已出版了150多种,累计印数超过900万册,成为几代人了解祖国悠久历史与伟大文明最基本的普及读物,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套名副其实的“公共历史”作品。
蒋赞初那时是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刚过而立之年,在校长郭影秋的推荐下接受了编写任务。这本小册子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全书不过12000字)准确勾勒了南京城市变迁的历史线索,初步呈现了“十朝都会”的基本面貌。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南京史话》的修订版,篇幅扩充了近一倍,在保持“面向公众的通俗普及历史读物”定位的前提下,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提出了一些前人没有的观点,例如宋代王安石围玄武湖造田,直到元末才重新恢复。与此同时,蒋先生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将《南京史话》扩写为16万字的专书,大大提升了其史学专业程度,尤其突出六朝和明代两个历史阶段,并第一次对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城市规划和建筑遗产做了初步梳理,实际上奠定了今天我们对南京历史文化认知和叙事的基本格局,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江苏各市编写“史话”系列的范本。1995年,蒋赞初先生再次将全书扩充至20余万字,收入“可爱的南京丛书”,也是先生身前最后的定本。
《南京史话》充分体现了“大家写小书”的学术风格和写作特点,也就是张荫麟先生说的“深厚的历史知识”加上“通俗的文章技巧”。比如第一章“从‘龙蟠虎踞’说起”,概述南京的地理形势,蒋先生简明扼要地将南京地区主要的山岗丘岭、河流湖泊结合重要史实一一做了介绍,印证孙中山先生“南京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的观点。其文辞之雅驯优美,对读者来说也不啻一种享受。
更重要的是,从这本数易其版的作品中,我读到的是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淑世情怀。上世纪50年代吴晗专门撰文,批评那种“认为只有写专门论文、专门著作才是学者,才是专家。至于写普及知识的小册子,那是低人一等的”的错误观点,他为“历史小丛书”设定的读者对象是小学六年级以上的学生和摘了文盲帽子认得两千字左右的工人农民,蒋赞初先生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最普通读者写作,也是继承了这种“把知识普及给人民”的信念。今天,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可我们依然需要新时代的蒋赞初和“大家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