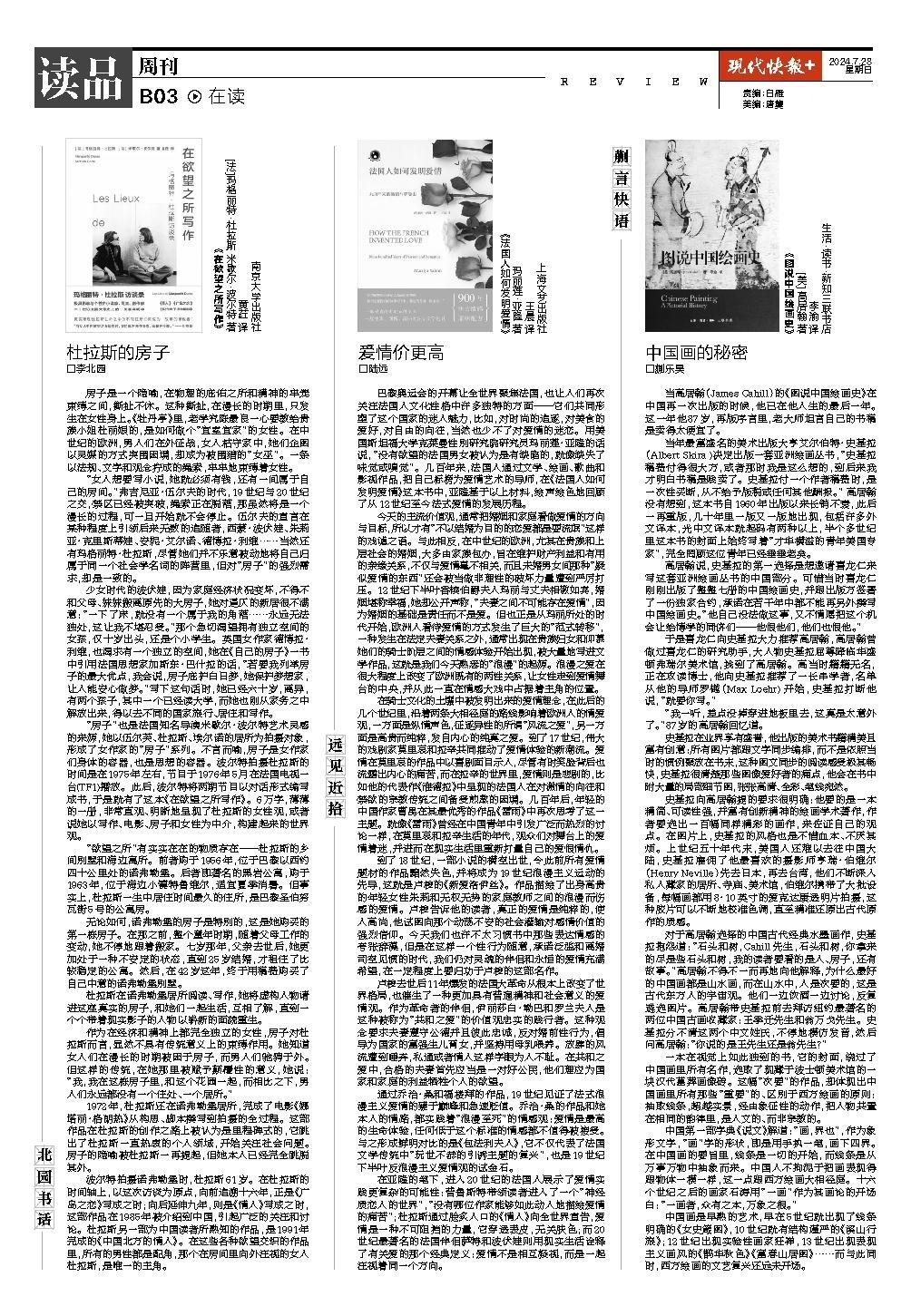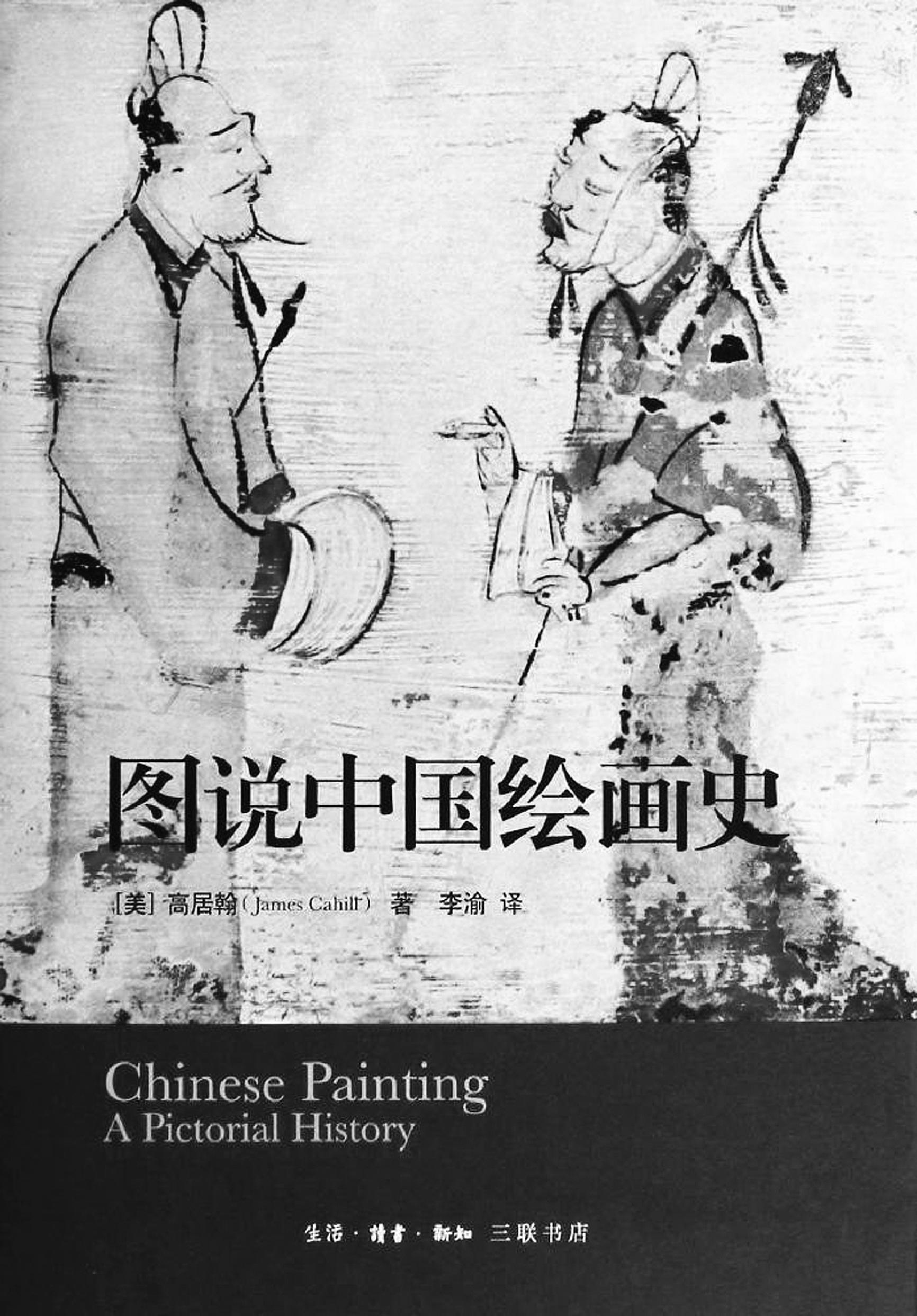□蒯乐昊
当高居翰(James Cahill)的《图说中国绘画史》在中国再一次出版的时候,他已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87岁,再版序言里,老大师坦言自己的书稿是卖得太便宜了。
当年最富盛名的美术出版大亨艾尔伯特·史基拉(Albert Skira )决定出版一套亚洲绘画丛书,“史基拉稿费付得很大方,或者那时我是这么想的,到后来我才明白书稿是贱卖了。史基拉付一个作者稿费时,是一次性买断,从不给予版税或任何其他酬报。” 高居翰没有想到,这本书自1960年出版以来长销不衰,此后一再重版,几十年里一版又一版地出现,包括许多外文译本,光中文译本就起码有两种以上,半个多世纪里这本书的封面上始终写着“才华横溢的青年美国专家”,完全罔顾这位青年已经垂垂老矣。
高居翰说,史基拉的第一选择是想邀请喜龙仁来写这套亚洲绘画丛书的中国部分。可惜当时喜龙仁刚刚出版了整整七册的中国绘画史,并跟出版方签署了一份独家合约,承诺在若干年中都不能再另外撰写中国绘画史。“他自己没法做这事,又不情愿把这个机会让给博学的同侪们——他恨他们,他们也恨他。”
于是喜龙仁向史基拉大力推荐高居翰,高居翰曾做过喜龙仁的研究助手,大人物史基拉屈尊降临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找到了高居翰。高当时籍籍无名,正在攻读博士,他向史基拉推荐了一长串学者,名单从他的导师罗樾(Max Loehr) 开始,史基拉打断他说,“就要你写。”
“我一听,差点没掉穿进地板里去,这真是太意外了。”87岁的高居翰回忆道。
史基拉在业界享有盛誉,他出版的美术书籍精美且富有创意:所有图片都跟文字同步编排,而不是依照当时的惯例聚放在书末,这种图文同步的阅读感受极其畅快,史基拉很清楚那些图像爱好者的痛点,他会在书中附大量的局部细节图,张张高清、全彩、笔线宛然。
史基拉向高居翰提的要求很明确:他要的是一本精简、可读性强,并富有创新精神的绘画学术著作,作者要选出一百幅同样精彩的画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图片上,史基拉的风格也是不惜血本、不厌其烦。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人还难以去往中国大陆,史基拉雇佣了他最喜欢的摄影师亨瑞·伯维尔(Henry Neville)先去日本,再去台湾,他们不断深入私人藏家的居所、寺庙、美术馆,伯维尔携带了大批设备,每幅画都用8·10英寸的爱克达康透明片拍摄,这种胶片可以不断地校准色调,直至精准还原出古代原作的质感。
对于高居翰选择的中国古代经典水墨画作,史基拉抱怨道:“石头和树,Cahill先生,石头和树,你拿来的尽是些石头和树,我的读者要看的是人、房子,还有故事。”高居翰不得不一而再地向他解释,为什么最好的中国画都是山水画,而在山水中,人是次要的,这是古代东方人的宇宙观。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讨论,反复遴选图片。高居翰带史基拉前去拜访纽约最著名的两位中国古画收藏家:王季迁先生和翁万戈先生。史基拉分不清这两个中文姓氏,不停地模仿发音,然后问高居翰:“你说的是王先生还是翁先生?”
一本在视觉上如此独到的书,它的封面,绕过了中国画里所有名作,选取了现藏于波士顿美术馆的一块汉代墓葬画像砖。这幅“次要”的作品,却体现出中国画里所有那些“重要”的、区别于西方绘画的原则:抽取线条,超越实景,经由象征性的动作,把人物共置在相同的韵律里,是人文的、而非宗教的。
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道:“画,界也”,作为象形文字,“画”字的形状,即是用手执一笔,画下四界。在中国画的要旨里,线条是一切的开始,而线条是从万事万物中抽象而来。中国人不拘泥于把画表现得跟物体一模一样,这一点跟西方绘画大相径庭。十六个世纪之后的画家石涛用“一画”作为其画论的开场白:“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
中国画是早熟的艺术,早在5世纪就出现了线条明确的《女史箴图》,10世纪就有结构谨严的《溪山行旅》;12世纪出现实验性画家狂禅,13世纪出现表现主义画风的《鹊华秋色》《富春山居图》……而与此同时,西方绘画的文艺复兴还远未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