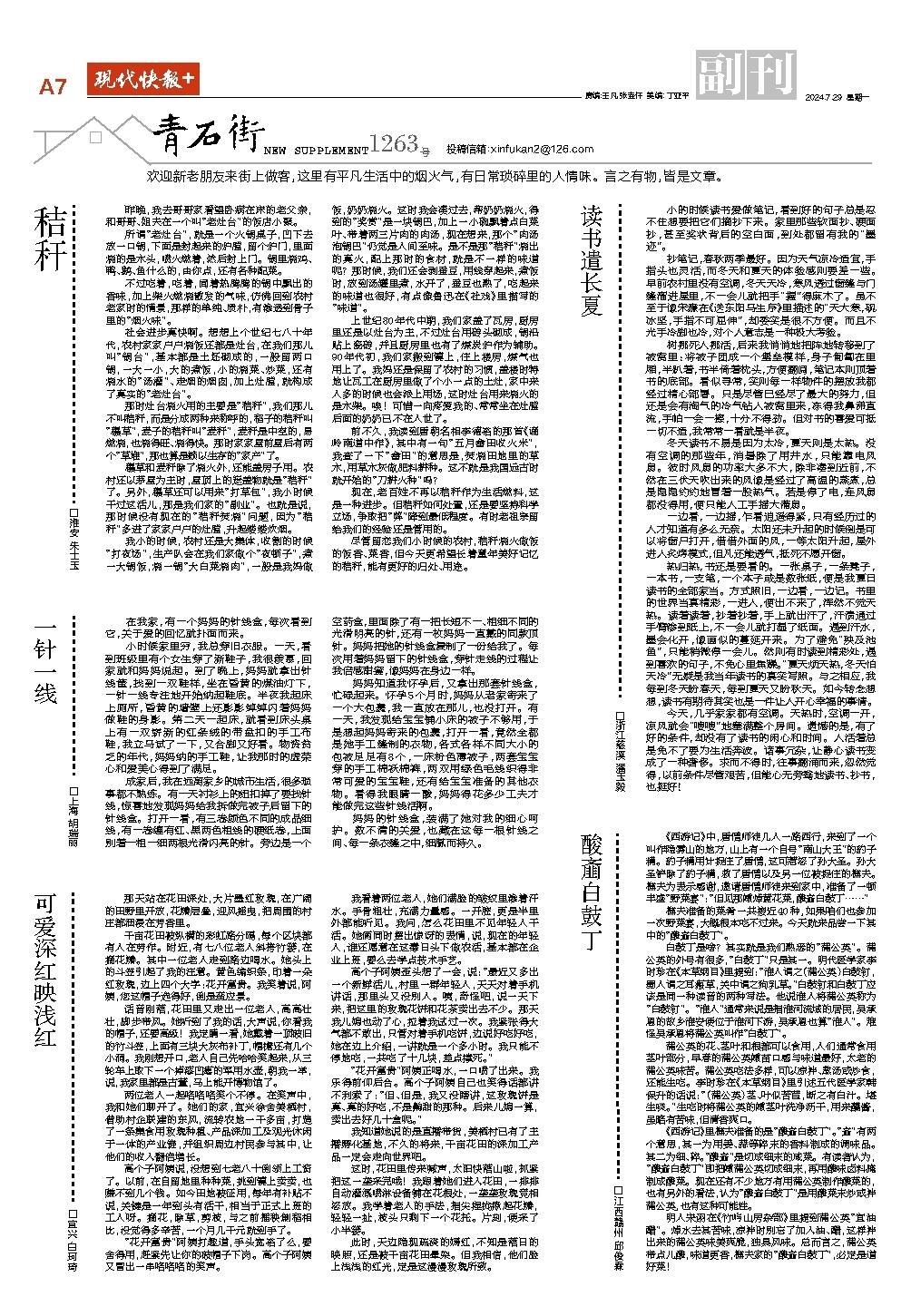□淮安 朱士玉
昨晚,我去哥哥家看望卧病在床的老父亲,和哥哥、姐夫在一个叫“老灶台”的饭店小聚。
所谓“老灶台”,就是一个火锅桌子,凹下去放一口锅,下面是封起来的炉膛,留个炉门,里面烧的是木头,喷火燃着,然后封上门。锅里烧鸡、鸭、鹅、鱼什么的,由你点,还有各种配菜。
不过吃着,吃着,闻着热腾腾的锅中飘出的香味,加上柴火燃烧散发的气味,仿佛回到农村老家时的情景,那样的单纯、质朴,有渗透到骨子里的“烟火味”。
社会进步真快啊。想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家家户户烧饭还都是灶台,在我们那儿叫“锅台”,基本都是土坯砌成的,一般留两口锅,一大一小,大的煮饭,小的烧菜、炒菜,还有烧水的“汤灌”、走烟的烟囱,加上灶膛,就构成了真实的“老灶台”。
那时灶台烧火用的主要是“秸秆”,我们那儿不叫秸秆,而是分成两种来称呼的,稻子的秸秆叫“穰草”,麦子的秸秆叫“麦秆”,麦秆是中空的,易燃烧,也烧得旺、烧得快。那时家家屋前屋后有两个“草堆”,那也算是赖以生存的“家产”了。
穰草和麦秆除了烧火外,还能盖房子用。农村还以茅屋为主时,屋顶上的遮盖物就是“秸秆”了。另外,穰草还可以用来“打草包”,我小时候干过这活儿,那是我们家的“副业”。也就是说,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秸秆焚烧”问题,因为“秸秆”多进了家家户户的灶膛,升起缕缕炊烟。
我小的时候,农村还是大集体,收割的时候“打夜场”,生产队会在我们家做个“夜顿子”,煮一大锅饭,烧一锅“大白菜烧肉”,一般是我妈做饭,奶奶烧火。这时我会凑过去,帮奶奶烧火,得到的“奖赏”是一块锅巴,加上一小碗飘着点白菜叶、带着两三片肉的肉汤,现在想来,那个“肉汤泡锅巴”仍觉是人间至味。是不是那“秸秆”烧出的真火,配上那时的食材,就是不一样的味道呢?那时候,我们还会剥蚕豆,用线穿起来,煮饭时,放到汤罐里煮,水开了,蚕豆也熟了,吃起来的味道也很好,有点像鲁迅在《社戏》里描写的“味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家盖了瓦房,厨房里还是以灶台为主,不过灶台用砖头砌成,锅沿贴上瓷砖,并且厨房里也有了煤炭炉作为辅助。90年代初,我们家搬到镇上,住上楼房,煤气也用上了。我妈还是保留了农村的习惯,盖楼时特地让瓦工在厨房里做了个小一点的土灶,家中来人多的时候也会派上用场,这时灶台用来烧火的是木柴。唉!可惜一向疼爱我的、常常坐在灶膛后面的奶奶已不在人世了。
前不久,我读到唐朝名相李德裕的那首《谪岭南道中作》,其中有一句“五月畬田收火米”,我查了一下“畬田”的意思是,焚烧田地里的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耕种。这不就是我国远古时就开始的“刀耕火种”吗?
现在,老百姓不再以秸秆作为生活燃料,这是一种进步。但秸秆如何处置,还是要坚持科学立场,争取把“弊”降到最低程度。有时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经验还是管用的。
尽管留恋我们小时候的农村,秸秆烧火做饭的饭香、菜香,但今天更希望长着童年美好记忆的秸秆,能有更好的归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