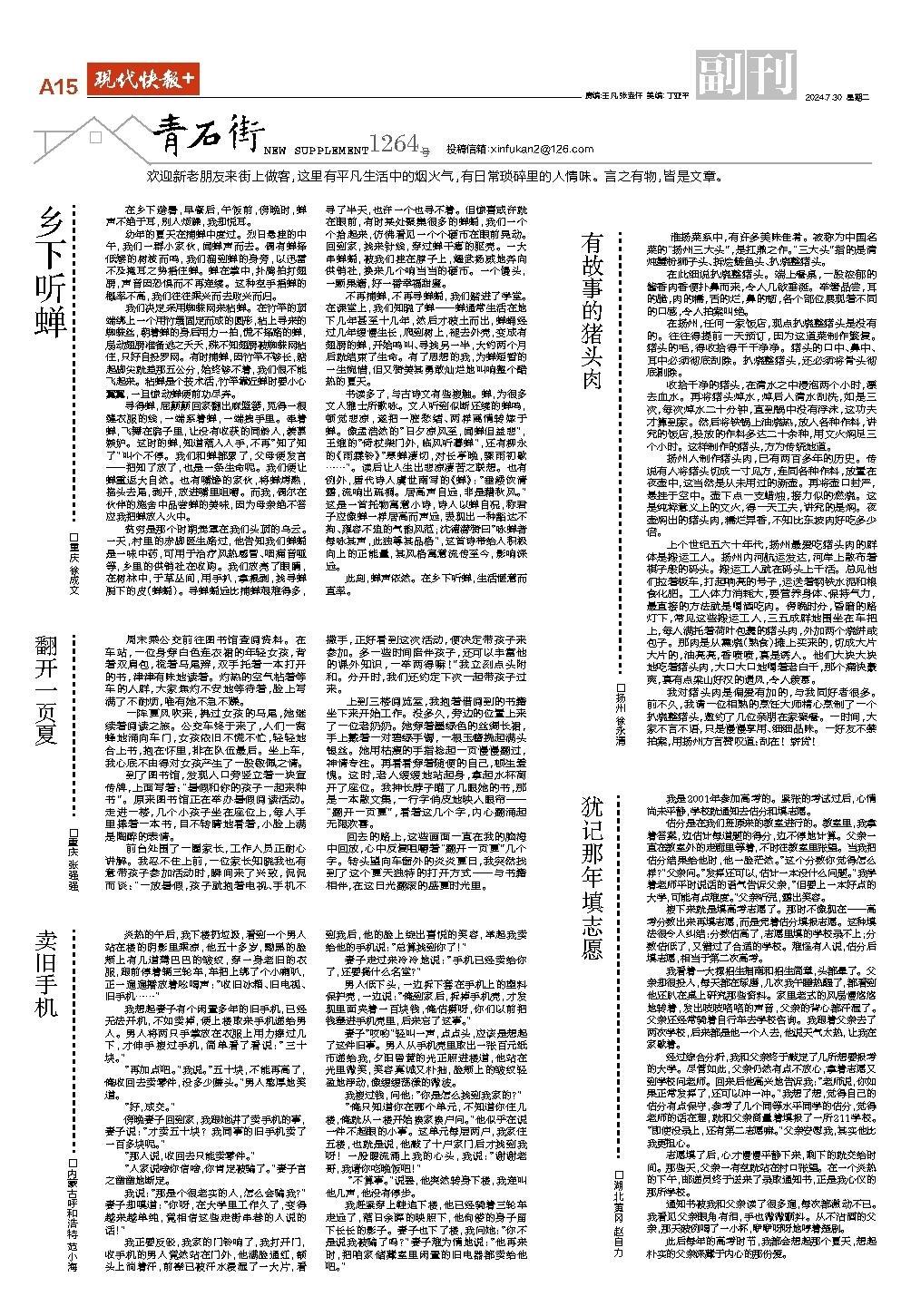□湖北黄冈 赵自力
我是2001年参加高考的。紧张的考试过后,心情尚未平静,学校就通知去估分和填志愿。
估分是在我们班原来的教室进行的。教室里,我拿着答案,边估计每道题的得分,边不停地计算。父亲一直在教室外的走廊里等着,不时往教室里张望。当我把估分结果给他时,他一脸茫然。“这个分数你觉得怎么样?”父亲问。“发挥还可以,估计一本没什么问题。”我学着老师平时说话的语气告诉父亲,“但要上一本好点的大学,可能有点难度。”父亲听完,露出笑容。
接下来就是填高考志愿了。那时不像现在——高考分数出来再填志愿,而是凭着估分填报志愿。这种填法很令人纠结:分数估高了,志愿里填的学校录不上;分数估低了,又错过了合适的学校。难怪有人说,估分后填志愿,相当于第二次高考。
我看着一大摞招生指南和招生简章,头都晕了。父亲却很投入,每天都在琢磨,几次我午睡热醒了,都看到他还趴在桌上研究那些资料。家里老式的风扇慢悠悠地转着,发出吱吱咯咯的声音,父亲的背心都汗湿了。父亲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学校咨询。我跟着父亲去了两次学校,后来都是他一个人去,他说天气太热,让我在家歇着。
经过综合分析,我和父亲终于敲定了几所想要报考的大学。尽管如此,父亲仍然有点不放心,拿着志愿又到学校问老师。回来后他高兴地告诉我:“老师说,你如果正常发挥了,还可以冲一冲。”我想了想,觉得自己的估分有点保守,参考了几个同等水平同学的估分,觉得老师的话在理,就和父亲商量着填报了一所211学校。“即使没录上,还有第二志愿嘛。”父亲安慰我,其实他比我更担心。
志愿填了后,心才慢慢平静下来,剩下的就交给时间。那些天,父亲一有空就站在村口张望。在一个炎热的下午,邮递员终于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正是我心仪的那所学校。
通知书被我和父亲读了很多遍,每次都激动不已。我看见父亲眼角有泪,手也微微颤抖。从不沾酒的父亲,那天破例喝了一小杯,咿咿呀呀地哼着楚剧。
此后每年的高考时节,我都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朴实的父亲深藏于内心的那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