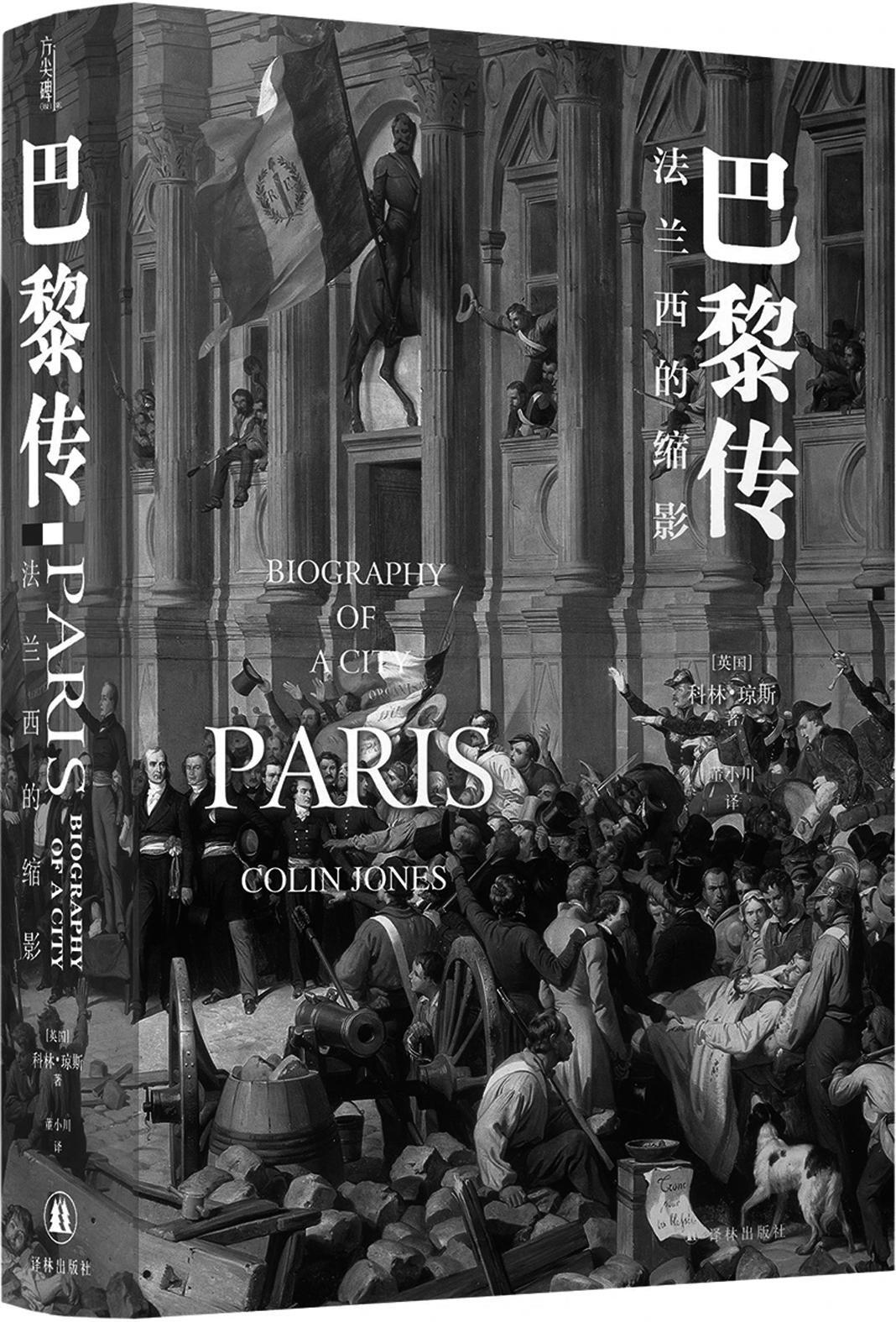“我们确信,即使是爱财如命的美国人也不想要它。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也都因为它而极度心烦——而我们的说法只是广大民众呼声中一个小小的回音,要知道,广大民众的呼声是很值得警觉的。人们只需想象一下,一座现代工厂里巨大的黑烟囱那样的铁塔主宰着巴黎,以其野蛮的块头压倒了圣母院、圣礼拜堂、圣雅克塔、卢浮宫、荣军院的穹顶、凯旋门等,埃菲尔铁塔简直不值一提。”
上面这段陈词是1887年由大约50位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后发出的,其中包括作家小仲马、勒贡特·德·列尔和莫泊桑,建筑师夏尔·加尼叶,作曲家古诺和马斯内,剧作家维克托里安·萨尔杜,以及许多建筑设计师。他们宣称自己是“美的激情热爱者”,自认为是所有喜爱历史上巴黎的人的代表,无法忍受巴黎将要被正在准备建立的那个“毫无价值的柱状形铁架那令人厌恶的阴影”所亵渎。
对于一个在所需的250万颗铆钉尚未有一颗敲定之前就受到法国文学和艺术大师们全面谴责的建筑,埃菲尔铁塔的质量惊人地好。负责铁塔建造的勃艮第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尽管它事实上是由他的同事努吉耶和凯什兰设计的——给那帮大师们写了一份激情似火的答复,声称他提出的这种新型美的建筑并没有违背艺术标准和历史惯例,而是超越了这两者。他指出:是因为埃及那些金字塔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才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吗?……埃菲尔铁塔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高大的建筑物,为什么金字塔在埃及具有令人钦佩的价值,而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却变成了丑陋与荒唐的话柄?
确实有些人十分讨厌埃菲尔铁塔。例如,J. M. 于斯曼攻击它是一个“毫无价值的蜡烛台”,一个“浑身是洞的固体栓剂”。但是埃菲尔同时代的人和后代子孙们纷纷来铁塔参观。铁塔落成于1889年博览会,仅这一年就有200万人参观该铁塔,其中包括威尔士王子、八位非洲国王、托马斯·爱迪生、莎拉·伯恩哈德和“水牛”比尔,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嘉宾跋涉1710个阶梯,来到300米高的铁塔顶端。巴黎春天百货公司独家获得了建塔所剩的边角余料,用来制造许多微型埃菲尔铁塔,作为纪念物卖给游客,结果使铁塔的形象遍布全法各地。到21世纪初,来埃菲尔铁塔参观的人数已经接近2亿人。
尽管毕沙罗是埃菲尔铁塔著名的坚决反对者,但法国大多数画家还是几乎立刻表示愿意来看看铁塔。例如,修拉早在1889年铁塔落成当年就来参观,1890年来参观的著名画家还有卢梭、希涅克,夏加尔、德罗内、郁特里罗、杜菲、谷克多等也步其后尘。诗人们也纷纷来访。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前线服务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创作了一首抗击德国的诗歌,用的就是埃菲尔铁塔式的排列方式。阿波利奈尔的姿态表明一个事实,即埃菲尔铁塔是巴黎城市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纪念物,巴黎所有著名的纪念场所也无一可以与之相比拟。在这方面,巴黎圣母院与埃菲尔铁塔十分相近,尽管巴黎圣母院的宗教功能使它超出了巴黎反教权主义的目标界限,但它事实上出自技艺精湛但默默无名的劳动者之手。埃菲尔本人将他的铁塔称为“300米高的旗杆”,三色旗在塔顶飘扬。埃菲尔铁塔的形象,从绘画、诗歌、图片、电影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都让人想起巴黎而非整个法国。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埃菲尔铁塔就是巴黎城市的化身。
埃菲尔铁塔超越了艺术标准,也超越了所有实用功能的概念。最终,人们发现了它的一些其他用途:1908年,人们在塔上竖起一根无线电杆,后来又建了一根电视信号杆;它的顶端还是军事观察点;它还被用来做巨大的广告板和气象观察站。然而,埃菲尔铁塔的这些实用功能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代替,因此,铁塔在这方面的所有意义和目的都不那么重要,它的工程设计本身就是它的最高成就。与埃菲尔铁塔同时期开放的英国福斯大桥也是如此,除了它本身在建筑史上的荣耀和地位外,这座桥至少还承担了从河口一岸到对岸的交通运输,所不同的是福斯大桥建筑过程中有大约100人死亡,而埃菲尔铁塔建筑工地仅有一人重伤。
作为一个出色的旅游景点,铁塔还超越了旅游行业的陈旧观念。铁塔最高明的评论家罗兰·巴特指出,游客在塔上无可探求,塔上一无所有,除了巴黎,事实上在塔上什么也看不到。人们在埃菲尔铁塔上不仅可以俯瞰巴黎全景,而且可以领略巴黎难得一见的空中轮廓。难怪莫泊桑在塔中餐馆用餐时说:“这里是巴黎唯一一个看不到铁塔的地方!”
大众媒体助力巴黎的体育运动
市场的发展使巴黎的艺术也商品化了,巴黎的艺术反过来又有助于巴黎本身形象的商业化,进而为广大民众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视觉享受。类似于1900年博览会那样繁茂的商业活动使巴黎给人留下了自力更生的印象,也向外界展示了现代化巴黎的特定景色,巴黎上下两层的知识分子以及放荡不羁的文人都赞同这种看法。有关印象派的论争已经在报纸上展开,这事实上使他们更加有知名度。在现代优雅生活方式商品化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增长的读写能力十分重要。1882年,巴黎开始实行小学义务教育,政府不仅自己投巨资建设学校,同时要求个人或天主教会投资办学,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使新闻媒体传播取得成功。到19世纪90年代,《巴黎小报》以其调查报道、犯罪故事、连载小说、名人事迹和插图而闻名,其发行量每日高达100万份。
大众媒体还在日益流行的体育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这是另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正是这种休闲娱乐形式使巴黎在世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1903年开始举办的环法自行车赛,起点和终点都在巴黎,该项赛事本来是一张名为“汽车”(L’ Auto)的体育报为增加发行量而做的尝试,没想到影响如此巨大。在巴黎举办体育赛事是使这种比赛最大限度地深入民众的可靠途径,同时也得到有关当局的支持。一年一度的巴黎—鲁昂自行车赛始于1869年,巴黎—布列斯特自行车赛始于1892年。随后,1894年开始举办了巴黎—鲁昂和巴黎—布列斯特汽车拉力赛,从1895年开始举办巴黎—波尔多—巴黎汽车拉力赛。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这些赛事十分盛行,同时也推动巴黎修建了一些知名的体育馆。第二帝国末期,朗尚、奥特尤尔、万塞讷的赛马场逐渐发展起来。另外,1910年修建的“冬季赛车场”承办了一些重要的自行车赛事。位于郊区的王子公园体育场和哥伦布体育场分别于1897年和1907年正式开放,举办团体运动项目。第二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00年在这个城市举办,各项赛事都是在这些场馆及其他一些竞技场内完成的。
这些体育场所及其他相关事宜的宣传活动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以及海报的形式进行的。最初宣传语似乎是手写的即兴创造,摩洛哥学者穆哈默德·阿萨法于1845年至1846年间访问巴黎时对广告宣传作了如下描述:商人们将自己的货物及其特点写在纸上,同时标明货物的产地和价格,然后将这些纸粘贴在人们路过的墙上、休闲的小亭子上,或者城门口……即贴在人群聚集的每个角落,以达到推销的目的。
内容简介
从罗马时代的“卢特提亚”到21世纪的“大巴黎”,作为首都城市,巴黎的历史与法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巴黎见证了一个个王朝的兴亡盛衰;在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中,巴黎始终在漩涡中心左右着法国前进的方向;在浪漫传奇的世纪之交,巴黎也作为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书是一部巴黎通史,既包罗万象又妙趣横生。城市的建设,民众的斗争,文化的衍生……科林·琼斯以生动、诙谐的笔法,呈现了巴黎千余年的历史进程,勾勒出一幅幅迷人的城市生活图景。
作者简介
科林·琼斯
英国历史学家、法国史专家。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于伦敦大学任教,曾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八大、法兰西公学院等著名高校及科研机构任访问学者。著有《剑桥插图法国史》《凡尔赛宫》《微笑革命》《伟大民族》等十余部著作。2014年,因其在历史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荣获大英帝国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