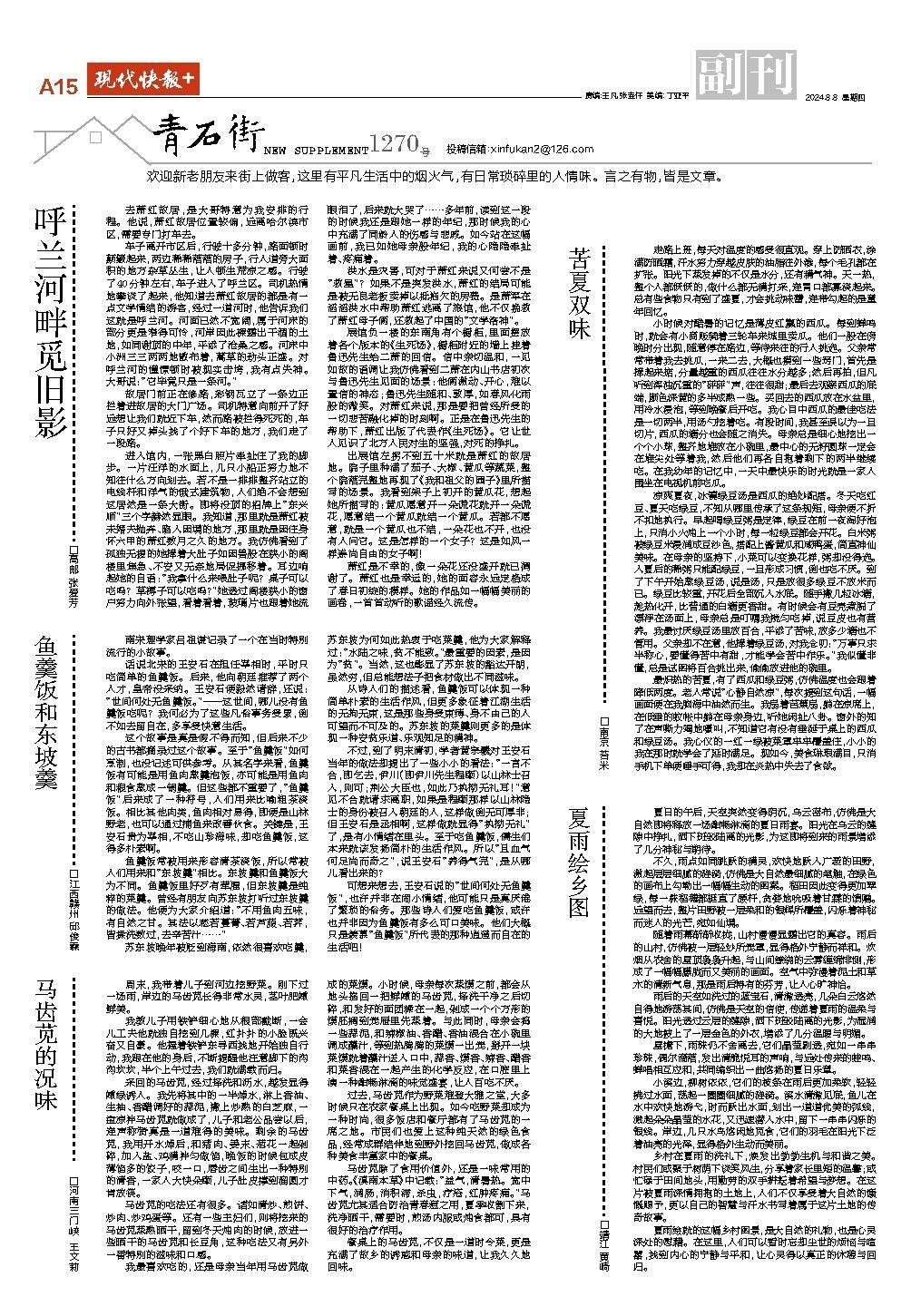□高邮 张爱芳
去萧红故居,是大哥特意为我安排的行程。他说,萧红故居位置较偏,远离哈尔滨市区,需要专门打车去。
车子离开市区后,行驶十多分钟,路面顿时颠簸起来,两边稀稀落落的房子,行人道旁大面积的地方杂草丛生,让人顿生荒凉之感。行驶了40分钟左右,车子进入了呼兰区。司机热情地攀谈了起来,他知道去萧红故居的都是有一点文学情结的游客,经过一道河时,他告诉我们这就是呼兰河。河面已然不宽阔,属于河床的部分更是窄得可怜,河岸因此裸露出干涸的土地,如同谢顶的中年,平添了沧桑之感。河床中小洲三三两两地散布着,蒿草的劲头正盛。对呼兰河的憧憬顿时被现实击垮,我有点失神。大哥说:“它毕竟只是一条河。”
故居门前正在修路,彩钢瓦立了一条边正拦着进故居的大门广场。司机特意向前开了好远想让我们就近下车,然而路被拦得死死的,车子只好又掉头找了个好下车的地方,我们走了一段路。
进入馆内,一张黑白照片牵扯住了我的脚步。一片汪洋的水面上,几只小船正努力地不知往什么方向划去。若不是一排排整齐站立的电线杆和洋气的俄式建筑物,人们绝不会想到这居然是一条大街。即将没顶的招牌上“东兴顺”三个字赫然显眼。我知道,那里就是萧红被未婚夫抛弃、陷入困境的地方,那里就是困住身怀六甲的萧红数月之久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了孤独无援的她捧着大肚子如困兽般在狭小的阁楼里焦急、不安又无奈地局促挪移着。耳边响起她的自语:“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她透过阁楼狭小的窗户努力向外张望,看着看着,玻璃片也跟着她流眼泪了,后来就大哭了……多年前,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是跟她一样的年纪,那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同龄人的伤感与悲戚。如今站在这幅画前,我已如她母亲般年纪,我的心隐隐牵扯着、疼痛着。
洪水是灾害,可对于萧红来说又何尝不是“救星”?如果不是突发洪水,萧红的结局可能是被无良老板卖掉以抵拖欠的房费。是萧军在滔滔洪水中帮助萧红逃离了旅馆,他不仅挽救了萧红母子俩,还救起了中国的“文学洛神”。
展馆负一楼的东南角有个橱柜,里面摆放着各个版本的《生死场》,橱柜附近的墙上挂着鲁迅先生给二萧的回信。信中亲切温和,一见如故的语调让我仿佛看到二萧在内山书店初次与鲁迅先生见面的场景:他俩激动、开心,难以置信的神态;鲁迅先生随和、敦厚,如春风化雨般的微笑。对萧红来说,那是要把曾经所受的一切悲苦融化掉的时刻啊。正是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出版了代表作《生死场》。它让世人见识了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
出展馆左拐不到五十米就是萧红的故居地。院子里种满了茄子、大椒、黄瓜等蔬菜,整个院落完整地再现了《我和祖父的园子》里所描写的场景。我看到架子上初开的黄瓜花,想起她所描写的: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这是怎样的一个女子?这是如风一样崇尚自由的女子啊!
萧红是不幸的,像一朵花还没盛开就已凋谢了。萧红也是幸运的,她的面容永远定格成了春日初绽的模样。她的作品如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一首首动听的歌谣经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