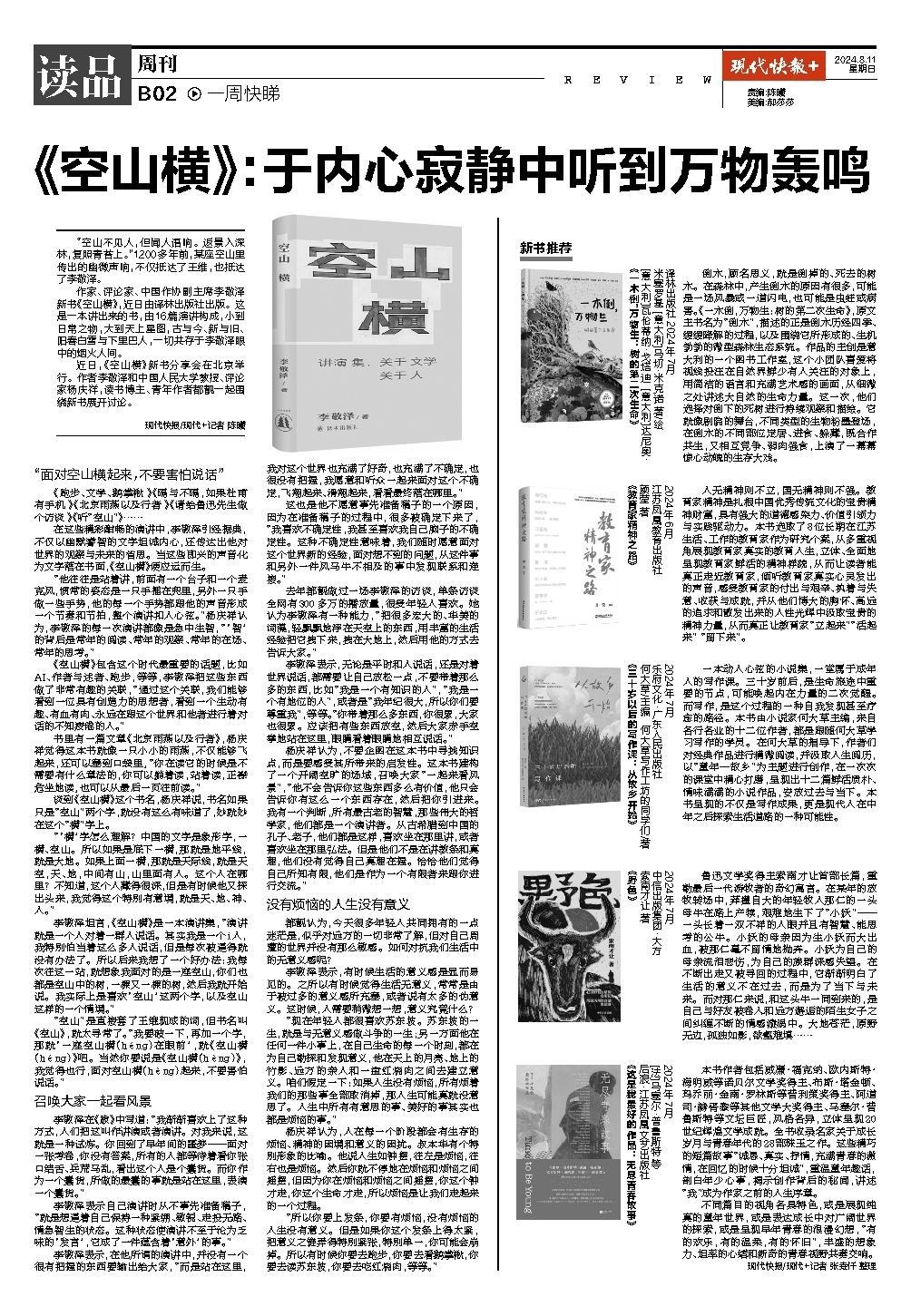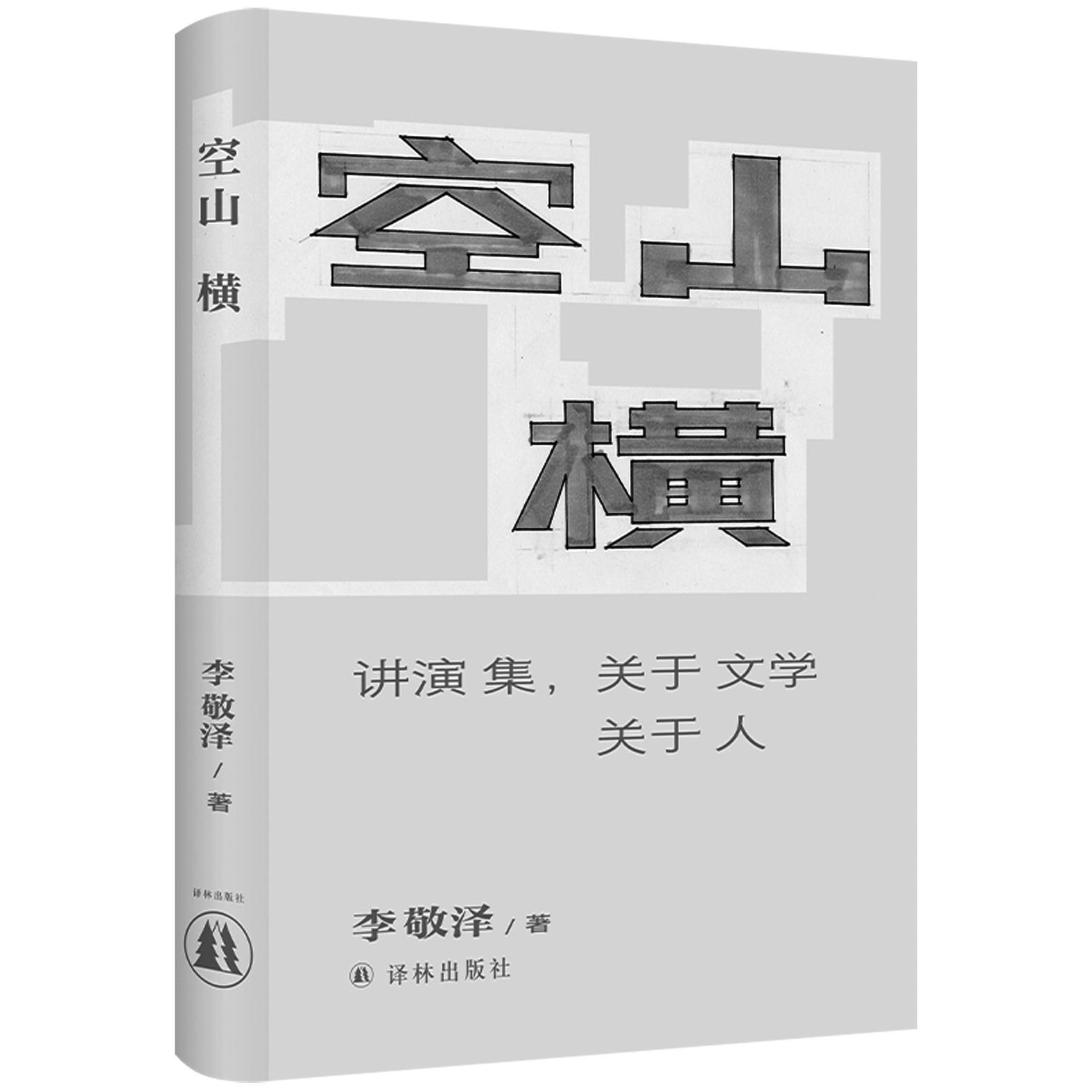“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1200多年前,某座空山里传出的幽微声响,不仅抵达了王维,也抵达了李敬泽。
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新书《空山横》,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讲出来的书,由16篇演讲构成,小到日常之物,大到天上星图,古与今、新与旧、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一切共存于李敬泽眼中的烟火人间。
近日,《空山横》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作者李敬泽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评论家杨庆祥,读书博主、青年作者都靓一起围绕新书展开讨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面对空山横起来,不要害怕说话”
《跑步、文学、鹅掌楸 》《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 》《北京雨燕以及行者 》《请给鲁迅先生做个访谈 》《听“空山”》……
在这些精彩酣畅的演讲中,李敬泽引经据典,不仅以幽默睿智的文字坦诚内心,还传达出他对世界的观察与未来的省思。当这些即兴的声音化为文字落在书面,《空山横》便应运而生。
“他往往是站着讲,前面有一个台子和一个麦克风,惯常的姿态是一只手插在兜里,另外一只手做一些手势,他的每一个手势都跟他的声音形成一个节奏和节拍,整个演讲扣人心弦。”杨庆祥认为,李敬泽的每一次演讲都像是急中生智,“‘智’的背后是常年的阅读、常年的观察、常年的在场、常年的思考。”
《空山横》包含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话题,比如AI、作者与述者、跑步,等等,李敬泽把这些东西做了非常有趣的关联,“通过这个关联,我们能够看到一位具有创造力的思想者,看到一个生动有趣、有血有肉、永远在跟这个世界和他者进行着对话的不知疲倦的人。”
书里有一篇文章《北京雨燕以及行者》,杨庆祥觉得这本书就像一只小小的雨燕,不仅能够飞起来,还可以塞到口袋里,“你在读它的时候是不需要有什么章法的,你可以躺着读,站着读,正襟危坐地读,也可以从最后一页往前读。”
谈到《空山横》这个书名,杨庆祥说,书名如果只是“空山”两个字,就没有这么有味道了,妙就妙在这个“横”字上。
“‘横’字怎么理解?中国的文字是象形字,一横、空山。所以如果是底下一横,那就是地平线,就是大地。如果上面一横,那就是天际线,就是天空,天、地,中间有山,山里面有人。这个人在哪里?不知道,这个人藏得很深,但是有时候他又探出头来,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境,就是天、地、神、人。”
李敬泽坦言,《空山横》是一本演讲集,“演讲就是一个人对着一群人说话。其实我是一个i人,我特别怕当着这么多人说话,但是每次被逼得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我每次往这一站,就想象我面对的是一座空山,你们也都是空山中的树,一棵又一棵的树,然后我就开始说。我实际上是喜欢‘空山’这两个字,以及空山这样的一个情境。”
“空山”是直接套了王维现成的词,但书名叫《空山》,就太寻常了。“我要破一下,再加一个字,那就‘一座空山横(héng)在眼前’,就《空山横(héng)》吧。当然你要说是《空山横(hèng)》,我觉得也行,面对空山横(hèng)起来,不要害怕说话。”
召唤大家一起看风景
李敬泽在《跋》中写道:“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方式,人们把这叫作讲演或者演讲。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试炼。你回到了早年间的噩梦——面对一张考卷,你没有答案,所有的人都等待着看你张口结舌、兵荒马乱,看出这个人是个蠢货。而你作为一个蠢货,所做的最蠢的事就是站在这里,表演一个蠢货。”
李敬泽表示自己演讲时从不事先准备稿子,“就是想逼着自己保持一种紧绷、敏锐、走投无路、情急智生的状态。这种状态使演讲不至于沦为乏味的‘发言’,它成了一件蕴含着‘意外’的事。”
李敬泽表示,在他所谓的演讲中,并没有一个很有把握的东西要输出给大家,“而是站在这里,我对这个世界也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不确定,也很没有把握,我愿意和听众一起来面对这个不确定,飞翔起来、滑翔起来,看看最终落在哪里。”
这也是他不愿意事先准备稿子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准备稿子的过程中,很多被确定下来了,“我喜欢不确定性,我甚至喜欢我自己脑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随时愿意面对这个世界新的经验,面对想不到的问题,从这件事和另外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中发现联系和连接。”
去年都靓做过一场李敬泽的访谈,单条访谈全网有300多万的播放量,很受年轻人喜欢。她认为李敬泽有一种能力,“把很多宏大的、华美的词藻,轻飘飘地浮在天空上的东西,用丰富的生活经验把它拽下来,拽在大地上,然后用他的方式去告诉大家。”
李敬泽表示,无论是平时和人说话,还是对着世界说话,都需要让自己放松一点,不要带着那么多的东西,比如“我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或者是“我年纪很大,所以你们要尊重我”,等等。“你带着那么多东西,你很累,大家也很累。应该把有些东西放空,然后大家赤手空拳地站在这里,眼睛看着眼睛地相互说话。”
杨庆祥认为,不要企图在这本书中寻找知识点,而是要感受其所带来的启发性。这本书建构了一个开阔空旷的场域,召唤大家“一起来看风景”,“他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多么有价值,他只会告诉你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然后把你引进来。我有一个判断,所有最古老的智慧,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他们都是一个演讲者。从古希腊到中国的孔子、老子,他们都是这样,喜欢坐在那里讲,或者喜欢坐在那里弘法。但是他们不是在讲教条和真理,他们没有觉得自己真理在握。恰恰他们觉得自己所知有限,他们是作为一个有限者来跟你进行交流。”
没有烦恼的人生没有意义
都靓认为,今天很多年轻人共同拥有的一点迷茫是,似乎对远方的一切非常了解,但对自己周遭的世界并没有那么敏感。如何对抗我们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呢?
李敬泽表示,有时候生活的意义感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有时候觉得生活无意义,常常是由于被过多的意义感所充塞,或者说有太多的伪意义。这时候,人需要稍微想一想,意义究竟什么?
“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苏东坡。苏东坡的一生,就是与无意义感做斗争的一生;另一方面他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在为自己勘探和发现意义,他在天上的月亮、地上的竹影、远方的亲人和一盘红烧肉之间去建立意义。咱们假定一下:如果人生没有烦恼,所有烦着我们的那些事全部取消掉,那人生可能真就没意思了。人生中所有有意思的事、美好的事其实也都是烦恼的事。”
杨庆祥认为,人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生存的烦恼、精神的困境和意义的困扰。叔本华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他说人生如钟摆,往左是烦恼,往右也是烦恼。然后你就不停地在烦恼和烦恼之间摇摆,但因为你在烦恼和烦恼之间摇摆,你这个钟才走,你这个生命才走,所以烦恼是让我们走起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要上发条,你要有烦恼,没有烦恼的人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这个发条上得太紧,把意义之链弄得特别紧张,特别单一,你可能会崩掉。所以有时候你要去跑步,你要去看鹅掌楸,你要去读苏东坡,你要去吃红烧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