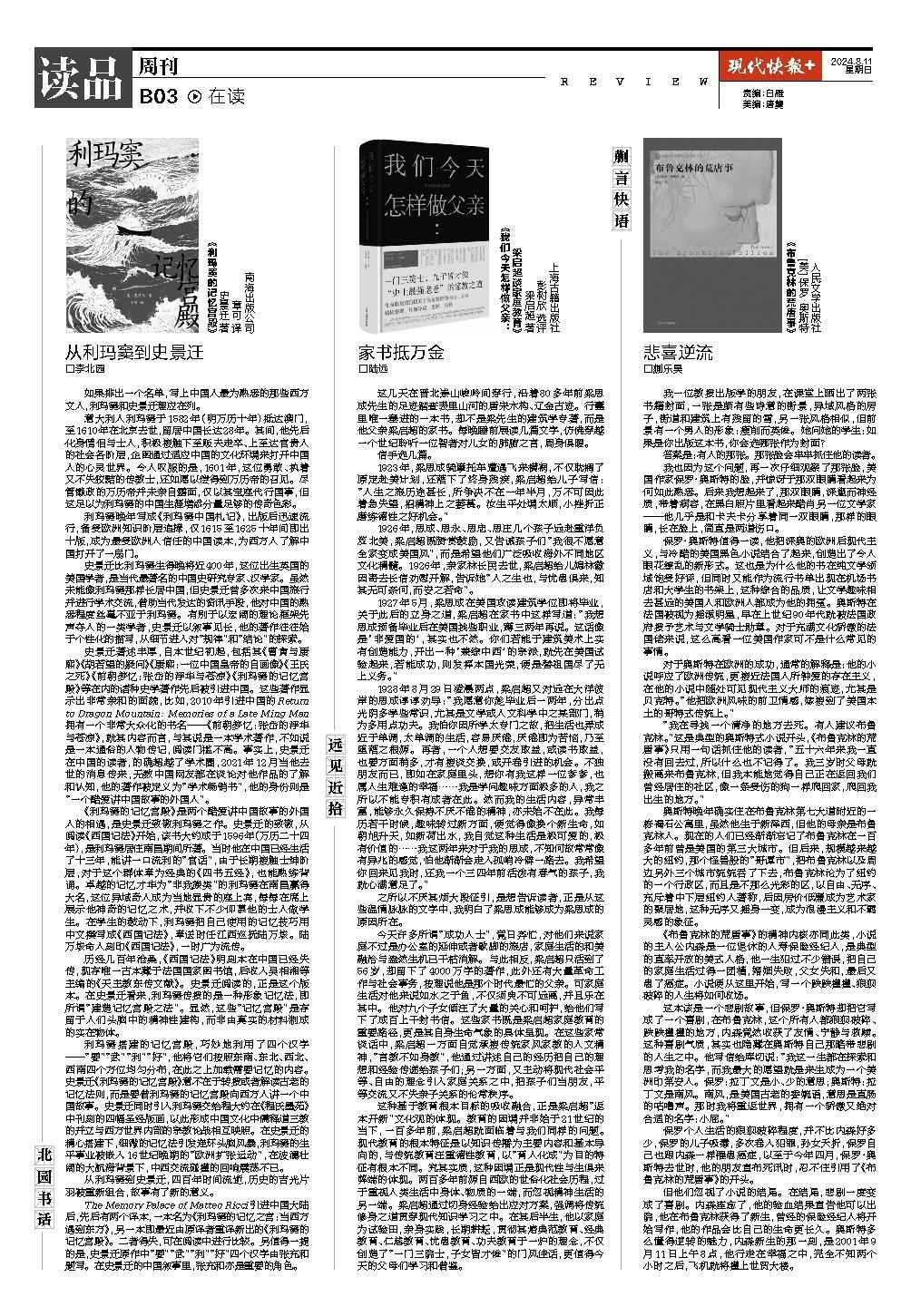□陆远
这几天在晋北崇山峻岭间穿行,沿着80多年前梁思成先生的足迹踏查表里山河的唐宋木构、辽金古迹。行囊里唯一塞进的一本书,却不是梁先生的建筑学专著,而是他父亲梁启超的家书。每晚睡前展读几篇文字,仿佛穿越一个世纪聆听一位智者对儿女的肺腑之言,周身俱暖。
信手选几篇。
1923年,梁思成骑摩托车遭遇飞来横祸,不仅耽搁了原定赴美计划,还落下了终身残疾,梁启超给儿子写信:“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葨。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1926年,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几个孩子远赴重洋负笈北美,梁启超既赞赏鼓励,又告诫孩子们“我很不愿意全家变成美国风”,而是希望他们广泛吸收海外不同地区文化精髓。1926年,亲家林长民去世,梁启超给儿媳林徽因寄去长信劝慰开解,告诉她“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1927年5月,梁思成在美国攻读建筑学位即将毕业,关于此后的立身之道,梁启超在家书中这样写道:“我想思成预备毕业后在美国找些职业,蹲三两年再说。这话像是‘非爱国的’,其实也不然。你们若能于建筑美术上实有创造能力,开出一种‘兼综中西’的宗派,就先在美国试验起来,若能成功,则发挥本国光荣,便是替祖国尽了无上义务。”
1928年8月29日凌晨两点,梁启超又对远在大洋彼岸的思成谆谆劝导:“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想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之所以不厌其烦大段征引,是想告诉读者,正是从这些温情脉脉的文字中,我明白了梁思成能够成为梁思成的原因所在。
今天许多所谓“成功人士”,竟日奔忙,对他们来说家庭不过是办公室的延伸或者歇脚的旅店,家庭生活的和美融洽与盎然生机已干枯消解。与此相反,梁启超只活到了56岁,却留下了4000万字的著作,此外还有大量革命工作与社会事务,按理说他是那个时代最忙的父亲。可家庭生活对他来说如水之于鱼,不仅须臾不可远离,并且乐在其中。他对九个子女倾注了大量的关心和呵护,给他们写下了成百上千封书信。这些家书既是梁启超家庭教育的重要路径,更是其自身生命气象的具体呈现。在这些家常谈话中,梁启超一方面自觉承接传统家风家教的人文精神,“言教不如身教”,他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把自己的理想和经验传递给孩子们;另一方面,又主动将现代社会平等、自由的理念引入家庭关系之中,把孩子们当朋友,平等交流又不失亲子关系的伦常秩序。
这种基于教育根本目标的吸收融合,正是梁启超“返本开新”文化观的体现。教育的困境并非始于21世纪的当下,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面临着与我们同样的问题。现代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以知识传播为主要内容和基本导向的,与传统教育注重德性教育,以“育人化成”为目的特征有根本不同。究其实质,这种困境正是现代性与生俱来弊端的体现。两百多年前源自西欧的世俗化社会历程,过于重视人类生活中身体、物质的一端,而忽视精神生活的另一端。梁启超通过切身经验给出应对方案,强调将传统修身之道贯穿现代知识学习之中。在其后半生,他以家庭为试验田,亲身实践,长期耕耘,贯彻其熔典范教育、经典教育、仁慈教育、忧患教育、功夫教育于一炉的理念,不仅创造了“一门三院士,子女皆才俊”的门风佳话,更值得今天的父母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