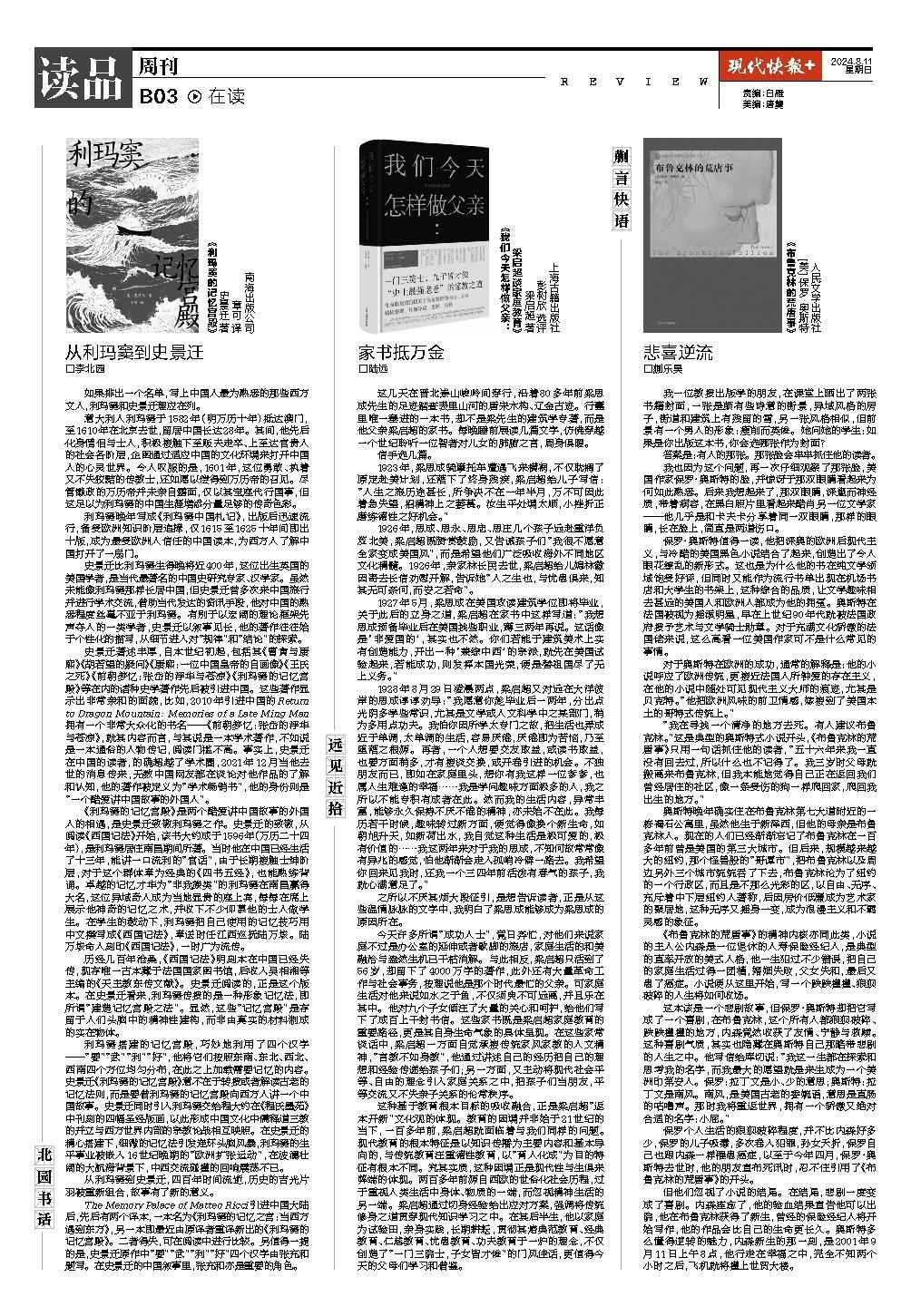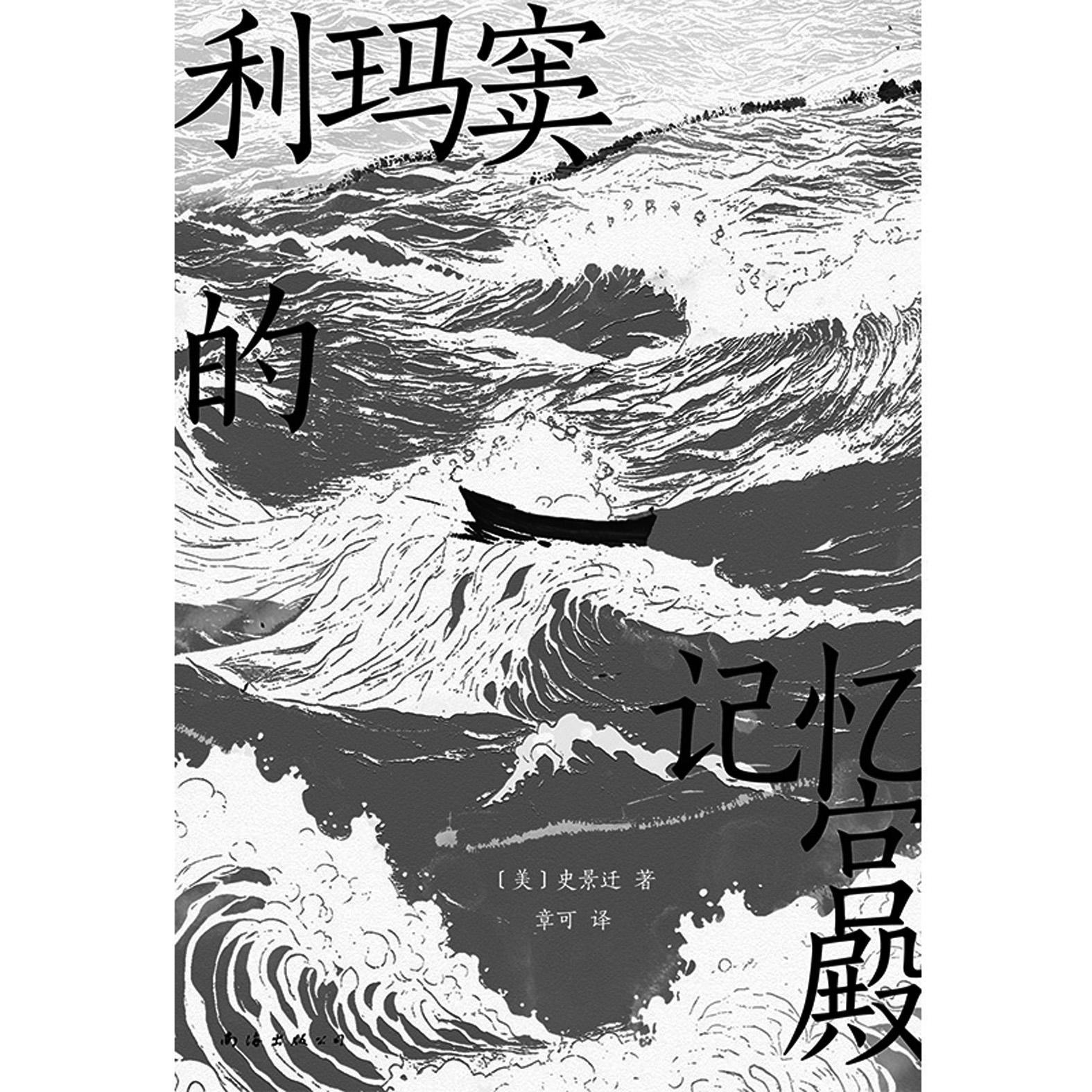□李北园
如果排出一个名单,写上中国人最为熟悉的那些西方文人,利玛窦和史景迁理应在列。
意大利人利玛窦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抵达澳门,至1610年在北京去世,留居中国长达28年。其间,他先后化身僧侣与士人,积极接触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贵人的社会各阶层,企图通过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来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令人叹服的是,1601年,这位勇敢、执着又不失狡黠的传教士,还如愿以偿得到万历帝的召见。尽管懒政的万历帝并未亲自露面,仅以其宝座代行国事,但这足以为利玛窦的中国生涯增添分量足够的传奇色彩。
利玛窦晚年写成《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后迅速流行,备受欧洲知识阶层追捧,仅1615至1625十年间即出十版,成为最受欧洲人信任的中国读本,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门。
史景迁比利玛窦生得晚将近400年,这位出生英国的美国学者,是当代最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虽然未能像利玛窦那样长居中国,但史景迁曾多次来中国旅行并进行学术交流,借助当代发达的资讯手段,他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丝毫不亚于利玛窦。有别于以宏阔的理论框架先声夺人的一类学者,史景迁以叙事见长,他的著作往往始于个性化的描写,从细节进入对“规律”和“结论”的探索。
史景迁著述丰厚,自本世纪初起,包括其《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康熙:一位中国皇帝的自画像》《王氏之死》《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利玛窦的记忆宫殿》等在内的诸种史学著作先后被引进中国。这些著作显示出非常亲和的面貌,比如,2010年引进中国的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拥有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书名——《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就其内容而言,与其说是一本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本通俗的人物传记,阅读门槛不高。事实上,史景迁在中国的读者,的确超越了学术圈,2021年12月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无数中国网友都在谈论对他作品的了解和认知,他的著作被定义为“学术畅销书”,他的身份则是“一个酷爱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人”。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是两个酷爱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人的相遇,是史景迁致敬利玛窦之作。史景迁的致敬,从阅读《西国记法》开始,该书大约成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是利玛窦居住南昌期间所著。当时他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三年,能讲一口流利的“官话”,由于长期接触士绅阶层,对于这个群体奉为经典的《四书五经》,也能熟练背诵。卓越的记忆才华为“非我族类”的利玛窦在南昌赢得大名,这位异域奇人成为当地显贵的座上宾,每每在席上展示他神奇的记忆之术,并收下不少仰慕他的士人做学生。在学生的鼓动下,利玛窦把自己使用的记忆技巧用中文撰写成《西国记法》,奉送时任江西巡抚陆万垓。陆万垓命人刻印《西国记法》,一时广为流传。
历经几百年沧桑,《西国记法》明刻本在中国已经失传,现存唯一古本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后收入吴相湘等主编的《天主教东传文献》。史景迁阅读的,正是这个版本。在史景迁看来,利玛窦传授的是一种形象记忆法,即所谓“建造记忆宫殿之法”。显然,这些“记忆宫殿”是存留于人们头脑中的精神性建构,而非由真实的材料制成的实在物体。
利玛窦搭建的记忆宫殿,巧妙地利用了四个汉字——“要”“武”“利”“好”,他将它们按照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个方位均匀分布,在此之上加载需要记忆的内容。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意不在于转授或者解读古老的记忆法则,而是要借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向西方人讲一个中国故事。史景迁同时引入利玛窦交给程大约在《程氏墨苑》中刊刻的四幅圣经版画,以此形成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的并立与西方世界内部的宗教论战相互映照。在史景迁的精心搭建下,细微的记忆法引发连环头脑风暴,利玛窦的生平事业被嵌入16世纪晚期的“欧洲扩张运动”,在波澜壮阔的大航海背景下,中西交流碰撞的回响震荡不已。
从利玛窦到史景迁,四百年时间流逝,历史的吉光片羽被重新组合,故事有了新的意义。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引进中国大陆后,先后有两个译本,一本名为《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另一本即最近由原译者重译新出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二者得失,可在阅读中进行比较。另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原作中“要”“武”“利”“好”四个汉字由张充和题写。在史景迁的中国叙事里,张充和亦是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