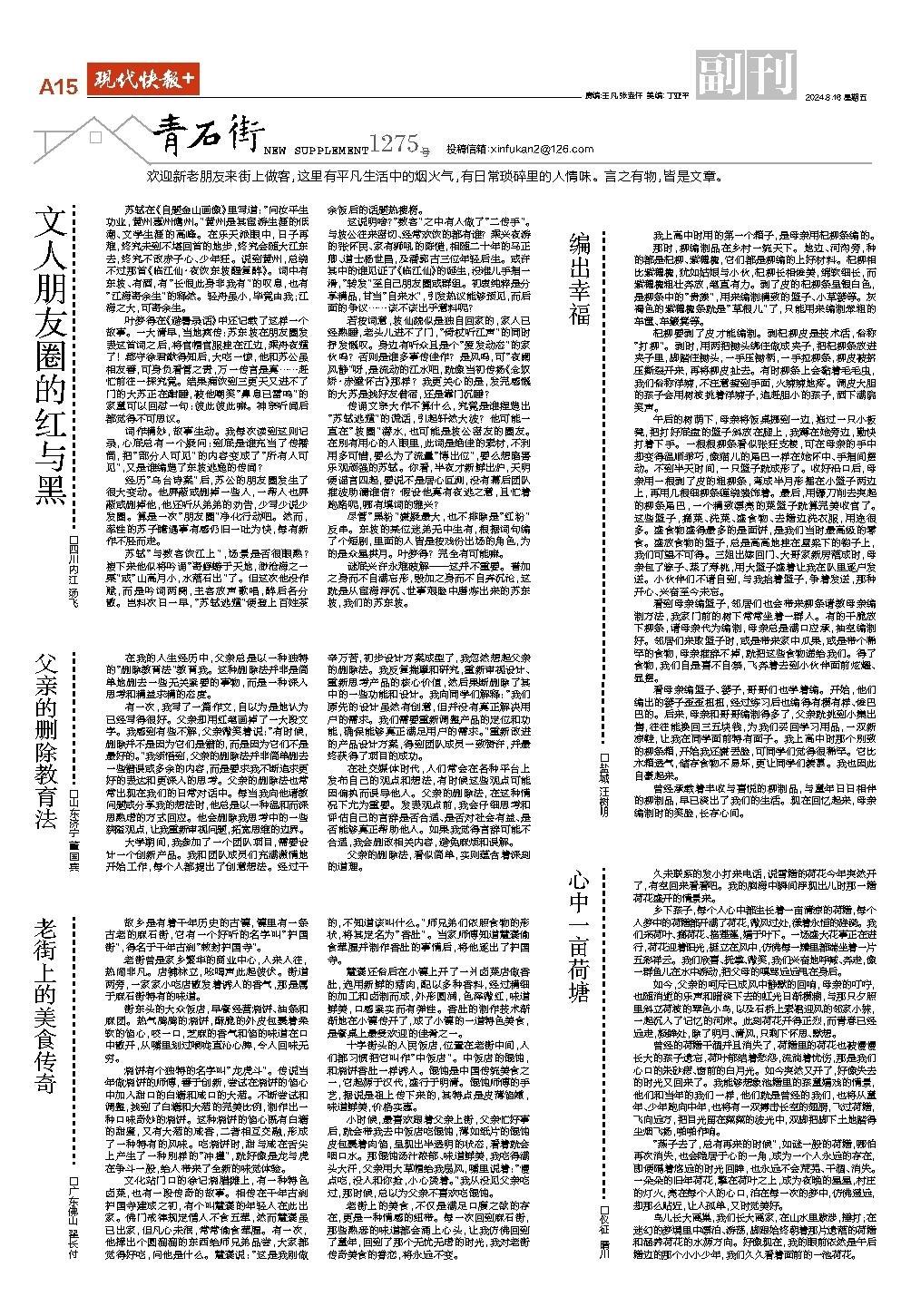□盐城 汪树明
我上高中时用的第一个箱子,是母亲用杞柳条编的。
那时,柳编制品在乡村一统天下。地边、河沟旁,种的都是杞柳、紫穗槐,它们都是柳编的上好材料。杞柳相比紫穗槐,犹如姑娘与小伙,杞柳长相俊美,绵软细长,而紫穗槐粗壮奔放,笔直有力。剥了皮的杞柳条呈银白色,是柳条中的“贵族”,用来编制精致的篮子、小草篓等。灰褐色的紫穗槐条就是“草根儿”了,只能用来编制笨粗的车筐、车簸箕等。
杞柳要剥了皮才能编制。剥杞柳皮是技术活,俗称“打柳”。剥时,用两把锄头绑住做成夹子,把杞柳条放进夹子里,脚踏住锄头,一手压锄柄,一手拉柳条,柳皮被挤压撕裂开来,再将柳皮扯去。有时柳条上会黏着毛毛虫,我们俗称洋辣,不注意蜇到手面,火辣辣地疼。调皮大胆的孩子会用树枝挑着洋辣子,追赶胆小的孩子,洒下满院笑声。
午后的树荫下,母亲将饭桌挪到一边,拖过一只小板凳,把打好底盘的篮子斜放在腿上,我蹲在她旁边,勤快打着下手。一根根柳条看似张狂支棱,可在母亲的手中却变得温顺乖巧,像猫儿的尾巴一样在她怀中、手指间摆动。不到半天时间,一只篮子就成形了。收好沿口后,母亲用一根剥了皮的粗柳条,弯成半月形插在小篮子两边上,再用几根细柳条缠绕装饰着。最后,用镰刀削去突起的柳条尾巴,一个精致漂亮的菜篮子就算完美收官了。这些篮子,摘菜、洗菜、盛食物、去塘边洗衣服,用途很多。盛食物盛得最多的是面饼,是我们当时最高级的零食。盛放食物的篮子,总是高高地挂在屋梁下的钩子上,我们可望不可得。三姐出嫁回门、大哥家新房落成时,母亲包了粽子、蒸了寿桃,用大篮子盛着让我在队里逐户发送。小伙伴们不请自到,与我抬着篮子,争着发送,那种开心、兴奋至今未忘。
看到母亲编篮子,邻居们也会带来柳条请教母亲编制方法,我家门前的树下常常坐着一群人。有的干脆放下柳条,请母亲代为编制,母亲总是满口应承,抽空编制好。邻居们来取篮子时,或是带来家中瓜果,或是带个稀罕的食物,母亲推辞不掉,就把这些食物递给我们。得了食物,我们自是喜不自禁,飞奔着去到小伙伴面前炫耀、显摆。
看母亲编篮子、篓子,哥哥们也学着编。开始,他们编出的篓子歪歪扭扭,经过练习后也编得有模有样、俊巴巴的。后来,母亲和哥哥编制得多了,父亲就挑到小集出售,往往能换回三五块钱,为我们买回学习用品,一双新凉鞋,让我在同学面前特有面子。我上高中时那个别致的柳条箱,开始我还嫌丢脸,可同学们觉得很稀罕。它比木箱透气,储存食物不易坏,更让同学们羡慕。我也因此自豪起来。
曾经承载着丰收与喜悦的柳制品,与童年日日相伴的柳制品,早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母亲编制时的笑脸,长存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