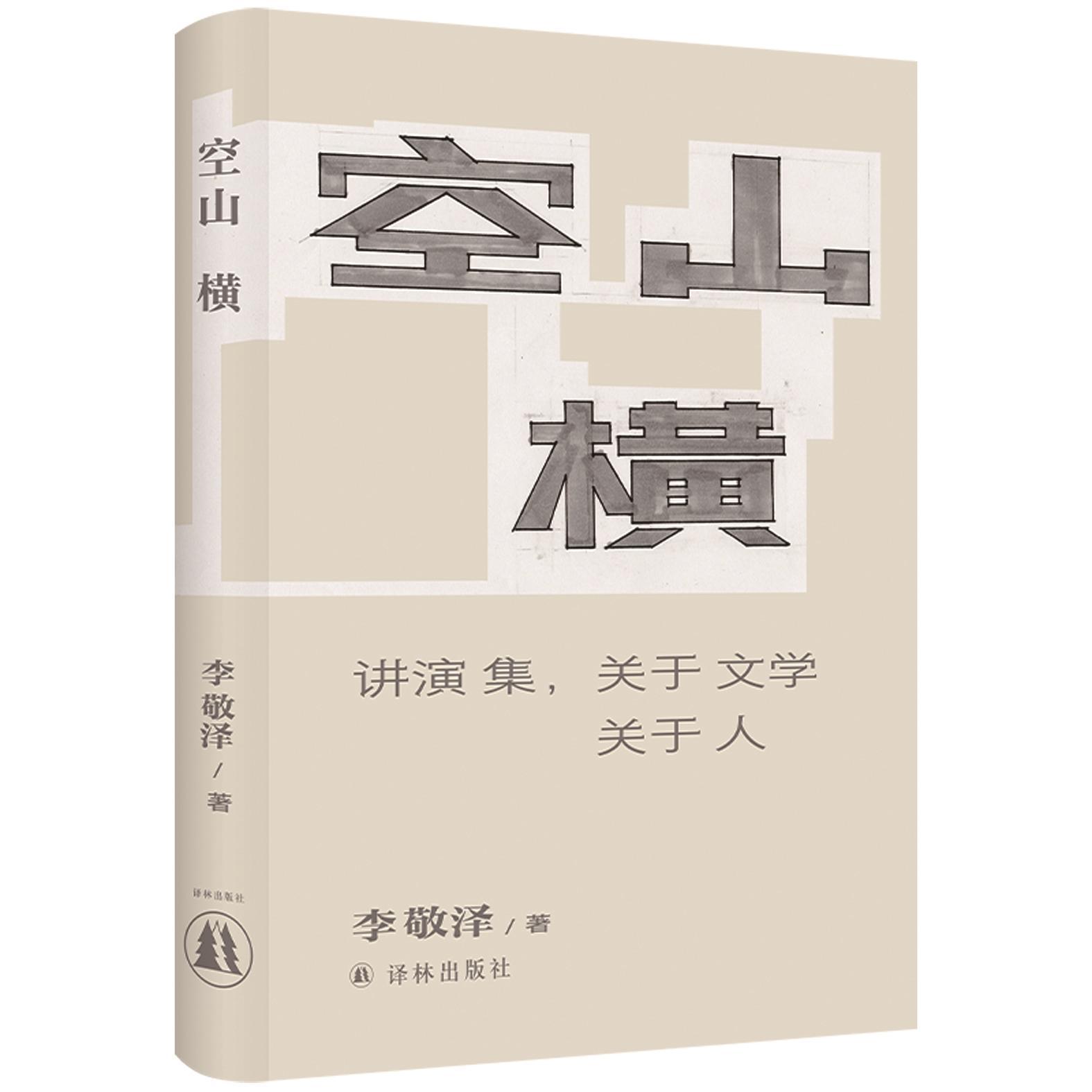如果你关注文学,很难不注意到近年来作家李敬泽贡献了很多“刷屏”的演讲。他在《南方周末》N-TALK文学之夜上说,写作不是证明“我”的存在,而是进入天地万事万物,体验“我不是我”;他在“凤凰文学之夜”上发问,面对ChatGPT的挑战,作者应如何捍卫人类创造力的尊严、能力和荣誉……这些演讲每每问世,都会在朋友圈引发一阵热议。
近日,由这些演讲结集而成的新书《空山横》由译林出版社推出。李敬泽在16篇演讲中引经据典,展现了他对文学、人生、自然乃至未来科技的深刻洞察与独到见解。8月15日,上海书展期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携新作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与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黄平以及媒体人罗昕一起,围绕文学与演讲展开讨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文
穆子健/摄
在演讲中,复活古典文学中的“气”与“势”
在毛尖看来,《空山横》中的文章是一种极具风格的文体,看似离题万里的讲述最后都能回归主题,这种文体背后,就是李敬泽“青鸟”般自由的写作精神,“他能从王维一下进入西欧的某个短篇小说,从小说中的壁橱谈到打工文学。他还能自由地出入小说、散文、演讲、随笔等各种文体,他把这些都打通了。这是人类能够与ChatGPT竞争的写作风格,因为ChatGPT还不会突破类型、不会联想。”
李敬泽表示,他的这种写作其实受到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影响,“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鲁迅的笔下最终都‘相及’了。鲁迅提供的伟大的方法论,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被穷尽。尤其是面对无穷复杂、嘈杂、碎片的现实,我们真的需要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进行归拢和建立意义的方法。”
黄平谈到,《空山横》中的文章虽然都是现代文,但其中弥漫着一种古意,叩响了中国古典文明中“文”的传承脉络。对此,李敬泽回应,古典文学中讲究“气”和“势”,这种“气”和“势”在现代文中是匮乏的,因为书面语的文章都是空间性的,缺乏生理性和身体性,而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在修改这些讲稿的过程中,他常常会回到面对着观众的现场,感受到那种现场感、互动感以及肾上腺素上升的感觉,“你知道自己的文章中有‘势’,这也是我这几年很喜欢这种文体的原因,你不知道从哪儿就开始‘飞’了。”
打破束缚,人生和自我应该是飞翔的、生长的
在李敬泽看来,写作与自我在某种程度上状态是相近的。由自由的写作方式,李敬泽进而谈到了人生和自我。
“现代世界中,每一个人都过于为自洽而焦虑。从原生家庭开始界定‘我是什么’。这种自洽一定程度上是自己给自己的小的强制性力量,把自己捆起来、关起来,一定要给自己赋型,觉得‘我就是这样’。其实我也可以是不自洽的,是开放的、飞翔的、御风而行的状态。”李敬泽觉得人其实可以同时喜欢优雅的艺术电影和恶俗的短视频,“面对一个繁星满天的世界,我们却在强烈地规训自己,你就失去了充分处理纷繁万物的能力。”
当下有很多人在谈自我,李敬泽认为,自我与世界并不是一种水瓶中的水与水瓶外的世界的关系,“自我处于不断生长和建构的关系中,有时候我们需要满怀好奇地去等待着、期待着自我可能是什么样的。当你想象有一个固定的完满的自我时,会认为意外和故障是负面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自我的‘意外’和‘故障’,这也许是我们在生长的一种表征。”
李敬泽特别谈到,在充斥着算法和“信息茧房”的当下,更不能去捍卫“窄”,“要有意识地寻找不一样的观点,人可能需要保持对差异、对与自己不同甚至构成张力、对让我们有点不舒服的东西的好奇。在众声嘈杂的时代,不能生活在一样的声音里,让自己做一个倾听者,听与我不一样的声音。世界的美好在于不同,而不在于相同。”
流量时代,文学也无须为“流量”焦虑
网络时代,一场演讲难免进入直播、弹幕、回放的流程。与此同时,“跨界”“破圈”等与流量紧密相关的词汇近年来频频被文学圈提及,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也影响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几位嘉宾如何看待“流量时代”的文学传播?
黄平认为,“跨界”“破圈”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向往,希望文学的声音能够抵达不同的群体,但文学向更远的世界传播不一定要以流量为衡量方式,“流量作为一种衡量方式也许是无效的。”毛尖觉得,“流量”其实是一个中性词,重要的是不要让“流量”影响了决策。
在李敬泽看来,作家的作品在当下如果能够通过各种形态达到延伸影响力的效果,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文学不必为“流量”焦虑。他不奢求有数量庞大的读者都来阅读他的书籍,如果有一些读者,已经买过几本他的书,也愿意继续在他出书的时候购买、阅读,他就已经觉得很满意,“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能够与读者建立类似于小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关系,依然是值得珍视的。”
参与本次分享会的嘉宾还有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袁楠、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