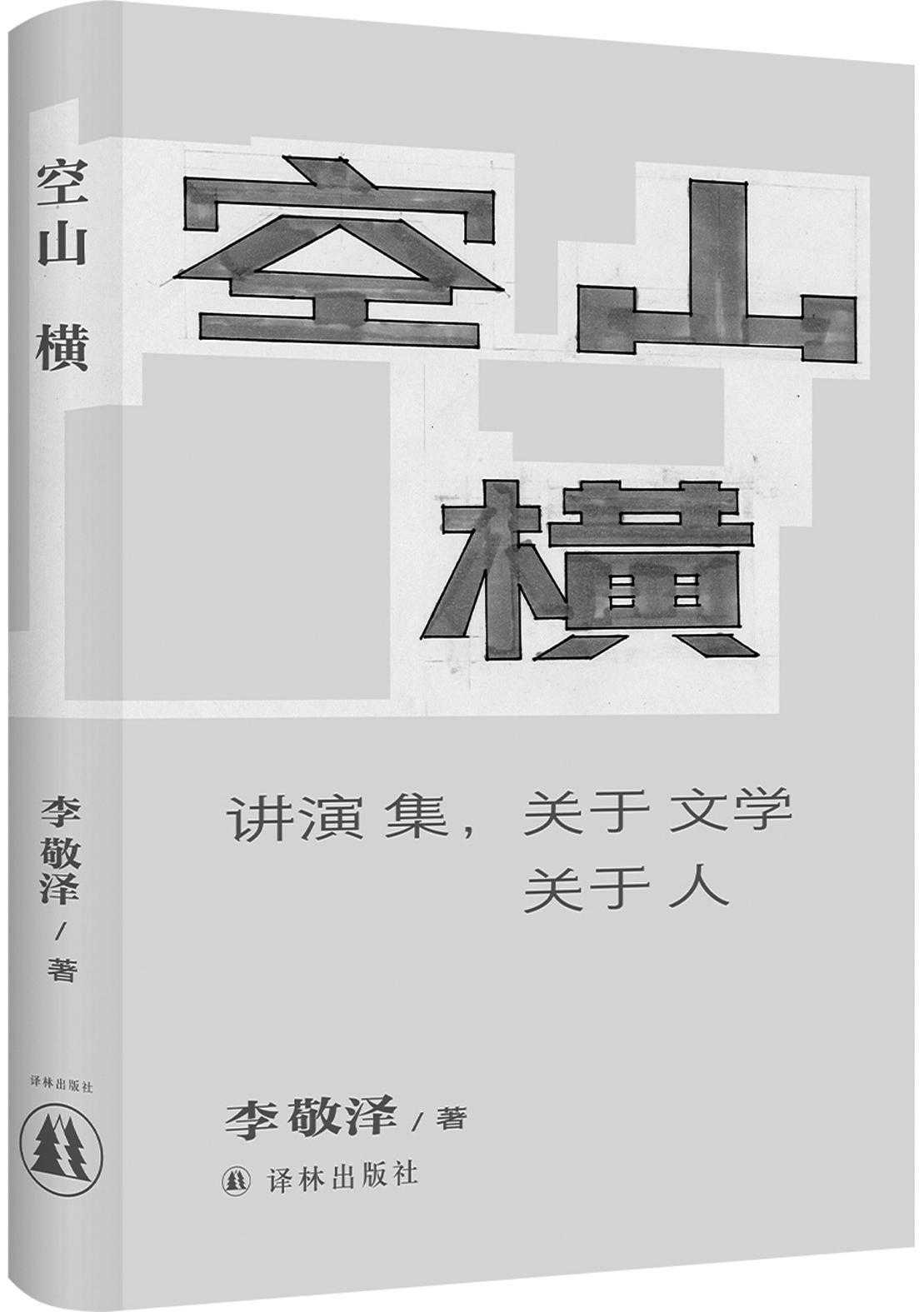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我们先从王维的一首诗说起,这首诗题为《鹿柴》。山本来无所谓空不空,山上有草木、飞禽、走兽、泉水和溪流,山怎么会空呢?但山就是空的,因为不见人。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吗?也不是,至少还是有一个的,就是说出“空山不见人”的那个人。人不见人,山才是空的,世界才是空的。什么是空?就是无,只有一个“我”的世界空空荡荡。
空山里的这个人,纵目一望,放眼看去,他看不见人,他看见了无。但是,接下来,空山不空了,无中生出了有,因为“但闻人语响”。
这个“人语”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话语,不是人在说话,是人的声音,是人最本真的声音:张开嘴,对着空山,喊一声“啊——”我在这里,你在吗?你是谁?这个“你”就是自我之外的他者。在山里,在莽莽苍苍的大自然的旷野里,在无边无际的沉默中,你的本能就是用你的声音寻找和确认他者的声音。一个人在寻找另一个人,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是个人,你就觉得山也不空了、世界也不空了。
在这样的时刻,喊出一声“啊”的人,吹口哨的人,你就是在搭建一个舞台,一座空山或这个寂静的夜晚成为了你的剧场。我坚信,人类的舞台和戏剧,它的原初的、根本的动机是声音。戏首先是听戏,你站在山野里一个临时搭起的野台子下面,你坐在国家大剧院的后排,或者你身处希腊一座古老圆形剧场的高处,你很可能无法看清舞台上的人长什么样,但是这有什么要紧,舞台上的声音,必定会清晰地抵达你的耳朵。在一些古老的戏剧形式中,舞台上的人常常会戴着面具或绘上脸谱,其中一层隐晦的意思是,你看不见我,“空山不见人”;然后,请听我的声音,让我的声音找到你,在你的耳膜、颅腔、心房中回荡,你在这声音中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既陌生又熟悉,你被叫醒、被召唤,你意识到你的有、你的在。你知道,真正的戏剧发生了。
这其实是一个奇迹。一个人与他者、与陌生人、与熟悉的陌生人的相遇,这其实是一个声音事件。“响”是声音,但“大音希声”,“不响”或无声或沉默也是声音。当人们以声音建立连接时,世界才得以展开,戏剧才真正开始,生活才真正开始。人类形而上的超验体验普遍来自声音,在华夏文明中,天意落为文字,但我坚信,在天意和天意的显现之间、在甲骨之形和甲骨之文之间,一定存有一个失落的声音环节——然后,我们才能理解礼乐之“乐”,才能理解某种声音何以从根本上照亮了我们。
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那座空山,声音照亮了王维,他听到了人语之“响”,但他是王维啊,一个绝顶闷骚的安静男子,他不可能扯开嗓子“啊”回去,他更不可能一个口哨打回去。他只是立在那里,静静地听,听着那声“啊”、那个口哨在空中消失,然后,“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他看见夕阳照进了深林,他又看见这光照在青苔上。
让我们想一想那个情境,在汉语中有一个词叫“响亮”,这个词真是绝妙的一个好词,“响”是听觉,是看不见的,但“亮”是视觉,是看得见的,是眼前一亮。钱锺书谈“通感”,响亮就是耳朵和眼睛相通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语响时,天地为之一亮,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烟花般的亮,不是静态的亮,是微妙的、流动着的亮。王维在这里用的词是“返”、是“复”,天光本来已经暗淡下去,但是随着“响”蓦然又亮起来,天光透过繁密的枝叶,探测着林有多深。王维的目光随着天光移动,从树梢到地上的青苔,他看着那被召唤回来的光照在了青苔上,就像暗香潜度,渐渐地洇染开来,青苔绿成了稀薄的阳光下微微动荡的海……
别忘了,王维是摩诘居士啊,这一刻,光的移动不是光动,是心动,不是光照亮了树林、照亮了青苔,而是他的心被那一“响”所照亮。考虑到王维的佛学背景,考虑到佛教在根本上是“如是我闻”的口传的声音宗教,《鹿柴》四句其实就是一条关于声音的偈子,由空到有、由外而内,世界在声音中无穷无尽地展开。
此身在处是空山。本来,今天的主题是“声音与文章之道”,但话从《鹿柴》说起,说着说着迷路了,找不到“文章之道”了。我的本意,是说在我们这个独特的古老文明中,声音是一条依稀隐微的线索,声音不是主流,文章之道是消音的,是无声的,古人所写的,其实是无声的文章。而现代性,在中国,它的一个重要面向是对声音的召唤和声音的觉醒,白话文运动的初衷就是让文章有声,但是,真的有声了吗?声音的现代性走过了曲折的路,现在,至少在所谓纯文学的文章写作中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但是,急什么呢?打开手机刷抖音吧,“抖音”这个名字起得真好,这也是通感,是“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寺多红叶烧人眼”,这个名字无意中透露了终极秘密,这不是视觉的统治,这是声音的胜利,是声音的抖动、痉挛、《科目三》,是声音的盛大狂欢,是人需要一万句两万句三万句……以至无穷句的说和听,是巨大的“响”覆盖和搜寻“不响”。
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每天都在刷抖音,我热爱这个“响”的世界。我的意思是,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正在与王维的《鹿柴》相互映照。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在朋友圈里都听到了一声响指,似乎遥远的和面前的事物将被震碎,OpenAI发布了首个视频生成模型。什么意思呢?好像是,搞电影的、拍视频的很快要无事可做了,我们可以输入《三体》,然后直接生成影像。但是,小说家们也不必庆幸,他们会是这个即将到来的未来世界的幸存者吗?超级AI真的不能生成尽如人意的小说吗?
——我不知道。但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比“空山”还空的山。万物繁盛,但人还剩下什么呢?你还剩下什么呢?也许,只剩下了你的声音,到目前为止。AI已经能够生成你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你吗?如果不是你,“他”又是谁呢?如果是你,你还在吗?远处传来你的声音,你是回应他还是回应你自己?还是最终,他就是你,你站在这里,听着远处的你发出一声“啊”?这“响”是不是最终会取消“不响”,把人与他者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那个静默的、充满无限可能性的间隙封死为一块浑然天成的巨石?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淡漠、超然地说出了一切,“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他也许是珍惜伤感地看着自己的心在移动,在那片光影波动的青苔上,他不仅看见了不久后的安史之乱,他还漠然地浏览着今天早上的朋友圈。
仅仅因为这首《鹿柴》,我认定王维是伟大的诗人和觉者。他洞彻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甚至暗自指引着一部英剧的创作。这个春节,除了刷抖音,我还看了《年轻的教宗》,那位希伯来-罗马传统下的教宗,那个来自另一个伟大的声音传统的年轻人,他竟对声音怀有深刻的不信任,但终有一日,他不得不发出声音,他必须演讲。那一天,当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愕然看见,他的座位是空的,他在远处,在众人视线之外,在干枯的树下,发出他的声音。
——他在空山中演讲,我听见他在阳光下发出安静的声音,他的声音回应着他很可能从来不曾听说的一位中国诗人的声音: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节选自《听“空山”—— 一次想象的讲演》)
内容简介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横》起于声音,它首先是说出来、讲出来的。由李敬泽的十六篇演讲构成,讨论文学、跑步、雨燕、鹅掌楸、超级AI、有机村庄、自然生态等多元主题。演讲或讲演,是一种与世界建立面对面的连接的方式。当我们以声音建立连接时,世界得以展开,生活真正开始。在这些精彩酣畅的演讲中,他引经据典,充满了真知灼见,不仅以幽默睿智的文字坦诚内心,还传达出他对世界的观察与未来的省思。事后他让即兴的声音化为文字落在书面。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作者简介
李敬泽
祖籍山西芮城,生于天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和评论作品《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上河记》《空山横:讲演集,关于文学关于人》《会议室和山丘》《跑步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等诸多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