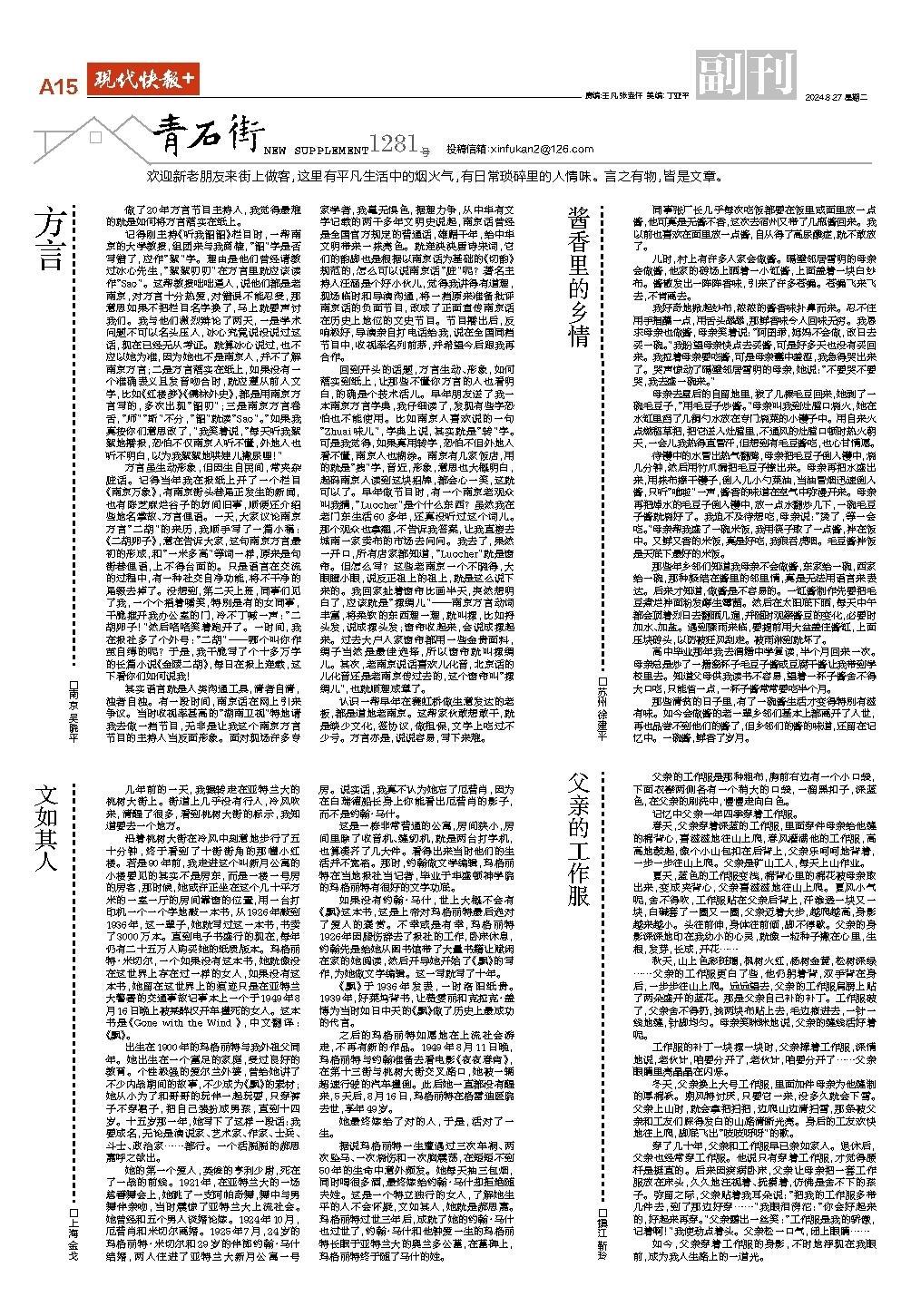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做了20年方言节目主持人,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将方言落实在纸上。
记得刚主持《听我韶韶》栏目时,一帮南京的大学教授,组团来与我商榷,“韶”字是否写错了,应作“絮”字。理由是他们曾经请教过冰心先生,“絮絮叨叨”在方言里就应该读作“Sao”。这帮教授咄咄逼人,说他们都是老南京,对方言十分热爱,对错误不能忍受,那意思如果不把栏目名字换了,马上就要声讨我们。我与他们激烈辩论了两天,一是学术问题不可以名头压人,冰心究竟说没说过这话,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就算冰心说过,也不应以她为准,因为她也不是南京人,并不了解南京方言;二是方言落实在纸上,如果没有一个准确表义且发音吻合时,就应遵从前人文字,比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用南京方言写的,多次出现“韶叨”;三是南京方言卷舌,“师”“斯”不分,“韶”就读“Sao”。“如果我真按你们意思改了,”我笑着说,“每天听我絮絮地播报,恐怕不仅南京人听不懂,外地人也听不明白,以为我絮絮地哄娃儿撒尿哩!”
方言虽生动形象,但因生自民间,常夹杂脏话。记得当年我在报纸上开了一个栏目《南京万象》,有南京街头巷尾正发生的新闻,也有陈芝麻烂谷子的坊间旧事,顺便还介绍些地名掌故、方言俚语。一天,大家议论南京方言“二胡”的来历,我顺手写了一篇小稿:《二胡卵子》,意在告诉大家,这句南京方言最初的形成,和“一米多高”等词一样,原来是句街巷俚语,上不得台面的。只是语言在交流的过程中,有一种社交自净功能,将不干净的尾缀去掉了。没想到,第二天上班,同事们见了我,一个个捂着嘴笑,特别是有的女同事,干脆推开我办公室的门,冷不丁喊一声:“二胡卵子!”然后咯咯笑着跑开了。一时间,我在报社多了个外号:“二胡”——哪个叫你作茧自缚的呢?于是,我干脆写了个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金陵二胡》,每日在报上连载,这下看你们如何说我!
其实语言就是人类沟通工具,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一段时间,南京话在网上引来争议。当时收视率甚高的“湖南卫视”特地请我去做一档节目,无非是让我这个南京方言节目的主持人当反面形象。面对现场许多专家学者,我毫无惧色,据理力争,从中华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多年文明史说起,南京话曾经是全国官方规定的普通话,雄踞千年,给中华文明带来一抹亮色。就连泱泱唐诗宋词,它们的韵脚也是根据以南京话为基础的《切韵》规范的,怎么可以说南京话“脏”呢?著名主持人汪涵是个好小伙儿,觉得我讲得有道理,现场临时和导演沟通,将一档原来准备批评南京话的负面节目,改成了正面宣传南京话在历史上地位的文史节目。节目播出后,反响极好,导演亲自打电话给我,说在全国同档节目中,收视率名列前茅,并希望今后跟我再合作。
回到开头的话题,方言生动、形象,如何落实到纸上,让那些不懂你方言的人也看明白,的确是个技术活儿。早年朋友送了我一本南京方言字典,我仔细读了,发现有些字恐怕也不能使用。比如南京人喜欢说的一句“Zhuai味儿”,字典上说,其实就是“转”字。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用转字,恐怕不但外地人看不懂,南京人也糊涂。南京有几家饭店,用的就是“拽”字,音近,形象,意思也大概明白,起码南京人读到这块招牌,都会心一笑,这就可以了。早年做节目时,有一个南京老观众叫我猜,“Luocher”是个什么东西?虽然我在老门东生活60多年,还真没听过这个词儿。那个观众也拿翘,不告诉我答案,让我直接去城南一家卖布的市场去问问。我去了,果然一开口,所有店家都知道,“Luocher”就是窗帘。但怎么写?这些老南京一个不晓得,大眼瞪小眼,说反正祖上的祖上,就是这么说下来的。我回家扯着窗帘比画半天,突然想明白了,应该就是“摞绸儿”——南京方言动词丰富,将柔软的东西理一理,就叫摞,比如捋头发,说成摞头发;窗帘收起来,会说成摞起来。过去大户人家窗帘都用一些金贵面料,绸子当然是最佳选择,所以窗帘就叫摞绸儿。其次,老南京说话喜欢儿化音,北京话的儿化音还是老南京传过去的,这个窗帘叫“摞绸儿”,也就顺理成章了。
认识一帮早年在赛虹桥做生意发达的老板,都是道地老南京。这帮家伙敢想敢干,就是缺少文化,签协议,做担保,文字上吃过不少亏。方言亦是,说说容易,写下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