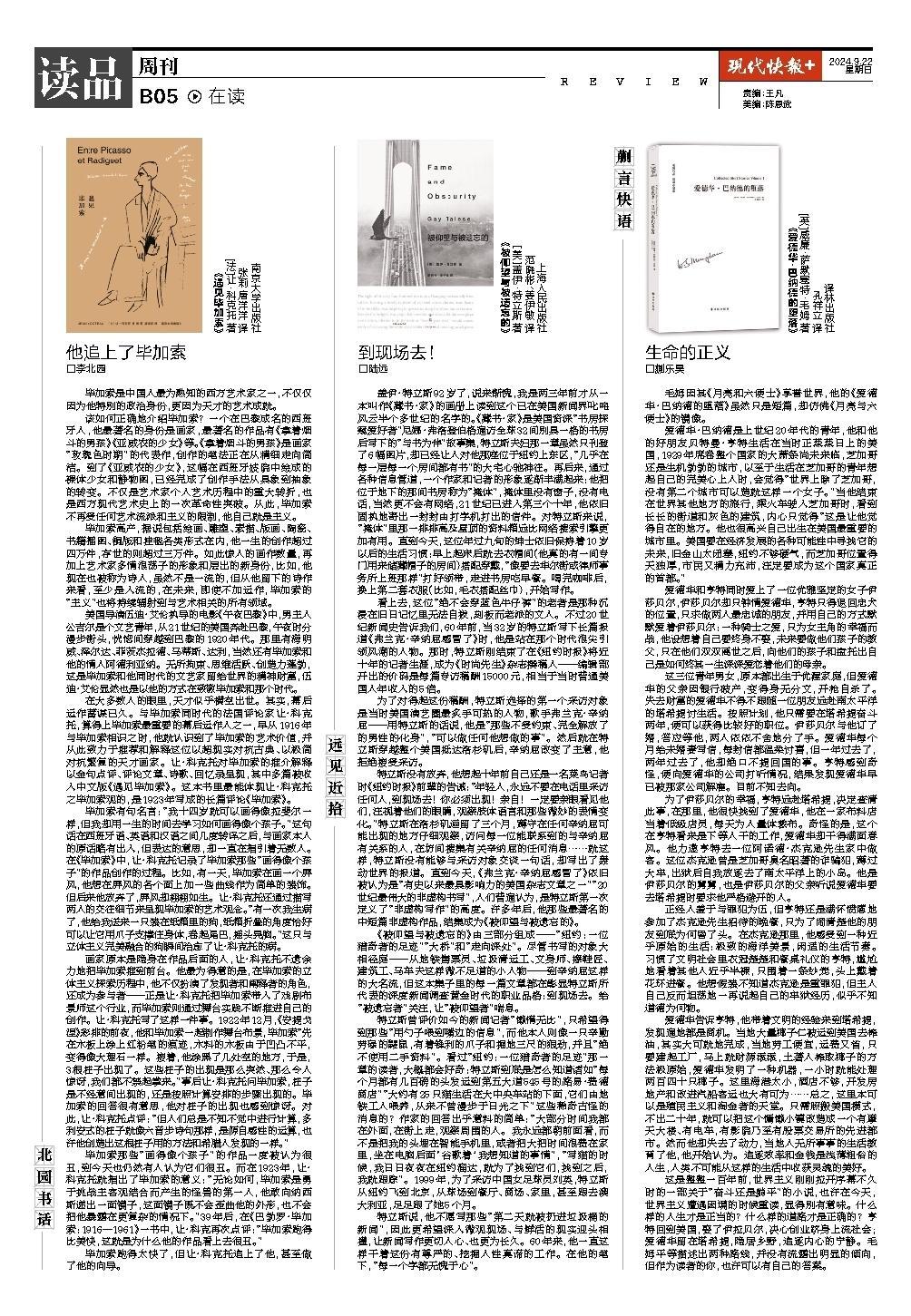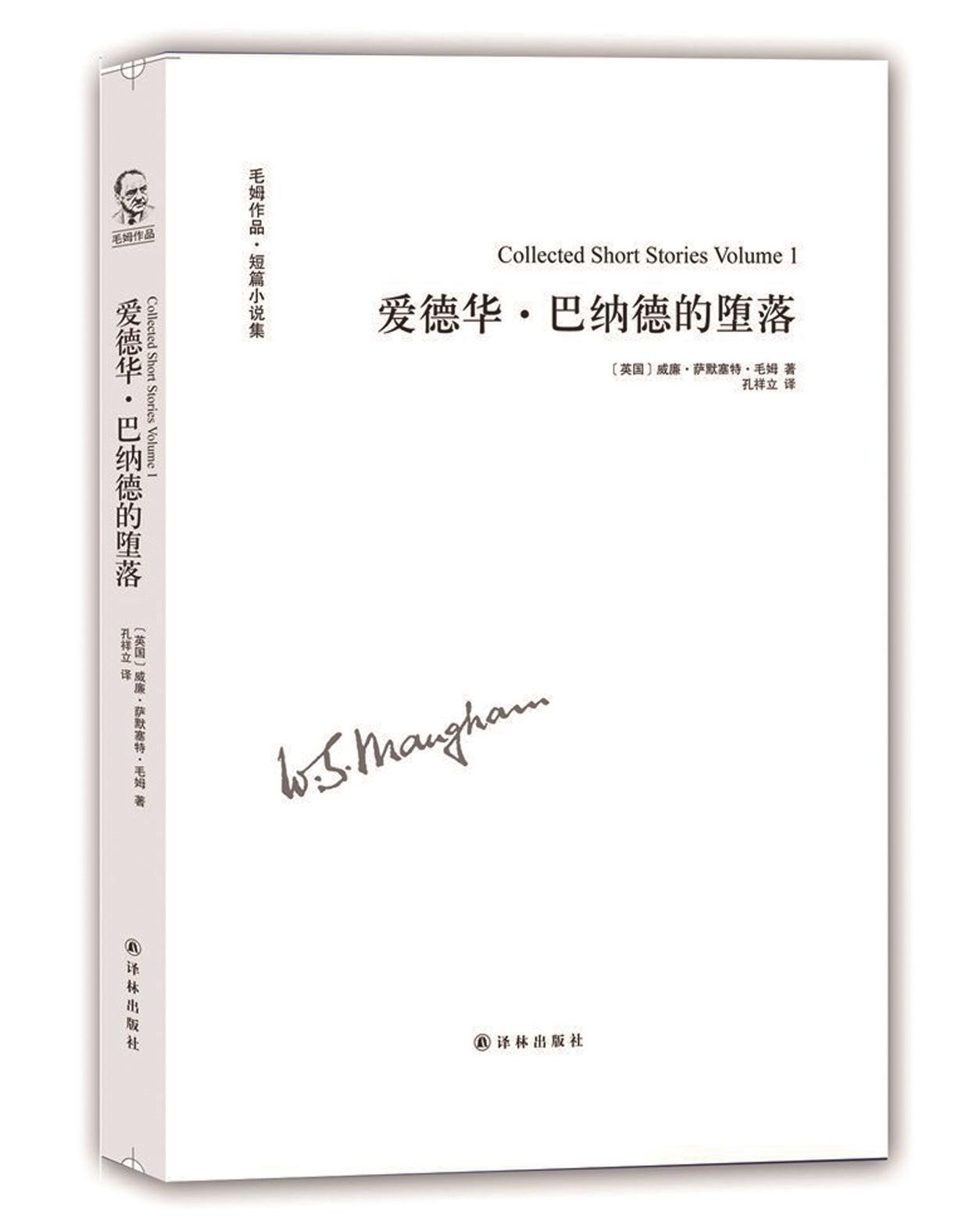□蒯乐昊
毛姆因其《月亮和六便士》享誉世界,他的《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虽然只是短篇,却仿佛《月亮与六便士》的镜像。
爱德华·巴纳德是上世纪20年代的青年,他和他的好朋友贝特曼·亨特生活在当时正蒸蒸日上的美国,1929年席卷整个国家的大萧条尚未来临,芝加哥还是生机勃勃的城市,以至于生活在芝加哥的青年想起自己的完美心上人时,会觉得“世界上除了芝加哥,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造就这样一个女子。”当他结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旅行,乘火车驶入芝加哥时,看到长长的街道和灰色的建筑,内心只觉得“这是让他觉得自在的地方。他也很高兴自己出生在美国最重要的城市里。美国要在经济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中寻找它的未来,旧金山太闭塞,纽约不够硬气,而芝加哥位置得天独厚,市民又精力充沛,注定要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首都。”
爱德华和亨特同时爱上了一位优雅坚定的女子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却只钟情爱德华,亨特只得退回忠犬的位置,只求做两人最忠诚的朋友,并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爱着伊莎贝尔:一种骑士之爱,只为女主角的幸福而战,他设想着自己要终身不娶,未来要做他们孩子的教父,只在他们双双离世之后,向他们的孩子和盘托出自己是如何终其一生深深爱恋着他们的母亲。
这三位青年男女,原本都出生于优渥家庭,但爱德华的父亲因银行破产,变得身无分文,开枪自杀了。失去财富的爱德华不得不跟随一位朋友远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讨生活。按照计划,他只需要在塔希提奋斗两年,便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职位。伊莎贝尔与他订了婚,答应等他,两人依依不舍地分了手。爱德华每个月给未婚妻写信,每封信都温柔讨喜,但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却绝口不提回国的事。亨特感到奇怪,便向爱德华的公司打听情况,结果发现爱德华早已被那家公司解雇。目前不知去向。
为了伊莎贝尔的幸福,亨特远赴塔希提,决定查清此事,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爱德华,他在一家布料店当着低级店员,每天为人量体裁布。奇怪的是,这个在亨特看来是下等人干的工作,爱德华却干得满面春风。他力邀亨特去一位阿诺德·杰克逊先生家中做客。这位杰克逊曾是芝加哥臭名昭著的诈骗犯,蹲过大牢,出狱后自我放逐去了南太平洋上的小岛。他是伊莎贝尔的舅舅,也是伊莎贝尔的父亲听说爱德华要去塔希提时要求他严格避开的人。
正经人羞于与罪犯为伍,但亨特还是满怀愤懑地参加了杰克逊先生招待的晚餐,只为了闹清楚他的朋友到底为何昏了头。在杰克逊那里,他感受到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活:极致的海洋美景,闲适的生活节奏。习惯了文明社会里衣冠楚楚和餐桌礼仪的亨特,尴尬地看着其他人近乎半裸,只围着一条纱笼,头上戴着花环进餐。他想假装不知道杰克逊是重罪犯,但主人自己反而坦荡地一再说起自己的牢狱经历,似乎不知道德为何物。
爱德华告诉亨特,他带着文明的经验来到塔希提,发现遍地都是商机。当地大量椰子仁被运到美国去榨油,其实大可就地完成,当地劳工便宜,运费又省,只要建起工厂,马上就财源滚滚,土著人榨取椰子的方法极原始,爱德华发明了一种机器,一小时就能处理两百四十只椰子。这里海港太小,酒店不够,开发房地产和改进汽船客运也大有可为……总之,这里本可以是殖民主义和淘金者的天堂。只需照搬美国模式,不出二十年,就可以把这个慵懒小镇改造成一个有摩天大楼、有电车,有影院乃至有股票交易所的先进都市。然而他却失去了动力,当地人无所事事的生活教育了他,他开始认为。追逐效率和金钱是浅薄粗俗的人生,人类不可能从这样的生活中收获灵魂的美好。
这是整整一百年前,世界主义刚刚拉开序幕不久时的一部关于“奋斗还是躺平”的小说,也许在今天,世界主义遭遇困境的时候重读,显得别有意味。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正当的?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亨特回到美国,娶了伊拉贝尔,决心创业跻身上流社会;爱德华留在塔希提,隐居乡野,追逐内心的宁静。毛姆平等描述出两种路线,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倾向,但作为读者的你,也许可以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