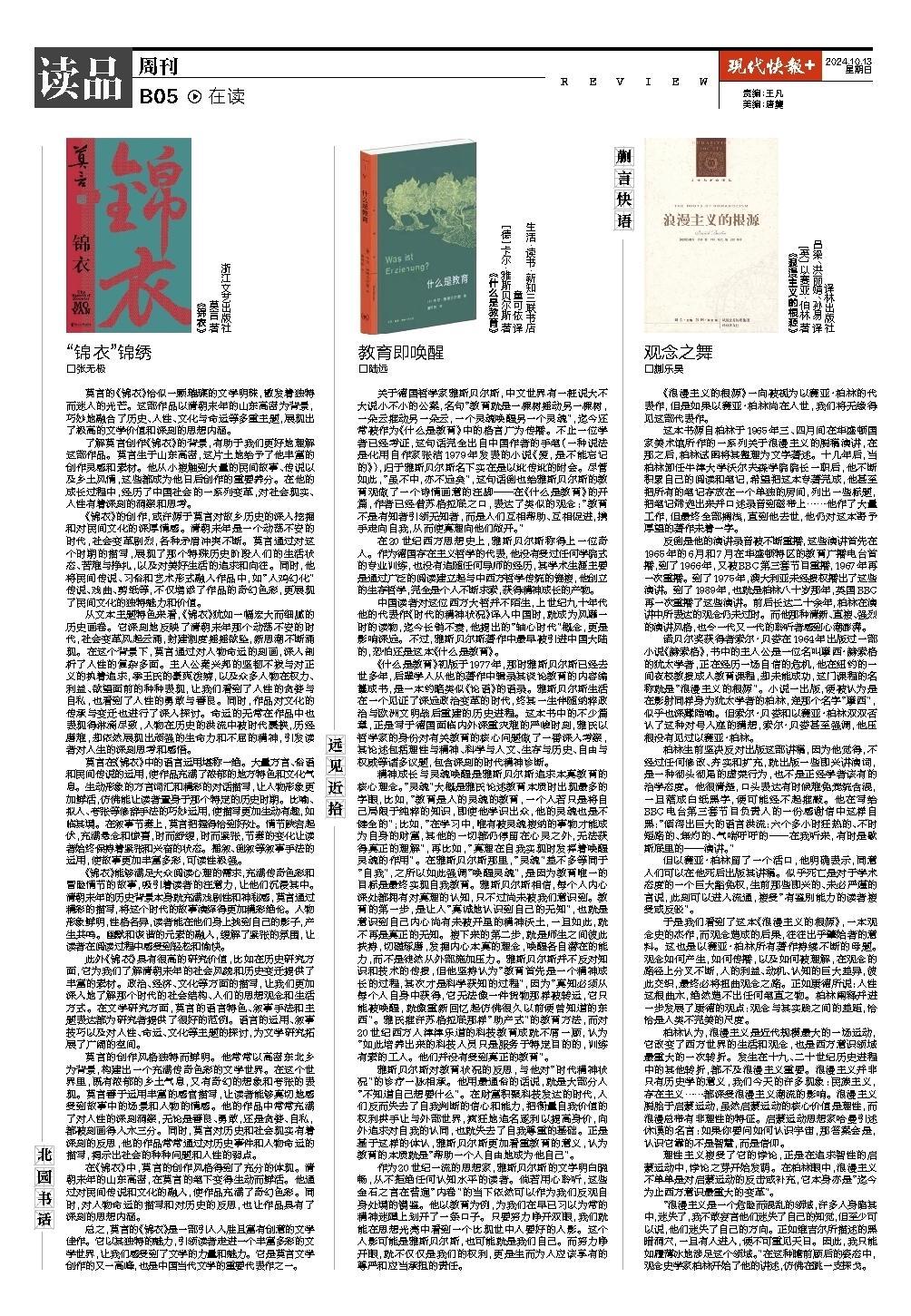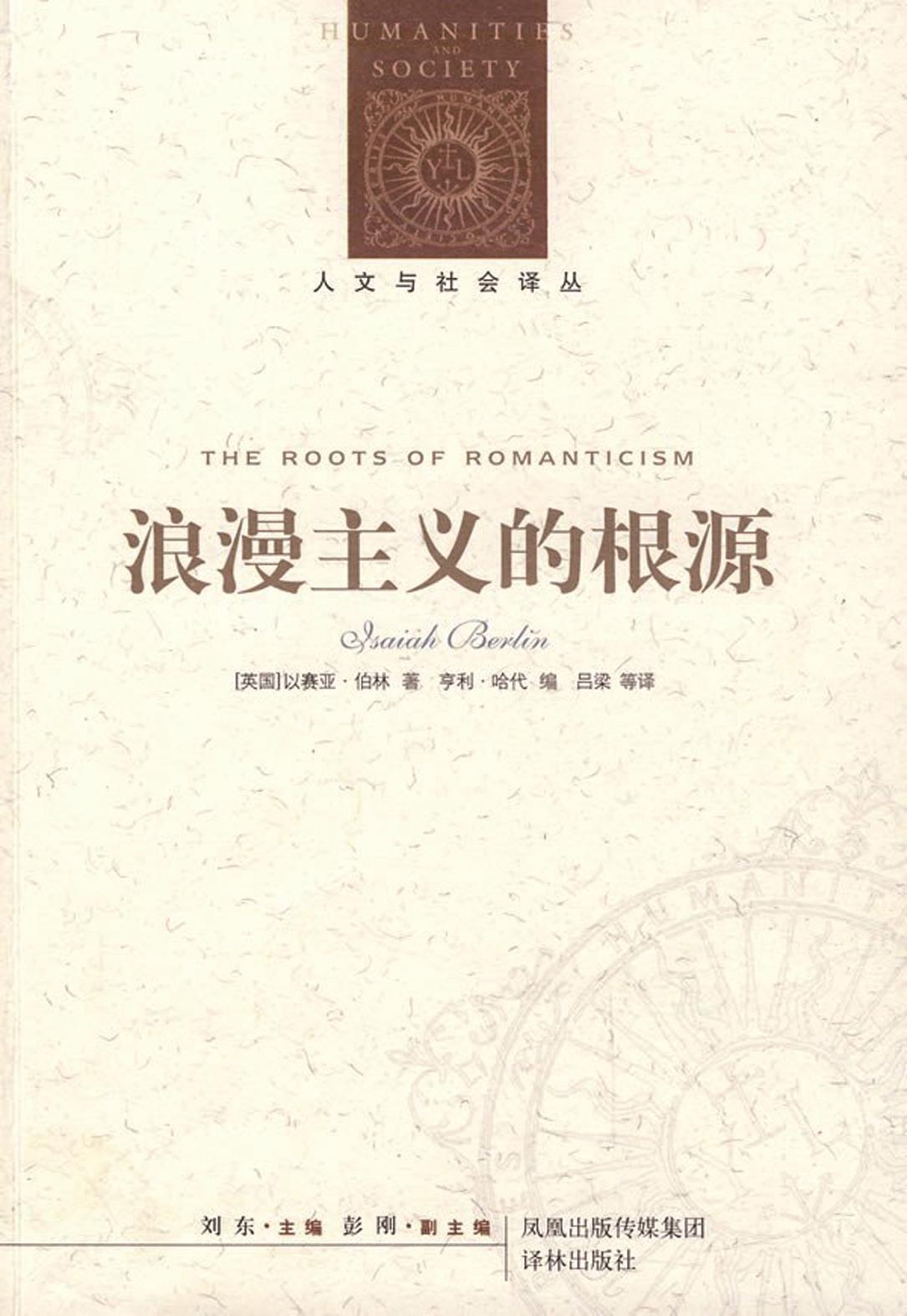□蒯乐昊
《浪漫主义的根源》一向被视为以赛亚·柏林的代表作,但是如果以赛亚·柏林尚在人世,我们将无缘得见这部代表作。
这本书源自柏林于1965年三、四月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所作的一系列关于浪漫主义的脱稿演讲,在那之后,柏林试图将其整理为文字著述。十几年后,当柏林卸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一职后,他不断积累自己的阅读和笔记,希望把这本专著完成,他甚至把所有的笔记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列出一些标题,把笔记筛选出来并口述录音到磁带上……他作了大量工作,但最终全部搁浅,直到他去世,他仍对这本寄予厚望的著作未着一字。
反倒是他的演讲录音被不断重播,这些演讲首先在1965年的6月和7月在华盛顿特区的教育广播电台首播,到了1966年,又被BBC第三套节目重播,1967年再一次重播。到了1975年,澳大利亚未经授权播出了这些演讲。到了1989年,也就是柏林八十岁那年,英国BBC再一次重播了这些演讲。前后长达二十余年,柏林在演讲中所表达的观念仍未过时。而他那种清新、直接、强烈的演讲风格,也令一代又一代的聆听者感到心潮澎湃。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1964年出版过一部小说《赫索格》,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摩西·赫索格的犹太学者,正在经历一场自信的危机,他在纽约的一间夜校教授成人教育课程,却未能成功,这门课程的名称就是“浪漫主义的根源”。小说一出版,便被认为是在影射同样身为犹太学者的柏林,连那个名字“摩西”,似乎也深藏隐喻。但索尔·贝娄和以赛亚·柏林双双否认了这种对号入座的猜想,索尔·贝娄甚至强调,他压根没有见过以赛亚·柏林。
柏林生前坚决反对出版这部讲稿,因为他觉得,不经过任何修改、夯实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讲演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荣行为,也不是正经学者该有的治学态度。他很清楚,口头表达有时候难免笼统含混,一旦落成白纸黑字,便可能经不起推敲。他在写给BBC电台第三套节目负责人的一份感谢信中这样自黑:“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演讲。”
但以赛亚·柏林留了一个活口,他明确表示,同意人们可以在他死后出版其讲稿。似乎死亡是对于学术态度的一个巨大豁免权,生前那些即兴的、未必严谨的言说,此刻可以进入流通,接受“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本《浪漫主义的根源》,一本观念史的杰作,而观念造成的后果,往往出乎肇始者的意料。这也是以赛亚·柏林所有著作持续不断的母题。观念如何产生,如何传播,以及如何被理解,在观念的路径上分叉不断,人的利益、动机、认知的巨大差异,彼此交织,最终必将扭曲观念之路。正如康德所说: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之物。柏林阐释并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观点:观念与其实践之间的差距,恰恰是人类不完美的尺度。
柏林认为,浪漫主义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它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也是西方意识领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浪漫主义并非只有历史学的意义,我们今天的许多现象:民族主义,存在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浪漫主义脱胎于启蒙运动,虽然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是理性,而浪漫总带有非理性的特征。启蒙运动思想家哈曼引述休谟的名言:如果你要问如何认识宇宙,那答案会是,认识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
理性主义接受了它的悖论,正是在追求智性的启蒙运动中,悖论之芽开始发萌。在柏林眼中,浪漫主义不单单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击或补充,它本身亦是“迄今为止西方意识最重大的变革”。
“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而混乱的领域,许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们迷失了自己的知觉,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维吉尔所描述的黑暗洞穴,一旦有人进入,便不可重见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地涉足这个领域。”在这种瞻前顾后的姿态中,观念史学家柏林开始了他的讲述,仿佛在跳一支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