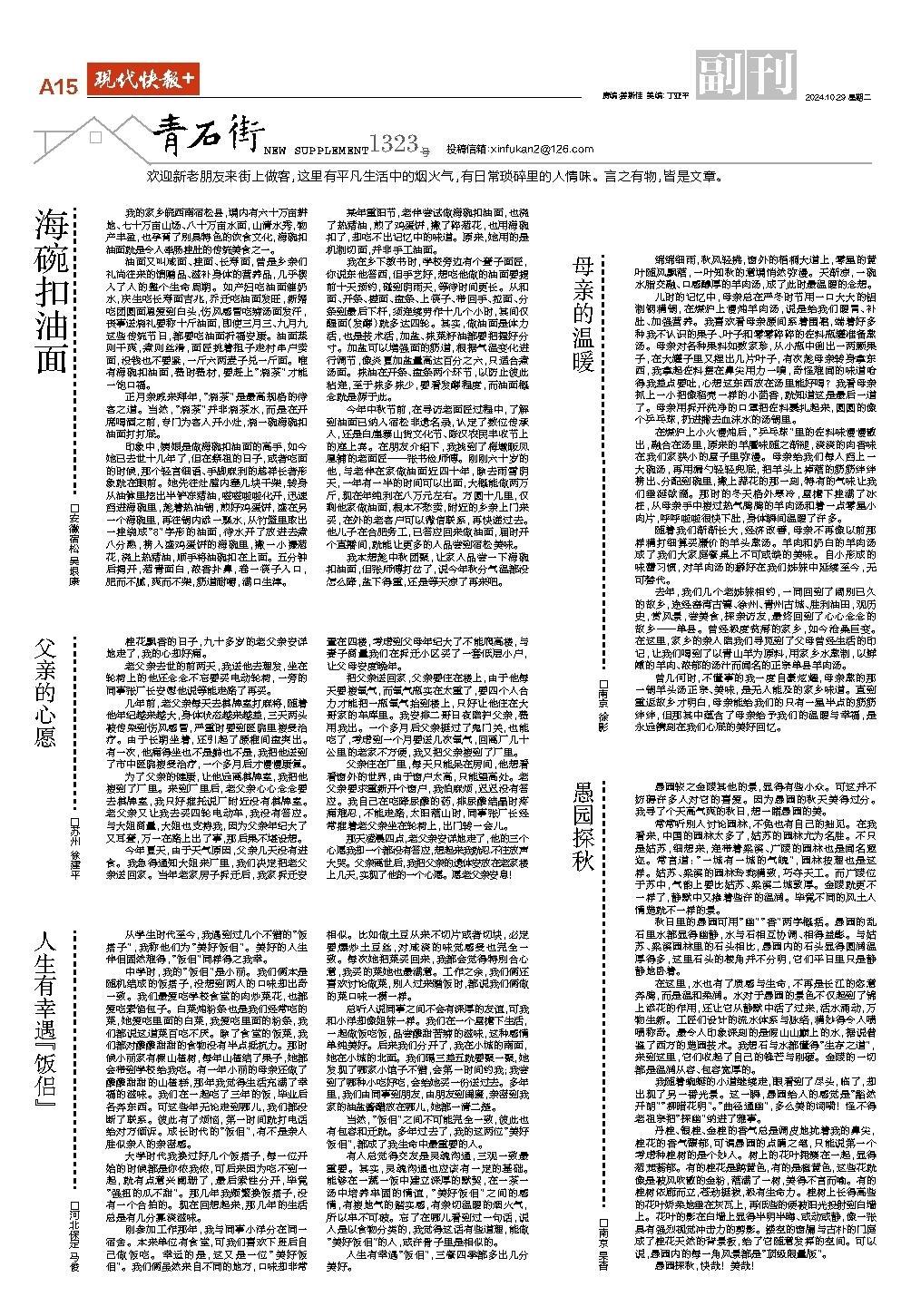□安徽宿松 吴垠康
我的家乡皖西南宿松县,境内有六十万亩耕地、七十万亩山场、八十万亩水面,山清水秀,物产丰盈,也孕育了别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海碗扣油面就是令人牵肠挂肚的传统美食之一。
油面又叫咸面、挂面、长寿面,曾是乡亲们礼尚往来的馈赠品、滋补身体的营养品,几乎楔入了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如产妇吃油面催奶水,庆生吃长寿面吉兆,乔迁吃油面发旺,新婚吃团圆面恩爱到白头,伤风感冒吃辣汤面发汗,丧事送烧礼要称十斤油面,即使三月三、九月九这些传统节日,都要吃油面祈福安康。油面蒸则干爽,煮则丝滑,面匠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面,没钱也不要紧,一斤六两麦子兑一斤面。唯有海碗扣油面,费时费材,要赶上“烧茶”才能一饱口福。
正月亲戚来拜年,“烧茶”是最高规格的待客之道。当然,“烧茶”并非烧茶水,而是在开席喝酒之前,专门为客人开小灶,烧一碗海碗扣油面打打底。
印象中,姨娘是做海碗扣油面的高手,如今她已去世十几年了,但在祭祖的日子,或者吃面的时候,那个轻言细语、手脚麻利的慈祥长者形象就在眼前。她先往灶膛内塞几块干柴,转身从油钵里挖出半铲冻猪油,嗞嗞啦啦化开,迅速舀进海碗里,趁着热油锅,煎好鸡蛋饼,盛在另一个海碗里,再往锅内添一瓢水,从竹篮里取出一挂绕成“8”字形的油面,待水开了放进去煮八分熟,捞入盛鸡蛋饼的海碗里,撒一小撮葱花,浇上热猪油,顺手将油碗扣在上面。五分钟后揭开,葱青面白,浓香扑鼻,卷一筷子入口,肥而不腻,爽而不柴,筋道耐嚼,满口生津。
某年重阳节,老伴尝试做海碗扣油面,也浇了热猪油,煎了鸡蛋饼,撒了碎葱花,也用海碗扣了,却吃不出记忆中的味道。原来,她用的是机制切面,并非手工油面。
我在乡下教书时,学校旁边有个聋子面匠,你说东他答西,但手艺好,想吃他做的油面要提前十天预约,碰到阴雨天,等待时间更长。从和面、开条、搓面、盘条、上筷子、带回手、拉面、分条到最后下杆,须连续劳作十几个小时,其间仅醒面(发酵)就多达四轮。其实,做油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加盐、抹菜籽油都要把握好分寸。加盐可以增强面的筋道,根据气温变化进行调节,像炎夏加盐量高达百分之六,只适合煮汤面。抹油在开条、盘条两个环节,以防止彼此粘连,至于抹多抹少,要看发酵程度,而油面概念就是源于此。
今年中秋节前,在寻访老面匠过程中,了解到油面已纳入宿松非遗名录,认定了数位传承人,还是白崖寨山货文化节、陈汉农民丰收节上的座上宾。在朋友介绍下,我找到了梅墩畈凤凰铺的老面匠——张书俭师傅。刚刚六十岁的他,与老伴在家做油面近四十年,除去雨雪阴天,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可以出面,大概能做两万斤,现在年纯利在八万元左右。方圆十几里,仅剩他家做油面,根本不愁卖,附近的乡亲上门来买,在外的老客户可以微信联系,再快递过去。他儿子在合肥务工,已答应回来做油面,届时开个直播间,就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宿松美味。
我本想趁中秋团聚,让家人品尝一下海碗扣油面,但张师傅打岔了,说今年秋分气温都没怎么降,盐下得重,还是等天凉了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