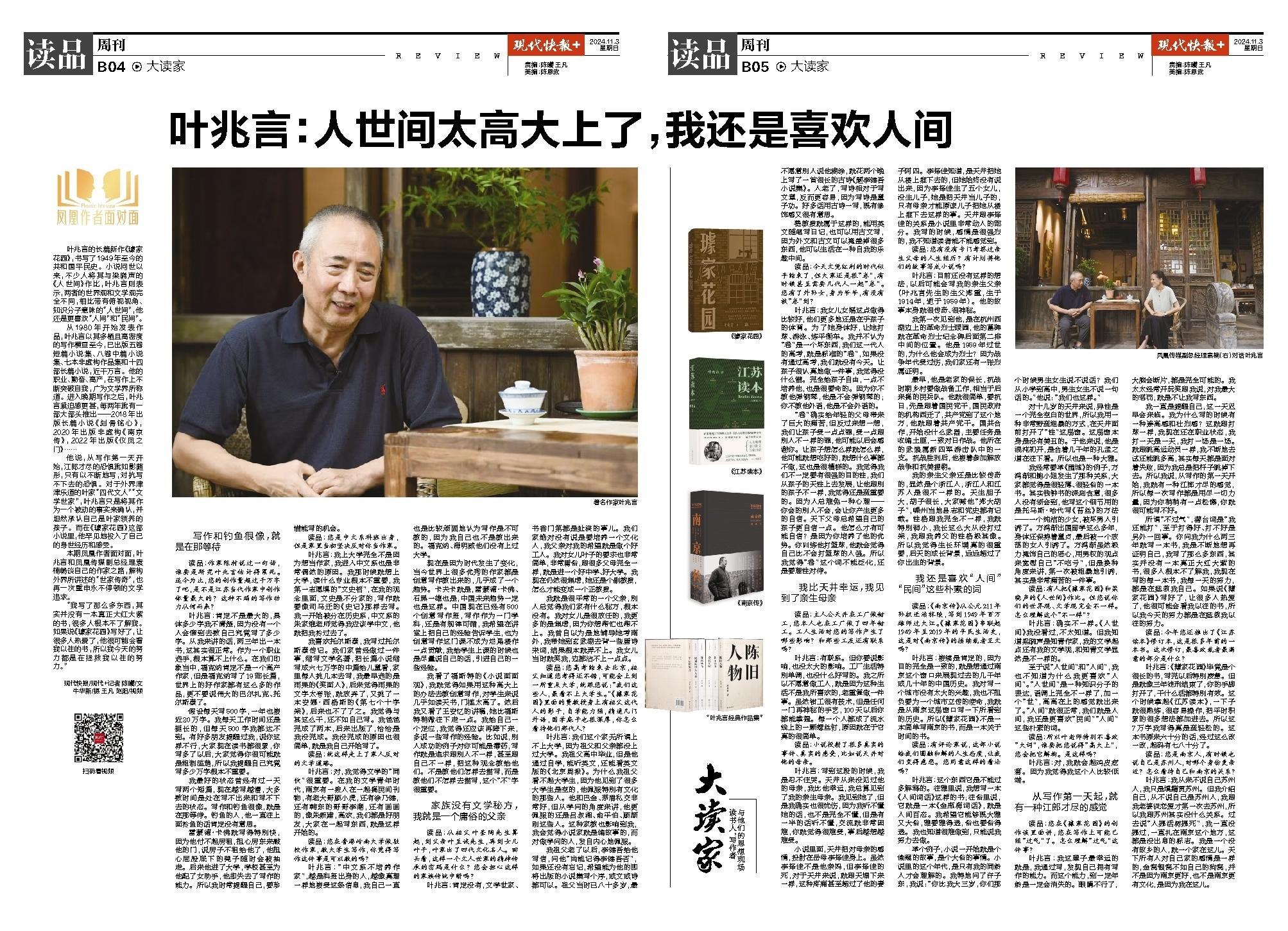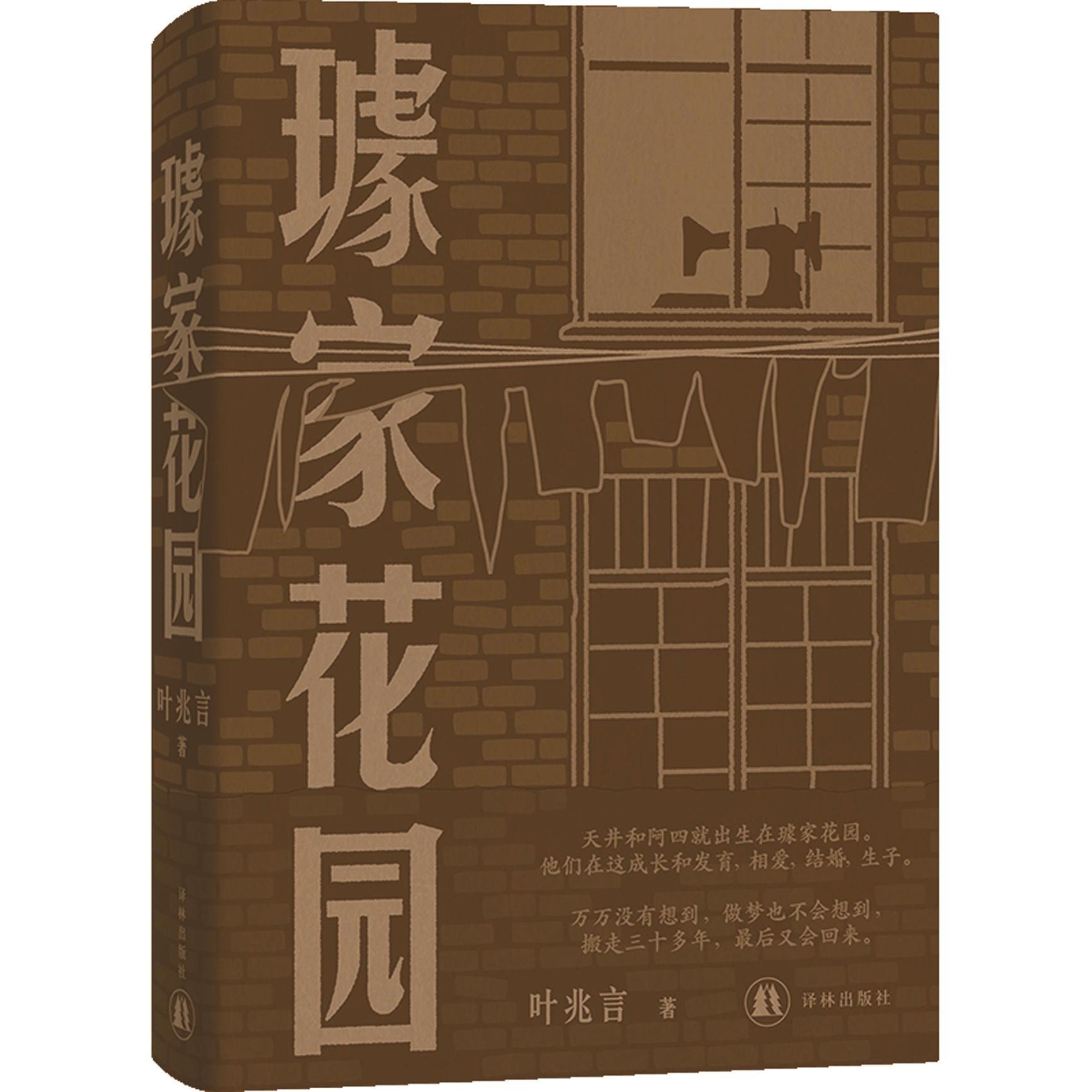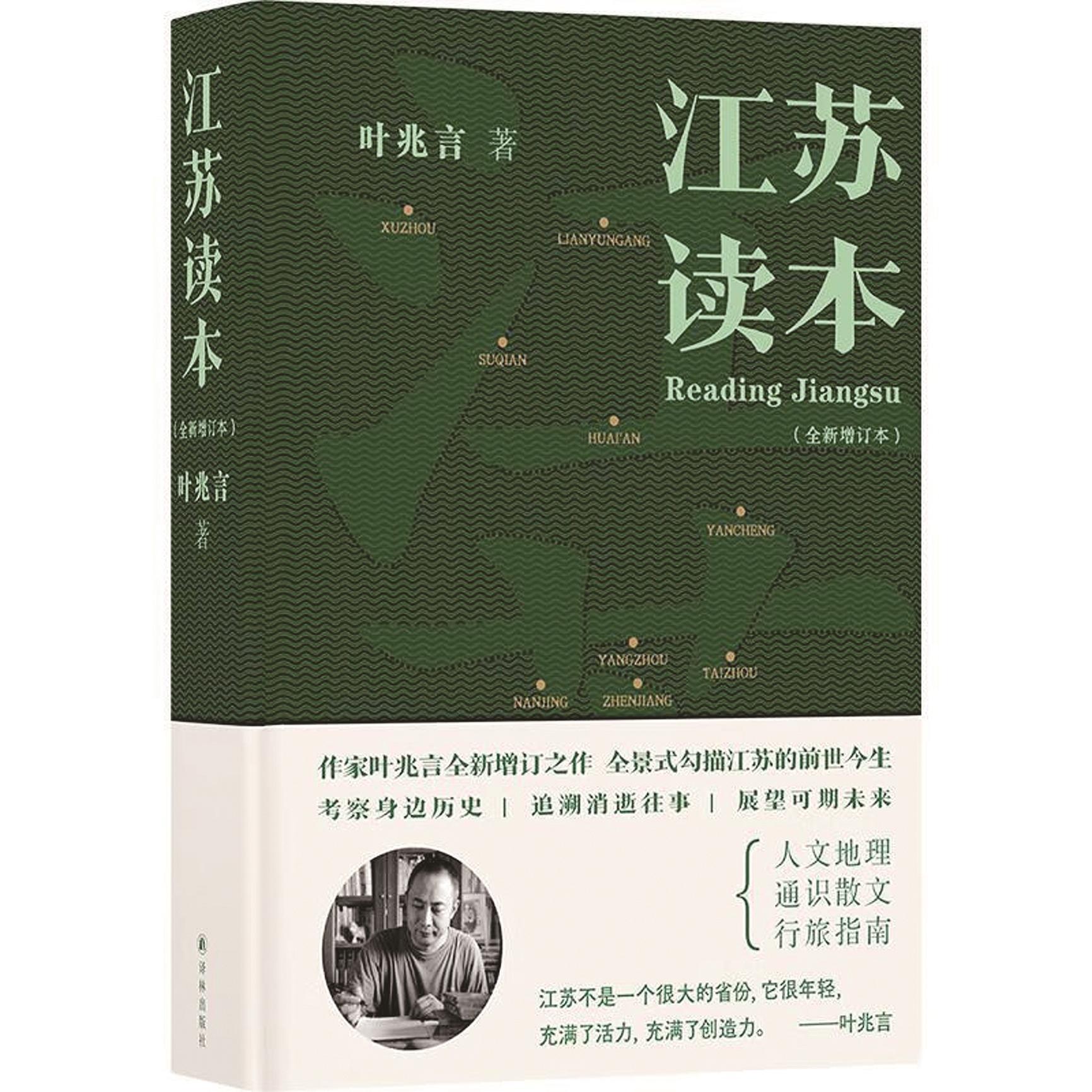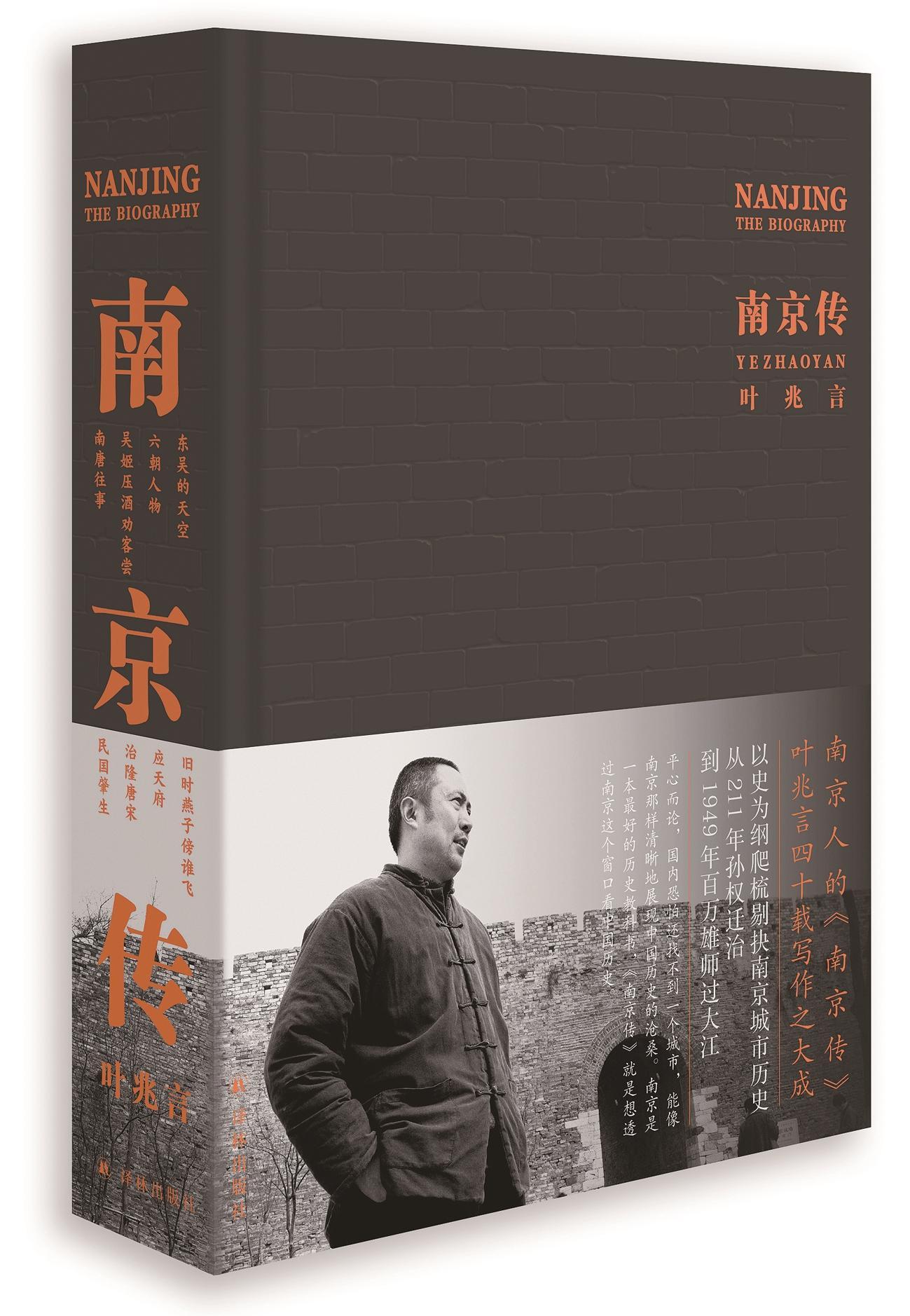叶兆言的长篇新作《璩家花园》,书写了1949年至今的共和国平民史。小说问世以来,不少人将其与梁晓声的《人世间》作比,叶兆言则表示,两者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完全不同,相比带有俯视视角、知识分子意味的“人世间”,他还是更喜欢“人间”和“民间”。
从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叶兆言以其多栖且高密度的写作横亘至今,已出版五卷短篇小说集、八卷中篇小说集、七本非虚构作品集和十四部长篇小说,近千万言。他的职业、勤奋、高产,在写作上不断突破自我,广为文学界所称道。进入晚期写作之后,叶兆言紧迫感更甚,每两年就有一部大部头推出——2018年出版长篇小说《刻骨铭心》,2020年出版非虚构《南京传》,2022年出版《仪凤之门》……
他说,从写作第一天开始,江郎才尽的恐惧就如影随形,只有以不断地写,对抗写不下去的恐惧。对于外界津津乐道的叶家“四代文人”“文学世家”,叶兆言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被动的事实来确认,并坦然承认自己是叶家领养的孩子。而在《璩家花园》这部小说里,他罕见地投入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和感受。
本期凤凰作者面对面,叶兆言和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袁楠畅谈自己的作家之路,解构外界所讲述的“世家传奇”,也再一次重申永不停顿的文学追求。
“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一本真正大红大紫的书,很多人根本不了解我。如果说《璩家花园》写好了,让很多人热爱了,他很可能会看我以往的书,所以我今天的努力都是在拯救我以往的努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文
牛华新/摄 王凡 赵阳/视频
写作和钓鱼很像,就是在那等待
读品:作家陈村说过一句话,谁要是研究叶兆言估计得累死。迄今为止,您的创作量超过千万字了吧,是不是江苏当代作家中创作体量最大的?这种不竭的写作动力从何而来?
叶兆言:肯定不是最大的,具体多少字我不清楚,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傻到去数自己究竟写了多少字。从我来讲的话,两三年出一本书,这其实很正常。作为一个职业选手,根本算不上什么。在我们印象当中,福克纳肯定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但是福克纳写了19部长篇,世界上的好作家都有这么多的作品,更不要说伟大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了。
假设每天写500字,一年也接近20万字。我每天工作时间还是挺长的,但每天500字我都达不到。有好多朋友提醒过我,说你这样不行,大家现在读书都很累,你写多了以后,大家觉得你很可能就是粗制滥造,所以我提醒自己究竟写多少万字根本不重要。
我最好的状态曾经有过一天写两个短篇,现在越写越慢,大多数时间是处在写不出来和写不下去的状态。写作和钓鱼很像,就是在那等待。钓鱼的人,他一直往上面拎鱼的话肯定没有意思。
雷蒙德·卡佛就写得特别快,因为他付不起房租,担心房东来敲他的门,说房子不租给他了,他担心屁股底下的凳子随时会被抽走。后来他进了大学,学校甚至为他配了女助手,他却失去了写作的能力。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要珍惜能写的机会。
读品:您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是家里当初坚决反对你当作家。
叶兆言:我上大学完全不是因为想当作家,我进入中文系也是非常偶然的原因。我那时候就想上大学,读什么专业根本不重要,我第一志愿填的“文史哲”,在我的观念里面,文史是不分家的,写作就要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去写。我一开始被分在历史系,中文系的朱家维老师觉得我应该学中文,他就把我拎过去了。
我喜欢托尔斯泰,我写过托尔斯泰传记。我们家曾经做过一件事,缩写文学名著,把长篇小说缩写成六七万字的中篇给儿童看,家里每人挑几本去写,我最早选的是雨果的《笑面人》,后来觉得雨果的文字太夸张,就放弃了,又挑了一本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后来也不了了之。我觉得与其这么干,还不如自己写。我爸爸完成了两本,后来出版了,恰恰是我没完成。我没完成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开始写了。
读品:就这样走上了家人反对的文学道路。
叶兆言:对,我觉得文学的“同伙”很重要。在我的文学青年时代,南京有一拨人在一起搞民间刊物,有老大哥顾小虎,还有徐乃健,还有韩东的哥哥李潮,还有画画的,像朱新建,高欢,我们都是好朋友,大家在一起写东西,就是这样开始的。
读品:您在香港岭南大学做驻校作家,教大学生写作,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是可以教的吗?
叶兆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越是科班出身的人,越像真理一样地接受这条信息,我自己一直也是比较顽固地认为写作是不可教的,因为我自己也不是教出来的。福克纳、海明威他们没有上过大学。
现在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当今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是创意写作教出来的,几乎成了一个趋势。卡夫卡就是,雷蒙德·卡佛、石黑一雄也是,中国未来趋势一定也是这样。中国现在已经有500个创意写作班,写作作为一门学科,还是有规律可循,我希望在讲堂上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学生,也为创意写作这门课不成为烂尾楼作一点贡献,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也是尽量说自己的话,引进自己的一些经验。
我看了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我就觉得如果用这种高大上的办法去教创意写作,对学生来说几乎如读天书,门槛太高了。然后我又看了王安忆的讲稿,她比福斯特稍微往下走一点。我给自己一个定位,我觉得还应该再降下来,多说一些写作的经验。比如说,别人成功的例子对你可能是毒药,写作就是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甚至跟自己不一样,把这种观念教给他们。不是教他们怎样去描写,而是教他们不怎样去描写,这个“不”字很重要。
家族没有文学秘方,我就是一个庸俗的父亲
读品:从祖父叶圣陶先生算起,到父亲叶至诚先生,再到女儿叶子,叶家出了四代文化名人。回头看,这样一个文人世家的精神传承的密码是什么?您会担心这样的家族传统中断吗?
叶兆言:肯定没有,文学世家、书香门第都是扯淡的事儿。我们家绝对没有说是要培养一个文化人,我父亲对我的希望就是做个好工人。我对女儿叶子的要求也非常简单,非常庸俗,跟很多父母完全一样,就是进一个好中学、好大学。我现在仍然很焦虑,她还是个副教授,怎么才能变成一个正教授。
我就是很平常的一个父亲,别人总觉得我们家有什么秘方,根本没有。我对女儿是很放任的,我更多的是焦虑,因为你想帮忙也帮不上。我曾自以为是地辅导她考南外,我带她到玄武湖去背一些唐诗宋词,结果根本就弄不上。我女儿当时就笑我,边都沾不上一点点。
读品:您高考结束去北京,祖父知道您考得还不错,可能会上到一所重点大学,就跟您说:“我们这些人,最看不上大学生。”《璩家花园》里面的费教授身上有祖父这代人的影子,自学能力强,精通几门外语,国学底子也很深厚,你怎么看待他们那代人?
叶兆言:我们这个家无所谓上不上大学,因为祖父和父亲都没上过大学。我祖父高中毕业,但是他通过自学,能听英文,还能看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为什么我祖父看不起大学生,因为他见到了很多大学生是空的,他佩服特别有文化的那些人。他和巴金、茅盾私交非常好,但从学问的角度来讲,他更佩服的还是吕叔湘、俞平伯、顾颉刚这些人。这种家教也影响到我,我会觉得小说家就是编故事的,而对做学问的人,发自内心地佩服。
我祖父老了以后,李健吾给他写信,问他“尚能记得李健吾否”,如果还没有忘记,希望能为他的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写个序,或文或诗都可以。祖父当时已八十多岁,最
不愿意别人说他糊涂,就花两个晚上写了一首很长的古诗《题李健吾小说集》。人老了,写诗相对于写文章,反而更容易,因为写诗是童子功。好多话用古诗一写,既有修饰感又很有意思。
费教授就属于这样的,能用英文随笔写日记,也可以用古文写,因为外文和古文可以掩盖掉很多东西,他可以生活在一种自我的乐趣中间。
读品:今天文凭红利的时代似乎结束了,但大家还是很“卷”,有时候甚至需要几代人一起“卷”。您有了外孙女,身为爷爷,有没有被“卷”到?
叶兆言:我女儿女婿这点做得比较好,他们更多地还是在乎孩子的体育。为了她身体好,让她打球、游泳、练平衡车。我并不认为“卷”是一个坏东西,我们这一代人的高考,就是标准的“卷”,如果没有通过高考,我们就没有今天。让孩子很认真地做一件事,我觉得没什么错。完全给孩子自由,一点不培养他,也是很要命的。因为你不教他弹钢琴,他是不会弹钢琴的;你不教他外语,他是不会外语的。
“卷”确实给年轻的父母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反过来想一想,我们让孩子受一点点罪,受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罪,他可能以后会感谢你。让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可能就想吃好的,就想什么事都不做,这也是很糟糕的。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有很强的目的性,我们从孩子的天性上去发展,让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人总难免一种心理——你会的别人不会,会让你产生更多的自信。天下父母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更自信一点。他怎么才有可能自信?是因为你培养了他的优势。你训练他打篮球,他就会觉得自己比不会打篮球的人强。所以我觉得“卷”这个词不能泛化,还是要理性对待。
我比天井幸运,我见到了亲生母亲
读品:主人公天井在工厂做钳工,您本人也在工厂做了四年钳工。工人生活对您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和那些工友还有联系吗?
叶兆言:有联系。但你要说影响,也没太大的影响。工厂生活特别单调,也没什么好写的。我之所以不愿意做工人,就是因为这种生活不是我所喜欢的,老重复做一件事。虽然钳工很有技术,但是任何一门再神秘的手艺,100天以后你都能掌握。每一个人都成了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原因就在于它真的很简单。
读品:小说投射了很多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感受,比如说天井对他的母亲。
叶兆言:写到这段的时候,我是忍不住哭。天井从来没见过他的母亲,我比他幸运,我总算见到了我的亲生母亲。我见到她了,但是我确实也很忧伤,因为我听不懂她的话,也不是完全不懂,但是有一半的话听不懂,交流就非常困难,你就觉得很难受,事后越想越难受。
小说里面,天井把对母亲的感情,投射在岳母李择佳身上。虽然李择佳不是他亲妈,但李择佳的死,对于天井来说,就跟天塌下来一样,这种疼痛甚至超过了他的妻子阿四。李择佳知道,是天井把她从楼上推下去的,但她始终没有说出来,因为李择佳生了五个女儿,没生儿子,她是把天井当儿子的,只有母亲才能原谅儿子把她从楼上推下去这样的事。天井跟李择佳的关系是小说里非常动人的部分。我写的时候,感情是很强烈的,我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感觉到。
读品:您有没有专门考察过亲生父母的人生经历?有计划将他们的故事写成小说吗?
叶兆言: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以后可能会写我的亲生父亲(叶兆言先生的生父郑重,生于1914年,逝于1959年)。他的故事本身就很传奇、很神秘。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革命烈士陵园,他的墓碑就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后面第二排中间的位置。他是1959年过世的,为什么他会成为烈士?因为战争年代受过伤,我们家还有一张烈属证明。
最早,他是老家的保长,抗战时期乡村要做战备工作,相当于后来搞的民兵队。他就很简单,要抗日,先是跟着国民党干,国民政府的机构西迁了,共产党到了这个地方,他就跟着共产党干。国共合作,开始没什么武器,主要任务是收编土匪,一致对日作战。他所在的武装属新四军游击队中的一支。抗战胜利后,他接着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我的亲生父亲还是比较传奇的,显然是个浙江人,浙江人和江苏人是很不一样的。天生胆子大,胡子很长,大家喊他“郑大胡子”,嵊州当地县志和党史都有记载。性格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就特别弱小,我长这么大从没打过架,我跟我养父的性格极其像。所以我觉得生长环境真的很重要,后天的成长背景,远远超过了你出生的背景。
我还是喜欢“人间”“民间”这些朴素的词
读品:《南京传》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秣陵,写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璩家花园》串联起1949年至2019年的平民生活史,这是对《南京传》的接续或者互文吗?
叶兆言:接续是肯定的,因为目的完全是一致的,就是想通过南京这个窗口来展现过去的几千年或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我对写一个城市没有太大的兴趣,我也不担负要为一个城市立传的使命,我就是从南京这扇窗口写一下所看到的历史。所以《璩家花园》不是一本简单写南京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时间的书。
读品: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给我们圆融和解的人生态度,让我们变得慈悲。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叶兆言:这个东西它是不能过多解释的。往雅里说,我想写一本《人间词话》这样的书;往俗里说,它就是一本《金瓶梅词话》,就是人间百态。我希望它能够既大雅又大俗,雅要雅得透,俗也要俗得透。我也知道很难做到,只能说我努力去做。
举个例子,小说一开始就是个偷窥的故事,是个大俗的事情。小说里的这个年代,是只有我的同龄人才会理解的。我特地问了许子东,我说:“你比我大三岁,你们那个时候男生女生说不说话?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男生女生不说一句话的。”他说:“我们也这样。”
对十几岁的天井来说,异性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世界,所以我用一种非常野蛮粗暴的方式,在天井面前打开了“性”这扇窗。这扇窗本身是没有美丑的。于他来说,他是混沌初开,是合着几千年的孔孟之道在往下看。所以也是一种大雅。
我经常要举《围城》的例子,方鸿渐和鲍小姐发生了那种关系,大家都觉得是很轻薄、很轻俗的一本书。其实钱钟书的深刻含意,很多人没有领会到,他写这个细节用的是托马斯·哈代写《苔丝》的方法——一个纯洁的少女,被坏男人引诱了。方鸿渐出国留学这么多年,身体还保持着童贞,最后被一个放荡的女人引诱了。方鸿渐虽然极力掩饰自己的恶心,用男权的观点来宽慰自己“不吃亏”,但是换种角度来讲,第一次被粗暴地引诱,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读品:有人把《璩家花园》和梁晓声的《人世间》作比。但您说你们的世界观、文学观完全不一样。怎么理解这个“不一样”?
叶兆言:确实不一样。《人世间》我没看过,不太知道。但我知道梁晓声是知青作家,我的文学起点还有我的文学观,和知青文学显然是不一样的。
至于说“人世间”和“人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喜欢“人间”。“人世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语调上完全不一样了,加一个“世”,高高在上的感觉就出来了。“人间”就很正常,我们就是人间,我还是更喜欢“民间”“人间”这些朴素的词。
读品:所以叶老师特别不喜欢“大词”,谁要把您说得“高大上”,您会把它解构。是这样吗?
叶兆言:对,我就会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低端。
从写作第一天起,就有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
读品:您在《璩家花园》的创作谈里面讲,您在写作上可能已经“过气”了。怎么理解“过气”这件事?
叶兆言: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我通过写,发现自己拥有写作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到一定年龄是一定会消失的。眼睛不行了,大脑会断片,都是完全可能的。我太太经常开玩笑跟我说,对我最大的惩罚,就是不让我写东西。
我一直是提醒自己,这一天迟早会来临。我为什么写的时候有一种崇高感和壮烈感?这就跟打球一样,我现在还在职业状态,我打一天是一天,我打一场是一场。就跟跳高运动员一样,我不断地去试还能跳多高,其实每天都是面对着失败,因为我总是把杆子跳掉下去。所以我说,从写作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有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所以每一次写作都是用尽一切力量,因为你稍稍有一点松懈,你就很可能写不好。
所谓“不过气”,潜台词是“我还能打”,至于打得好、打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你问我为什么两三年就写一本书,我是不断地想再证明自己,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其实并没有一本真正大红大紫的书,很多人根本不了解我,我现在写的每一本书,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是在拯救我自己。如果说《璩家花园》写好了,让很多人热爱了,他很可能会看我以往的书,所以我今天的努力都是在拯救我以往的努力。
读品:今年您还推出了《江苏读本》修订本,这是很多年前的一本书。这次修订,最喜欢或者最满意的部分是什么?
叶兆言:《璩家花园》毕竟是个很长的书,写完以后特别疲惫。但是就像三年徒刑结束了,你的手脚打开了,干什么活都特别有效。这个时候拿起《江苏读本》,一下子就很熟练,很容易操作,把平时积累的很多想法都加进去。所以这7万字我写得真是蛮轻松的。这本书原来六十分的话,经过这么改一改,起码有七八十分了。
读品:您是南京人,有时候也说自己是苏州人,对哪个身份更亲近?怎么看待自己和南京的关系?
叶兆言:我从来不说自己苏州人,我只是填籍贯苏州。但我介绍自己,从不说自己是苏州人,我跟我老婆谈恋爱才第一次去苏州,所以我跟苏州其实没什么关系。过去说“人挪活树挪死”,我一直没挪过,一直扎在南京这个地方,这都是没出息的标志。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就一个家在这儿。天下所有人对自己家的感情是一样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并不是因为南京更好,也不是南京更有文化,是因为我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