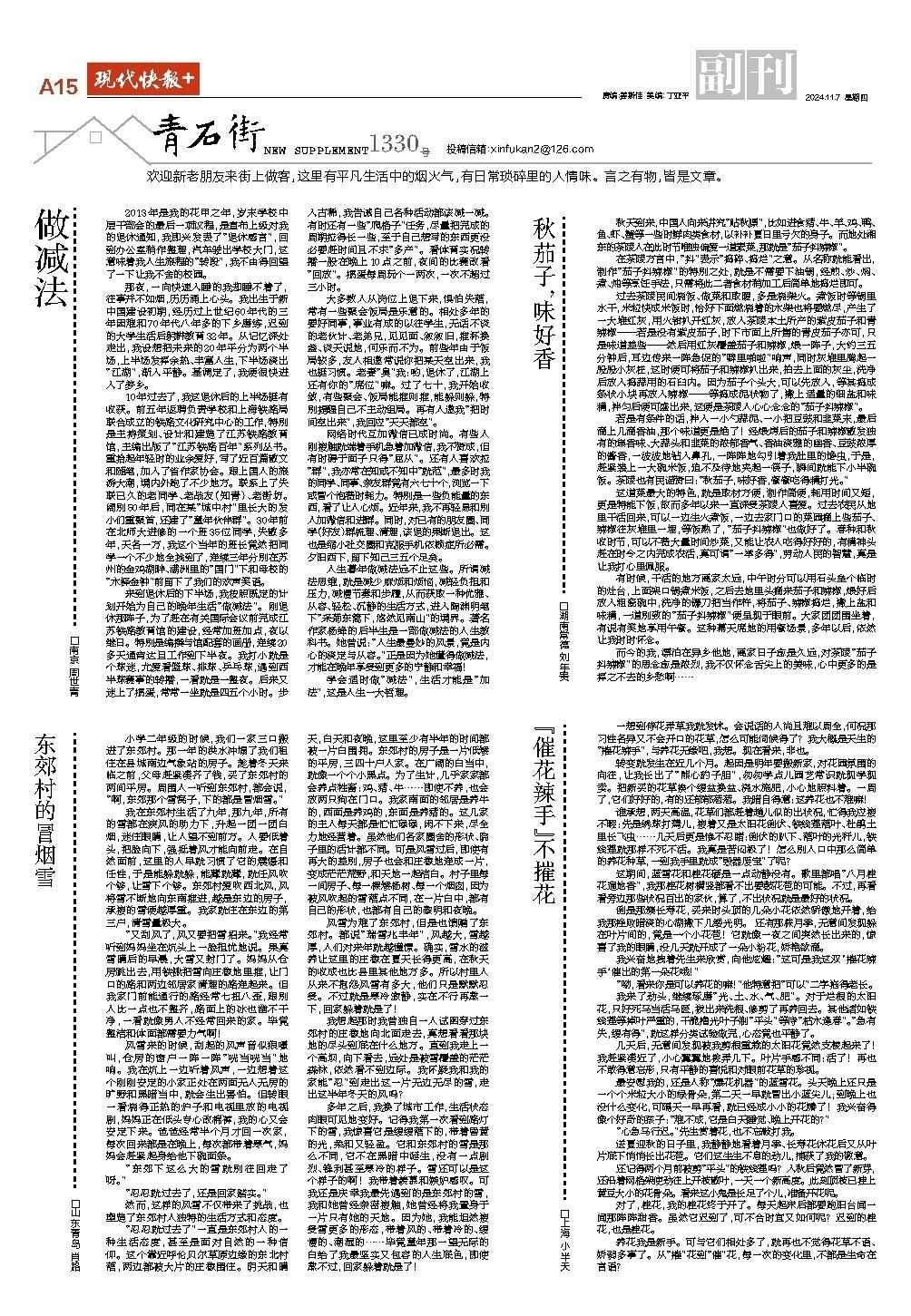□南京 周世青
2013年是我的花甲之年,岁末学校中层干部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宣布上级对我的退休通知,我即兴发表了“退休感言”,回到办公室稍作整理,汽车驶出学校大门,这意味着我人生旅程的“转段”,我不由得回望了一下让我不舍的校园。
那夜,一向快速入睡的我却睡不着了,往事并不如烟,历历涌上心头。我出生于新中国建设初期,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困难和70年代八年多的下乡磨练,迟到的大学生活后躬耕教育32年。从记忆深处走出,我设想把未来的20年平分为两个半场,上半场发挥余热、丰富人生,下半场淡出“江湖”,渐入平静。基调定了,我便很快进入了梦乡。
10年过去了,我这退休后的上半场挺有收获。前五年返聘负责学校和上海铁路局联合成立的铁路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特别是主持策划、设计和建造了江苏铁路教育馆,主编出版了“江苏铁路百年”系列丛书。重拾起年轻时的业余爱好,写了近百篇散文和随笔,加入了省作家协会。跟上国人的旅游大潮,境内外跑了不少地方。联系上了失联已久的老同学、老战友(知青)、老街坊。阔别50年后,同在某“城中村”里长大的发小们重聚首,还建了“童年伙伴群”。30年前在北师大进修的一个班35位同学,失散多年,天各一方,我这个当年的班长竟然把同学一个不少地全找到了,连续三年分别在苏州的金鸡湖畔、满洲里的“国门”下和母校的“木铎金钟”前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来到退休后的下半场,我按照既定的计划开始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减法”。刚退休那阵子,为了赶在有关国际会议前完成江苏铁路教育馆的建设,经常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特别是编撰与馆配套的画册,连续20多天通宵达旦工作到下半夜。我打小就是个球迷,尤爱看篮球、排球、乒乓球,遇到西半球赛事的转播,一看就是一整夜。后来又迷上了掼蛋,常常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步入古稀,我告诫自己各种活动都该减一减。有时还有一些“爬格子”任务,尽量把完成的周期拉得长一些,至于自己想写的东西更没必要赶时间且不求“多产”。看体育实况转播一般在晚上10点之前,夜间的比赛改看“回放”。掼蛋每周玩个一两次,一次不超过三小时。
大多数人从岗位上退下来,惧怕失落,常有一些聚会饭局是乐意的。相处多年的要好同事,事业有成的以往学生,无话不谈的老伙计、老弟兄,见见面、叙叙旧,推杯换盏、谈天说地,何乐而不为。前些年由于饭局较多,友人相邀常说你把某天空出来,我也挺习惯。老妻“臭”我:哟,退休了,江湖上还有你的“席位”嘛。过了七十,我开始收敛,有些聚会、饭局能推则推,能躲则躲,特别提醒自己不主动组局。再有人邀我“把时间空出来”,我回应“天天都空”。
网络时代互加微信已成时尚。有些人刚接触就端着手机急着加微信,我不赞成,但有时碍于面子只得“屈从”。还有人喜欢拉“群”,我亦常在知或不知中“就范”,最多时我的同学、同事、亲友群竟有六七十个,浏览一下或冒个泡费时耗力。特别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看了让人心烦。近年来,我不再轻易和别人加微信和进群。同时,对已有的朋友圈、同学(好友)群梳理、清理,该退的果断退出。这也是缩小社交圈和克服手机依赖症所必需。夕阳西下,留下知己三五个足矣。
人生暮年做减法远不止这些。所谓减法思维,就是减少麻烦和烦恼,减轻负担和压力,减慢节奏和步履,从而获取一种优雅、从容、轻松、沉静的生活方式,进入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著名作家杨绛的后半生是一部做减法的人生教科书。她曾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正是因为她懂得做减法,才能在晚年享受到更多的宁静和幸福!
学会适时做“减法”,生活才能是“加法”,这是人生一大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