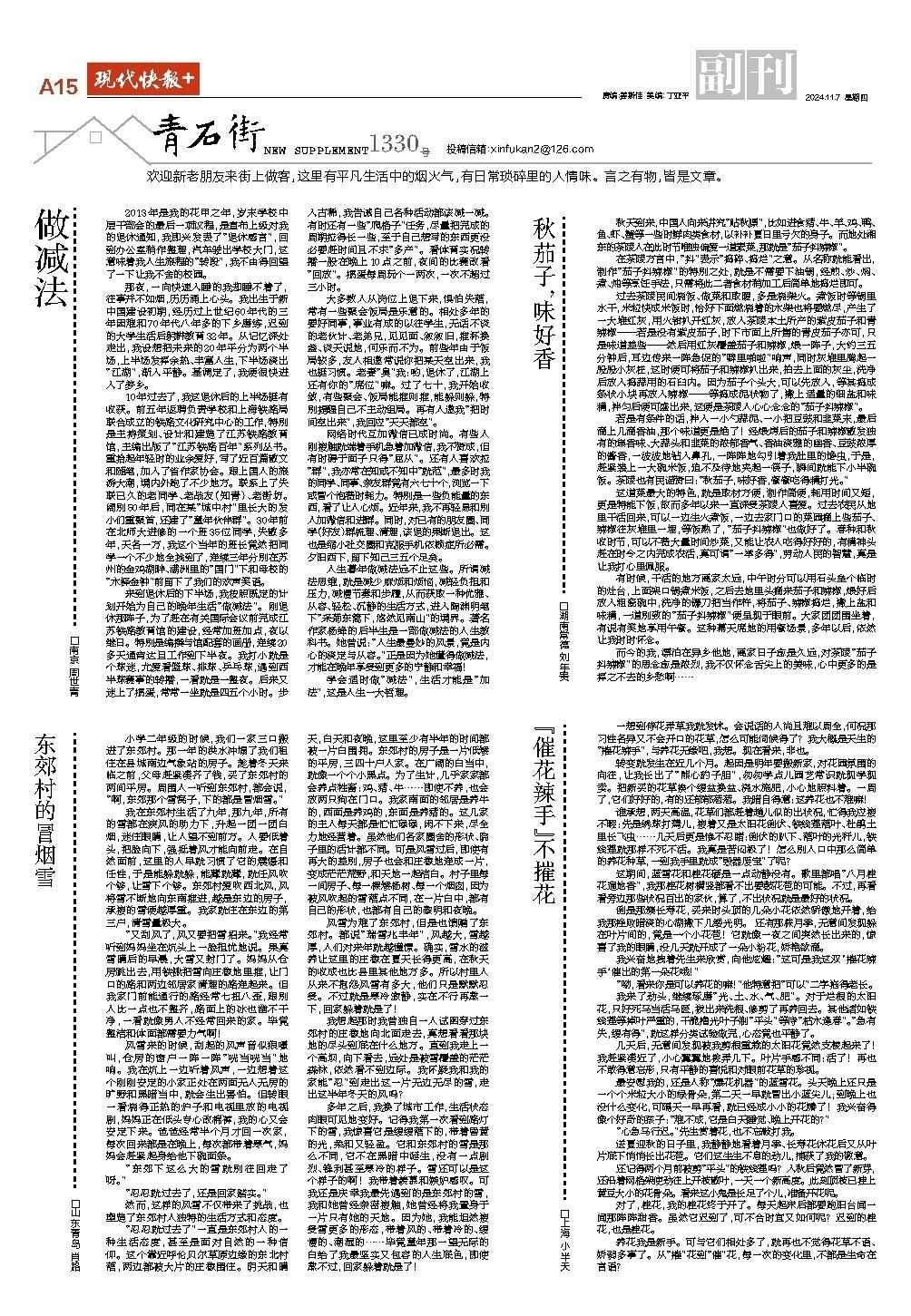□山东青岛 肖路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东郊村。那一年的洪水冲塌了我们租住在县城南边气象站的房子。趁着冬天来临之前,父母赶紧凑齐了钱,买了东郊村的两间平房。周围人一听到东郊村,都会说,“啊,东郊那个雪窝子,下的都是冒烟雪。”
我在东郊村生活了九年,那九年,所有的雪都在疾风的助力下,升起一团一团白烟,迷住眼睛,让人望不到前方。人要低着头,把脸向下,强抵着风才能向前走。在自然面前,这里的人早就习惯了它的震慑和任性,于是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就任风吹个够,让雪下个够。东郊村爱吹西北风,风将雪不断地向东南推进,越是东边的房子,承接的雪便越厚重。我家就住在东边的第三户,清雪量极大。
“又刮风了,风又要把雪招来。”我经常听到妈妈坐在炕头上一脸担忧地说。果真雪晴后的早晨,大雪又封门了。妈妈从仓房跳出去,用铁锹把雪向庄稼地里推,让门口的路和两边邻居家清理的路连起来。但我家门前能通行的路经常七扭八歪,跟别人比一点也不整齐,路面上的冰也凿不干净,一看就像男人不经常回来的家。毕竟整洁和体面都需要力气啊!
风雪来的时候,刮起的风声音似狼嚎叫,仓房的窗户一阵一阵“咣当咣当”地响。我在炕上一边听着风声,一边想着这个刚刚安定的小家正处在两面无人无房的旷野和黑暗当中,就会生出害怕。但转眼一看烧得正热的炉子和电视里放的电视剧,妈妈正在低头专心改棉裤,我的心又会安定下来。爸爸经常半个月才回一次家,每次回来都是在晚上,每次都带着寒气,妈妈会赶紧起身给他下碗面条。
“东郊下这么大的雪就别往回走了呀。”
“忍忍就过去了,还是回家踏实。”
然而,这样的风雪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塑造了东郊村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忍忍就过去了”一直是东郊村人的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面对自然的一种信仰。这个靠近呼伦贝尔草原边缘的东北村落,两边都被大片的庄稼围住。阴天和晴天,白天和夜晚,这里至少有半年的时间都被一片白围拥。东郊村的房子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三四十户人家。在广阔的白当中,就像一个个小黑点。为了生计,几乎家家都会养点牲畜:鸡、猪、牛……即使不养,也会放两只狗在门口。我家南面的邻居是养牛的,西面是养鸡的,东面是养猪的。这几家的主人每天都是忙忙碌碌,闲不下来,尽全力地经营着。虽然他们各家圈舍的形状、院子里的活计都不同。可是风雪过后,即使有再大的差别,房子也会和庄稼地连成一片,变成茫茫荒野,和天地一起洁白。村子里每一间房子、每一棵矮杨树、每一个烟囱,因为被风吹起的雪落点不同,在一片白中,都有自己的形状,也都有自己的黎明和夜晚。
风雪为难了东郊村,但是也馈赠了东郊村。都说“瑞雪兆丰年”,风越大,雪越厚,人们对来年就越憧憬。确实,雪水的滋养让这里的庄稼在夏天长得更高,在秋天的收成也比县里其他地方多。所以村里人从来不抱怨风雪有多大,他们只是默默忍受。不过就是寒冷寂静,实在不行再熬一下,回家躲着就是了!
我想起那时我曾独自一人试图穿过东郊村的庄稼地向北面走去,真想看看那块地的尽头到底在什么地方。直到我走上一个高坝,向下看去,远处是被雪覆盖的茫茫森林,依然看不到边际。我怀疑我和我的家能“忍”到走出这一片无边无尽的雪,走出这半年冬天的风吗?
多年之后,我换了城市工作,生活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好。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路灯下的雪,我惊喜它是缓缓落下的,带着昏黄的光,柔和又轻盈。它和东郊村的雪是那么不同,它不在黑暗中诞生,没有一点剧烈、锋利甚至寒冷的样子。雪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带着羡慕和嫉妒感叹。可我还是庆幸我最先遇到的是东郊村的雪,我和她曾经亲密接触,她曾经将我置身于一片只有她的天地。因为她,我能坦然接受雪更多的形态,带着风的、带着冷的、缓慢的、潮湿的……毕竟童年那一望无际的白给了我最坚实又包容的人生底色,即使熬不过,回家躲着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