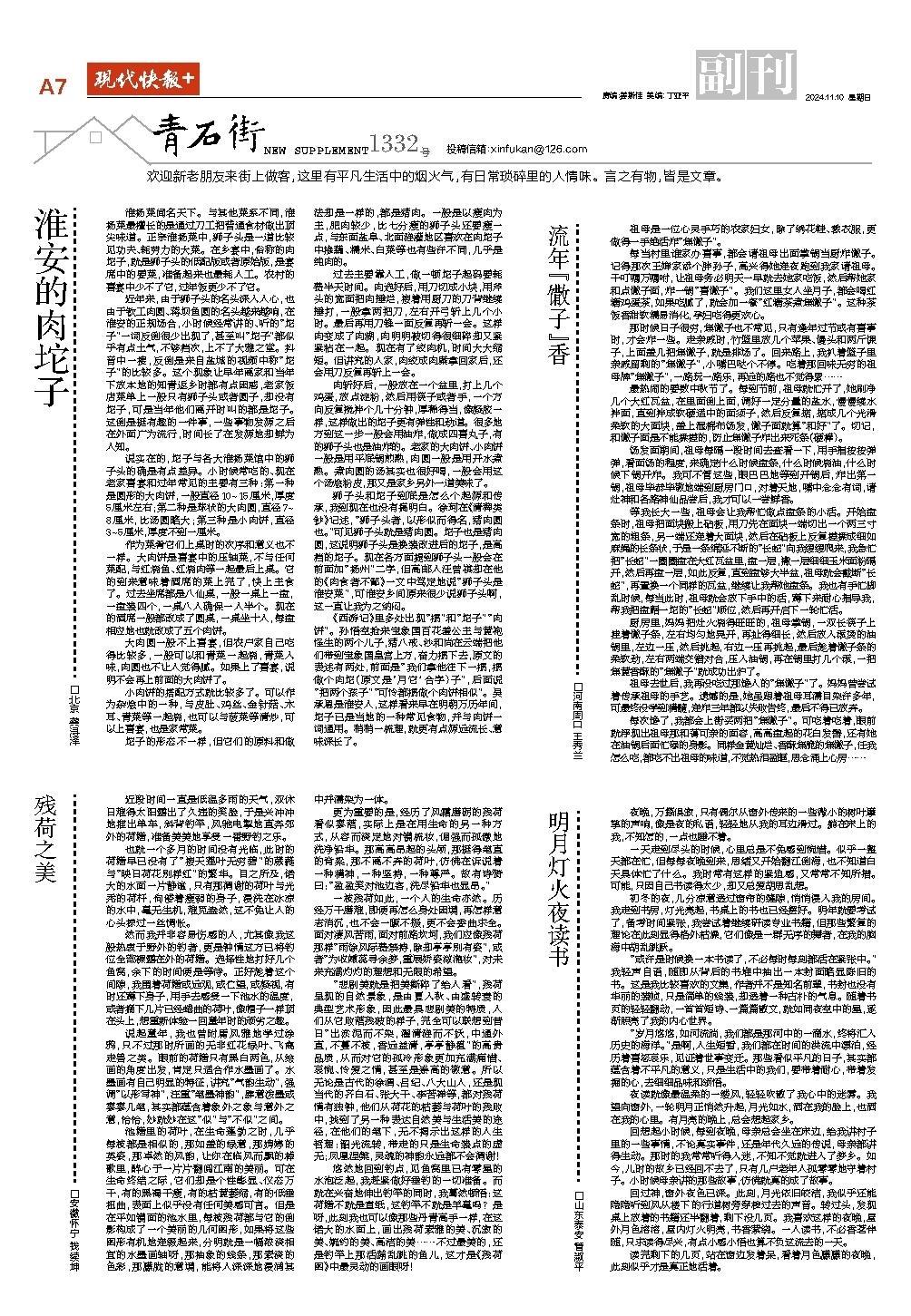□北京 龚浔泽
淮扬菜闻名天下。与其他菜系不同,淮扬菜最擅长的是通过刀工把普通食材做出顶尖味道。正宗淮扬菜中,狮子头是一道比较见功夫、耗劳力的大菜。在乡宴中,俗称的肉坨子,就是狮子头的低配版或者原始版,是宴席中的要菜,准备起来也最耗人工。农村的喜宴中少不了它,过年饭更少不了它。
近年来,由于狮子头的名头深入人心,也由于钦工肉圆、蒋坝鱼圆的名头越来越响,在淮安的正规场合,小时候经常讲的、听的“坨子”一词反倒很少出现了,甚至叫“坨子”都似乎有点土气,不够档次,上不了大雅之堂。抖音中一搜,反倒是来自盐城的视频中称“坨子”的比较多。这个现象让早年离家和当年下放本地的知青返乡时都有点困惑,老家饭店菜单上一般只有狮子头或者圆子,却没有坨子,可是当年他们离开时叫的都是坨子。这倒是挺有趣的一件事,一些事物发源之后在外面广为流行,时间长了在发源地却鲜为人知。
说实在的,坨子与各大淮扬菜馆中的狮子头的确是有点差异。小时候常吃的、现在老家喜宴和过年常见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圆形的大肉饼,一般直径10~15厘米,厚度5厘米左右;第二种是球状的大肉圆,直径7~8厘米,比汤圆略大;第三种是小肉饼,直径3~5厘米,厚度不到一厘米。
作为菜肴它们上桌时的次序和意义也不一样。大肉饼是喜宴中的压轴菜,不与任何菜配,与红烧鱼、红烧肉等一起最后上桌。它的到来意味着酒席的菜上完了,快上主食了。过去坐席都是八仙桌,一般一桌上一盘,一盘装四个,一桌八人确保一人半个。现在的酒席一般都改成了圆桌,一桌坐十人,每盘相应地也就改成了五个肉饼。
大肉圆一般不上喜宴,但农户家自己吃得比较多,一般可以和青菜一起烧,青菜入味,肉圆也不让人觉得腻。如果上了喜宴,说明不会再上前面的大肉饼了。
小肉饼的搭配方式就比较多了。可以作为杂烩中的一种,与皮肚、鸡丝、金针菇、木耳、青菜等一起烧,也可以与菠菜等清炒,可以上喜宴,也是家常菜。
坨子的形态不一样,但它们的原料和做法却是一样的,都是猪肉。一般是以瘦肉为主,肥肉较少,比七分瘦的狮子头还要瘦一点,与东面盐阜、北面涟灌地区喜欢在肉坨子中掺藕、糯米、白菜等也有些许不同,几乎是纯肉的。
过去主要靠人工,做一顿坨子起码要耗费半天时间。肉选好后,用刀切成小块,用斧头的宽面把肉捶烂,接着用厨刀的刀背继续捶打,一般拿两把刀,左右开弓斩上几个小时。最后再用刀锋一面反复再斩一会。这样肉变成了肉糊,肉明明被切得很细碎却又紧紧粘在一起。现在有了绞肉机,时间大大缩短。但讲究的人家,肉绞成肉糜拿回家后,还会用刀反复再斩上一会。
肉斩好后,一般放在一个盆里,打上几个鸡蛋,放点淀粉,然后用筷子或者手,一个方向反复搅拌个几十分钟,厚稀得当,像凝胶一样,这样做出的坨子更有弹性和劲道。很多地方到这一步一般会用油炸,做成四喜丸子,有的狮子头也是油炸的。老家的大肉饼、小肉饼一般是用平底锅煎熟,肉圆一般是用开水煮熟。煮肉圆的汤其实也很好喝,一般会用这个汤烩粉皮,那又是家乡另外一道美味了。
狮子头和坨子到底是怎么个起源和传承,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徐珂在《清稗类钞》记述,“狮子头者,以形似而得名,猪肉圆也。”可见狮子头就是猪肉圆。坨子也是猪肉圆,这说明狮子头是换装改进后的坨子,是高档的坨子。现在各方面提到狮子头一般会在前面加“扬州”二字,但高邮人汪曾祺却在他的《肉食者不鄙》一文中笃定地说“狮子头是淮安菜”,可淮安乡间原来很少说狮子头啊,这一直让我为之纳闷。
《西游记》里多处出现“掼”和“坨子”“肉饼”。孙悟空抢来宝象国百花羞公主与黄袍怪生的两个儿子,猪八戒、沙和尚在云端把他们带到宝象国皇宫上方,奋力掼下去,原文的表述有两处,前面是“我们拿他往下一掼,掼做个肉坨(原文是‘月它’合字)子”,后面说“把两个孩子”“可怜都掼做个肉饼相似”。吴承恩是淮安人,这样看来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坨子已是当地的一种常见食物,并与肉饼一词通用。稍稍一梳理,就更有点源远流长、意味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