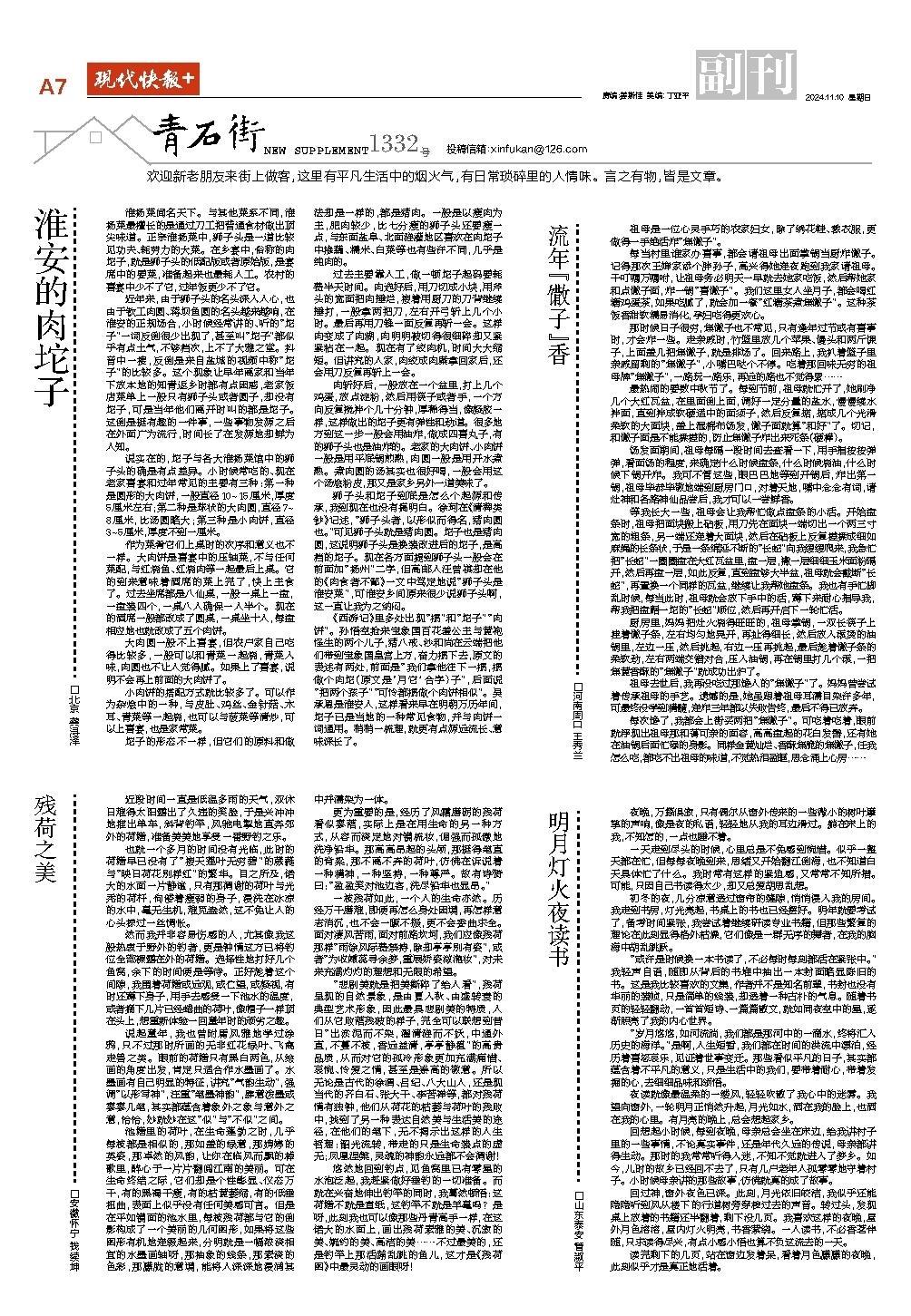□河南周口 王秀兰
祖母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农家妇女,除了绣花鞋、裁衣服,更做得一手绝活炸“焦馓子”。
每当村里谁家办喜事,都会请祖母出面掌锅当厨炸馓子。记得那次王婶家添个胖孙子,高兴得她连夜跑到我家请祖母。千叮嘱万嘱咐,让祖母务必明天一早就去她家吃饭,然后帮她家和点馓子面,炸一锅“喜馓子”。我们这里女人坐月子,都会喝红糖鸡蛋茶,如果吃腻了,就会加一餐“红糖茶煮焦馓子”。这种茶饭香甜软糯易消化,孕妇吃得更欢心。
那时候日子很穷,焦馓子也不常见,只有逢年过节或有喜事时,才会炸一些。走亲戚时,竹篮里放几个苹果、馒头和两斤馃子,上面盖几把焦馓子,就是排场了。回来路上,我扒着篮子里亲戚留剩的“焦馓子”,小嘴巴哒个不停。吃着那回味无穷的祖母牌“焦馓子”,一路玩一路乐,再远的路也不觉得累……
最热闹的要数中秋节了。每到节前,祖母就忙开了,她刷净几个大红瓦盆,在里面倒上面,调好一定分量的盐水,慢慢续水拌面,直到拌成软硬适中的面须子,然后反复掂,掂成几个光滑柔软的大面块,盖上湿棉布饧发,馓子面就算“和好”了。切记,和馓子面是不能揉搓的,防止焦馓子炸出来死条(硬棒)。
饧发面期间,祖母每隔一段时间去查看一下,用手指按按弹弹,看面饧的程度,来确定什么时候盘条,什么时候烧油,什么时候下锅开炸。我可不管这些,眼巴巴地等到开锅后,炸出第一锅,祖母毕恭毕敬地端到厨房门口,对着天地,嘴中念念有词,请灶神和各路神仙品尝后,我才可以一尝鲜香。
等我长大一些,祖母会让我帮忙做点盘条的小活。开始盘条时,祖母把面块搬上砧板,用刀先在面块一端切出一个两三寸宽的粗条,另一端还连着大面块,然后在砧板上反复搓揉成细如麻绳的长条状,于是一条绵延不断的“长蛇”向我缓缓爬来,我急忙把“长蛇”一圈圈盘在大红瓦盆里,盘一层,撒一层细细玉米面粉隔开,然后再盘一层,如此反复,直到盘够大半盆,祖母就会截断“长蛇”,再置换一个同样的瓦盆,继续让我帮她盘条。我也有手忙脚乱时候,每当此时,祖母就会放下手中的活,蹲下来耐心指导我,帮我把盘踞一坨的“长蛇”顺位,然后再开启下一轮忙活。
厨房里,妈妈把灶火烧得旺旺的,祖母掌锅,一双长筷子上挂着馓子条,左右均匀地晃开,再扯得细长,然后放入滚烫的油锅里,左边一压,然后挑起,右边一压再挑起,最后趁着馓子条的柔软劲,左右两端交错对合,压入油锅,再在锅里打几个滚,一把焦黄香酥的“焦馓子”就成功出炉了。
祖母去世后,我再没吃过那馋人的“焦馓子”了。妈妈曾尝试着传承祖母的手艺。遗憾的是,她虽跟着祖母耳濡目染许多年,可最终没学到精髓,连炸三年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已放弃。
每次馋了,我都会上街买两把“焦馓子”。可吃着吃着,眼前就浮现出祖母那和蔼可亲的面容,高高盘起的花白发髻,还有她在油锅后面忙碌的身影。同样金黄灿烂、香酥焦脆的焦馓子,任我怎么吃,都吃不出祖母的味道,不觉热泪盈眶,思念涌上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