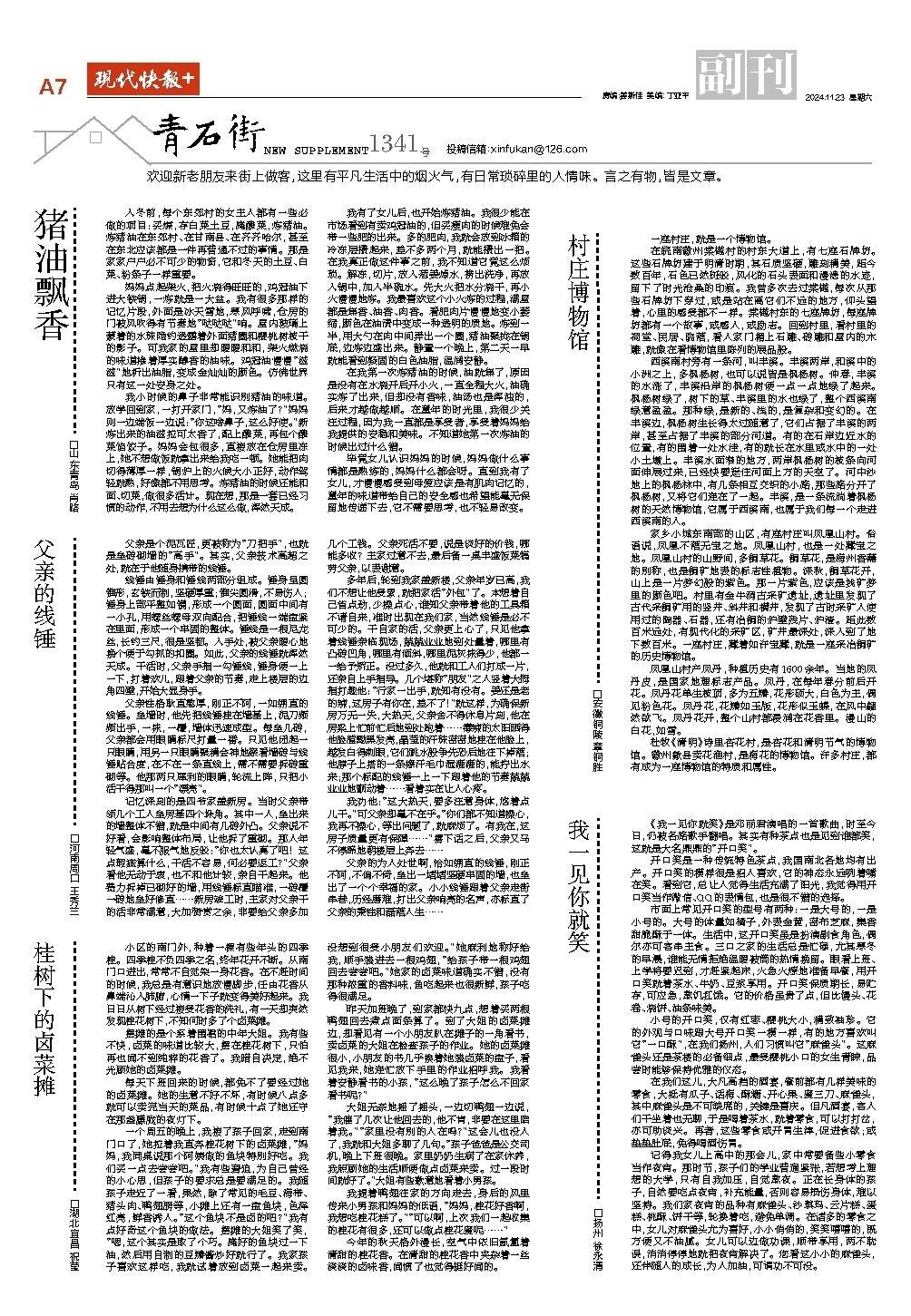□山东青岛 肖路
入冬前,每个东郊村的女主人都有一些必做的项目:买煤,存白菜土豆,腌酸菜,炼猪油。炼猪油在东郊村、在甘南县、在齐齐哈尔,甚至在东北应该都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那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物资,它和冬天的土豆、白菜、粉条子一样重要。
妈妈点起柴火,把火烧得旺旺的,鸡冠油下进大铁锅,一炼就是一大盆。我有很多那样的记忆片段,外面是冰天雪地,寒风呼啸,仓房的门被风吹得有节奏地“哒哒哒”响。屋内玻璃上蒙着的水珠隐约透露着外面猪圈和樱桃树枝干的影子。可我家的屋里却暖暖和和,柴火燃烧的味道掺着厚实醇香的油味。鸡冠油慢慢“滋滋”地析出油脂,变成金灿灿的颜色。仿佛世界只有这一处安身之处。
我小时候的鼻子非常能识别猪油的味道。放学回到家,一打开家门,“妈,又炼油了?”妈妈则一边端饭一边说:“你这啥鼻子,这么好使。”新炼出来的油滋拉可太香了,配上酸菜,再包个酸菜馅饺子。妈妈会包很多,直接放在仓房里冻上,她不想做饭就拿出来给我吃一顿。她能把肉切得薄厚一样,锅炉上的火候大小正好,动作驾轻就熟,好像都不用思考。炼猪油的时候还能和面、切菜,做很多活计。现在想,那是一套已经习惯的动作,不用去想为什么这么做,浑然天成。
我有了女儿后,也开始炼猪油。我很少能在市场看到有卖鸡冠油的,但买瘦肉的时候难免会带一些肥的出来。多的肥肉,我就会放到冰箱的冷冻层攒起来,差不多两个月,就能攒出一把。在我真正做这件事之前,我不知道它竟这么烦琐。解冻,切片,放入葱姜焯水,捞出洗净,再放入锅中,加入半碗水。先大火把水分烧干,再小火慢慢地炼。我最喜欢这个小火炼的过程,满屋都是焦香、油香、肉香。看肥肉片慢慢地变小萎缩,颜色在油渍中变成一种透明的质地。炼到一半,用大勺在肉中间弄出一个圈,猪油聚拢在锅底,边炼边盛出来。静置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能看到凝固的白色油脂,温润安静。
在我第一次炼猪油的时候,油就焦了,原因是没有在水烧开后开小火,一直全程大火,油确实炼了出来,但却没有香味,油汤也是浑浊的,后来才越做越顺。在童年的时光里,我很少关注过程,因为我一直都是享受者,享受着妈妈给我提供的安稳和美味。不知道她第一次炼油的时候出过什么错。
毕竟女儿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做什么事情都是熟练的,妈妈什么都会呀。直到我有了女儿,才慢慢感受到母爱应该是有肌肉记忆的,童年的味道带给自己的安全感也希望能毫无保留地传递下去,它不需要思考,也不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