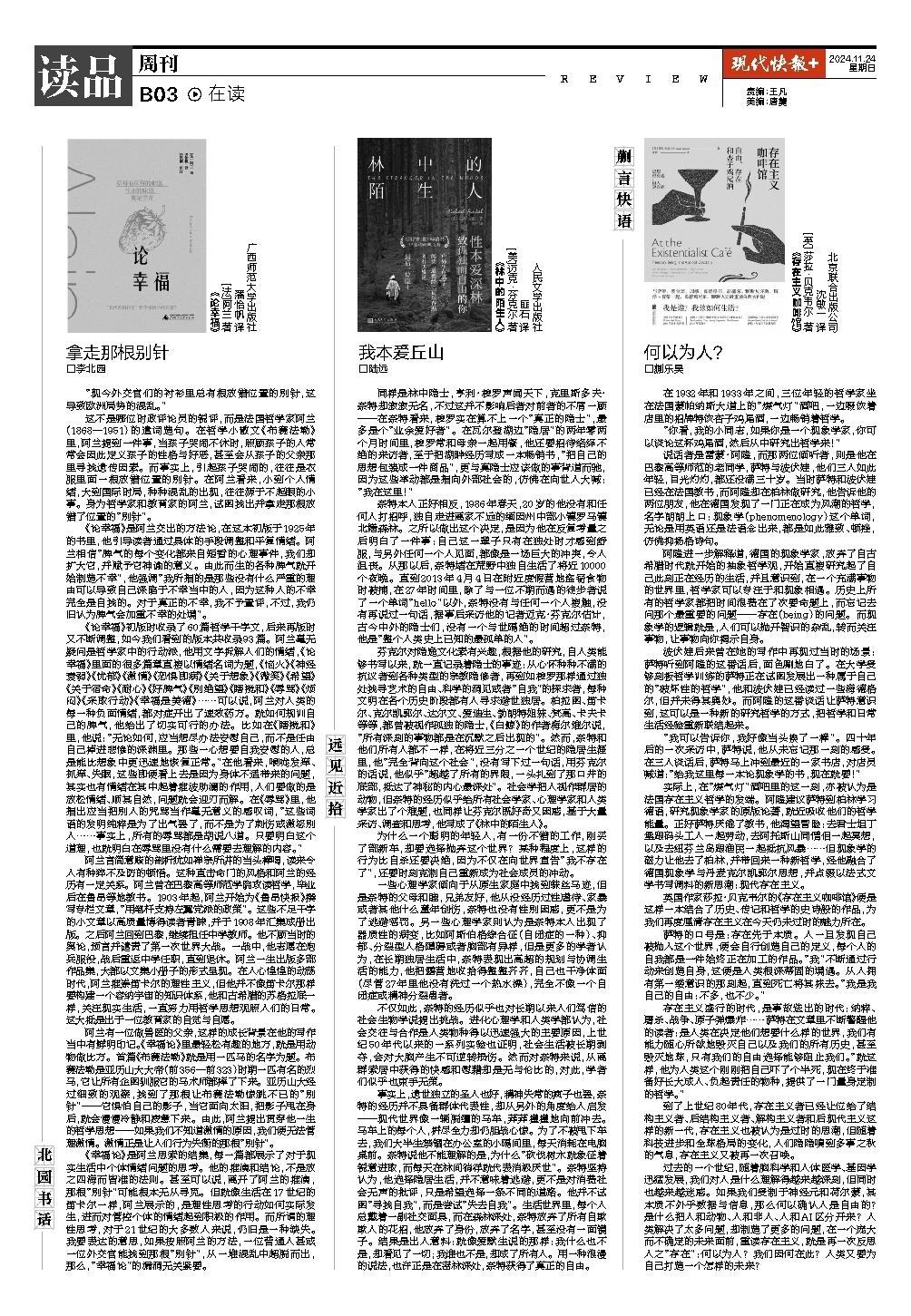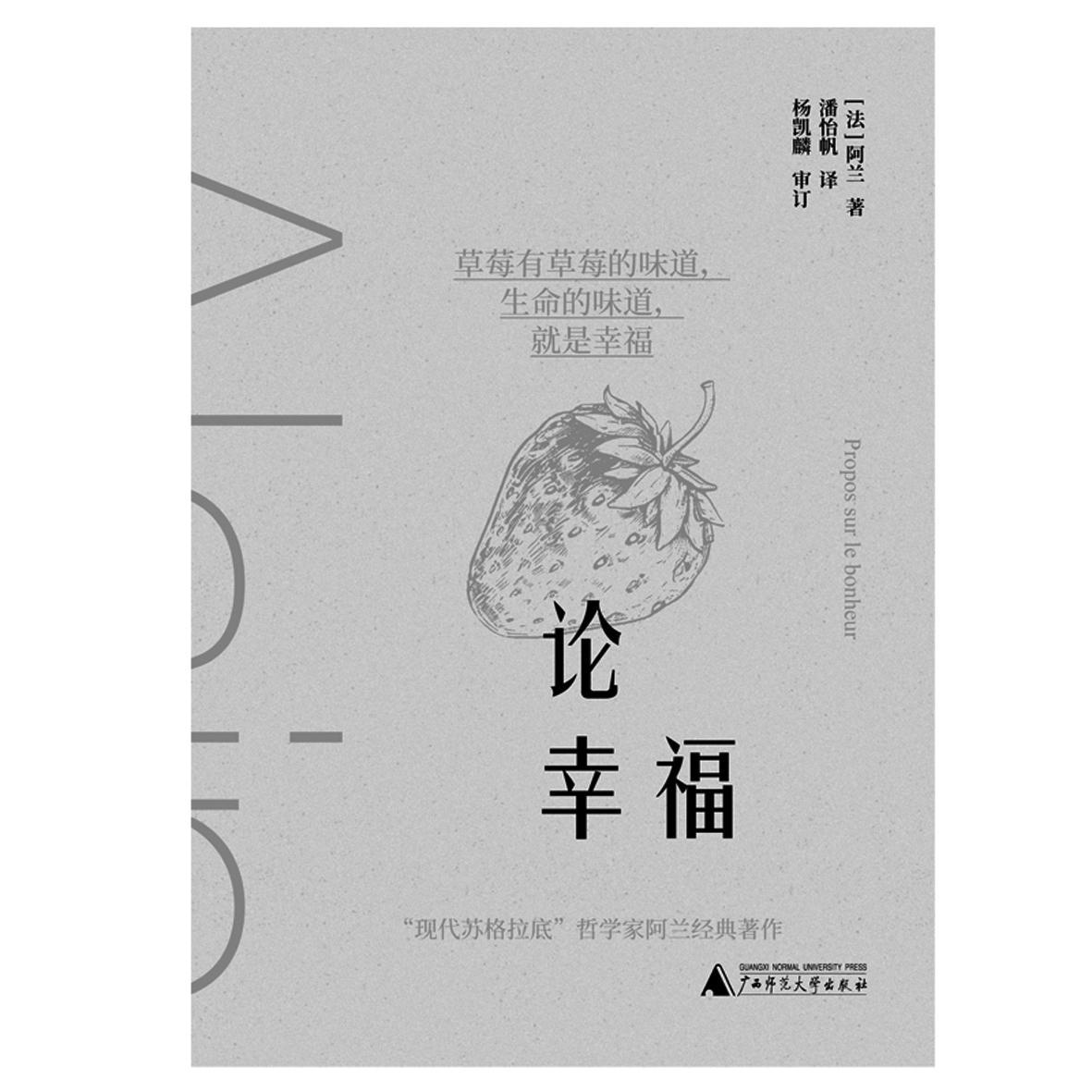□李北园
“现今外交官们的衬衫里总有根放错位置的别针,这导致欧洲局势的混乱。”
这不是哪位时政评论员的锐评,而是法国哲学家阿兰(1868—1951)的遣词造句。在哲学小散文《布赛法勒》里,阿兰提到一件事,当孩子哭闹不休时,照顾孩子的人常常会因此定义孩子的性格与好恶,甚至会从孩子的父亲那里寻找遗传因素。而事实上,引起孩子哭闹的,往往是衣服里面一根放错位置的别针。在阿兰看来,小到个人情绪,大到国际时局,种种混乱的出现,往往源于不起眼的小事。身为哲学家和教育家的阿兰,试图找出并拿走那根放错了位置的“别针”。
《论幸福》是阿兰交出的方法论,在这本初版于1925年的书里,他引导读者通过具体的手段调整和平复情绪。阿兰相信“脾气的每个变化都来自短暂的心理事件,我们却扩大它,并赋予它神谕的意义。由此而生的各种脾气就开始制造不幸”,他强调“我所指的是那些没有什么严重的理由可以导致自己深陷于不幸当中的人,因为这种人的不幸完全是自找的。对于真正的不幸,我不予置评,不过,我仍旧认为脾气会加重不幸的处境”。
《论幸福》初版时收录了60篇哲学千字文,后来再版时又不断调整,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共收录93篇。阿兰毫无疑问是哲学家中的行动派,他用文字拆解人们的情绪,《论幸福》里面的很多篇章直接以情绪名词为题,《恼火》《神经衰弱》《忧郁》《激情》《恐惧即病》《关于想象》《微笑》《希望》《关于宿命》《耐心》《好脾气》《别绝望》《瞎搅和》《辱骂》《烦闷》《采取行动》《幸福是美德》……可以说,阿兰对人类的每一种负面情绪,都对症开出了速效药方。就如何规训自己的脾气,他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在《瞎搅和》里,他说:“无论如何,应当想尽办法安慰自己,而不是任由自己掉进悲惨的深渊里。那些一心想要自我安慰的人,总是能比想象中更迅速地恢复正常。”在他看来,喉咙发痒、抓痒、失眠,这些即便看上去是因为身体不适带来的问题,其实也有情绪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要做的是放松情绪、顺其自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辱骂》里,他指出应当把别人的咒骂当作毫无意义的感叹词,“这些词语的发明纯粹是为了出气罢了,而不是为了刺伤或激怒别人……事实上,所有的辱骂都是胡说八道。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明白在辱骂里没有什么需要去理解的内容。”
阿兰言简意赅的剖析犹如禅宗所讲的当头棒喝,读来令人有种猝不及防的顿悟。这种直击命门的风格和阿兰的经历有一定关系。阿兰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毕业后在鲁昂等地教书。1903年起,阿兰开始为《鲁昂快报》撰写专栏文章,“用笔杆支持左翼党派的政策”。这些不足千字的小文章以高质量博得读者青睐,并于1908年汇集成册出版。之后阿兰回到巴黎,继续担任中学教师。他不顾当时的舆论,预言并谴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中,他志愿在炮兵服役,战后重返中学任职,直到退休。阿兰一生出版多部作品集,大都以文集小册子的形式呈现。在人心惶惶的动荡时代,阿兰推崇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但他并不像笛卡尔那样要构建一个容纳宇宙的知识体系,他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关注现实生活,一直努力用哲学思想观照人们的日常。这大抵是出于一位教育家的自觉与自愿。
阿兰有一位做兽医的父亲,这样的成长背景在他的写作当中有鲜明印记。《幸福论》里最轻松有趣的地方,就是用动物做比方。首篇《布赛法勒》就是用一匹马的名字为题。布赛法勒是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时期一匹有名的烈马,它让所有企图驯服它的马术师都摔了下来。亚历山大经过细致的观察,找到了那根让布赛法勒惊跳不已的“别针”——它惧怕自己的影子,当它面向太阳,把影子甩在身后,就会慢慢冷静和疲惫下来。由此,阿兰提出贯穿他一生的哲学思想——如果我们不知道激情的原因,我们便无法管理激情。激情正是让人们行为失衡的那根“别针”。
《幸福论》是阿兰思索的结集,每一篇都展示了对于现实生活中个体情绪问题的思考。他的推演和结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甚至可以说,离开了阿兰的推演,那根“别针”可能根本无从寻觅。但就像生活在17世纪的笛卡尔一样,阿兰展示的,是理性思考的行动如何实际发生,进而对管控个体的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所谓的理性思考,对于21世纪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种缺失。我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按照阿兰的方法,一位普通人甚或一位外交官能找到那根“别针”,从一堆混乱中超脱而出,那么,“幸福论”的漏洞无关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