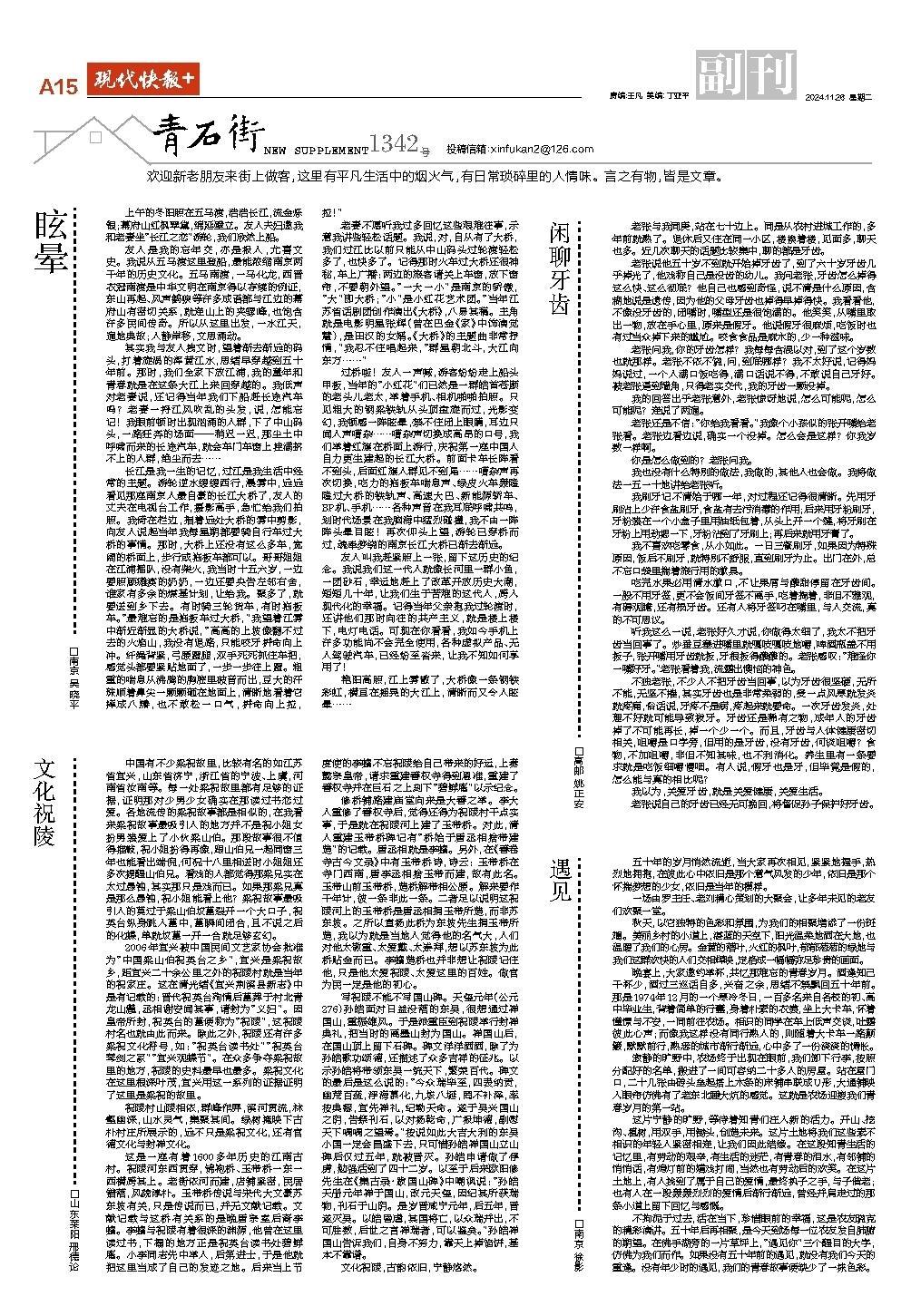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上午的冬阳照在五马渡,浩浩长江,流金烁银;幕府山红枫翠黛,绵延壁立。友人夫妇邀我和老妻坐“长江之恋”游轮,我们欣然上船。
友人是我的忘年交,亦是报人,尤喜文史。我说从五马渡这里登船,最能浓缩南京两千年的历史文化。五马南渡,一马化龙,西晋衣冠南渡是中华文明在南京得以存续的例证,东山再起、风声鹤唳等许多成语都与江边的幕府山有密切关系,就连山上的夹骡峰,也饱含许多民间传奇。所以从这里出发,一水江天,遍地典故;人静岸移,文思涌动。
其实我与友人拽文时,望着渐去渐远的码头,打着旋涡的浑黄江水,思绪早穿越到五十年前。那时,我们全家下放江浦,我的童年和青春就是在这条大江上来回穿越的。我低声对老妻说,还记得当年我们下船赶长途汽车吗?老妻一捋江风吹乱的头发,说,怎能忘记!我眼前顿时出现汹涌的人群,下了中山码头,一路狂奔的场面——稍迟一迟,那尘土中呼啸而来的长途汽车,就会车门车窗上挂满挤不上的人群,绝尘而去……
长江是我一生的记忆,过江是我生活中经常的主题。游轮逆水缓缓西行,晨雾中,远远看见那座南京人最自豪的长江大桥了,友人的丈夫在电视台工作,摄影高手,急忙给我们拍照。我倚在栏边,指着远处大桥的雾中剪影,向友人说起当年我每星期都要骑自行车过大桥的事情。那时,大桥上还没有这么多车,宽阔的桥面上,步行或拖板车都可以。哥哥姐姐在江浦插队,没有柴火,我当时十五六岁,一边要照顾瘫痪的奶奶,一边还要央告左邻右舍,谁家有多余的煤基计划,让给我。聚多了,就要送到乡下去。有时骑三轮货车,有时拖板车。“最难忘的是拖板车过大桥,”我望着江雾中渐近渐显的大桥说,“高高的上坡像翻不过去的火焰山,我没有退路,只能咬牙拼命向上冲。纤绳背紧,弓腰蹬腿,双手死死抓住车把,感觉头都要紧贴地面了,一步一步往上蹬。粗重的喘息从沸腾的胸腔里破音而出,豆大的汗珠顺着鼻尖一颗颗砸在地面上,清晰地看着它摔成八瓣,也不敢松一口气,拼命向上拉,拉!”
老妻不愿听我过多回忆这些艰难往事,示意我讲些轻松话题。我说,对,自从有了大桥,我们过江比以前只能从中山码头过轮渡轻松多了,也快多了。记得那时火车过大桥还很神秘,车上广播:两边的旅客请关上车窗,放下窗帘,不要朝外望。“一大一小”是南京的骄傲,“大”即大桥;“小”是小红花艺术团。“当年江苏省话剧团创作演出《大桥》,八易其稿。主角就是电影明星张辉(曾在巴金《家》中饰演觉慧),是田汉的女婿。《大桥》的主题曲非常抒情,”我忍不住唱起来,“群星朝北斗,大江向东方……”
过桥啦!友人一声喊,游客纷纷走上船头甲板,当年的“小红花”们已然是一群皓首苍颜的老头儿老太,举着手机、相机啪啪拍照。只见粗大的钢梁铁轨从头顶盘旋而过,光影变幻,我顿感一阵眩晕,禁不住闭上眼睛,耳边只闻人声嘈杂……嘈杂声切换成高昂的口号,我们举着红旗在桥面上游行,庆祝第一座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起的长江大桥。前面卡车长阵看不到头,后面红旗人群见不到尾……嘈杂声再次切换,吃力的拖板车喘息声、绿皮火车轰隆隆过大桥的铁轨声、高速大巴、新能源轿车、BP机、手机……各种声音在我耳底呼啸共鸣,划时代场景在我脑海中猛烈碰撞,我不由一阵阵头晕目眩!再次仰头上望,游轮已穿桥而过,魂牵梦绕的南京长江大桥已渐去渐远。
友人叫我赶紧照上一张,留下这历史的纪念。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就像长河里一群小鱼,一团砂石,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历史大潮,短短几十年,让我们生于苦难的这代人,跨入现代化的幸福。记得当年父亲抱我过轮渡时,还讲他们那时向往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现在你看看,我如今手机上许多功能尚不会完全使用,各种虚拟产品、无人驾驶汽车,已经纷至沓来,让我不知如何享用了!
艳阳高照,江上雾散了,大桥像一条钢铁彩虹,横亘在摇晃的大江上,清晰而又令人眩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