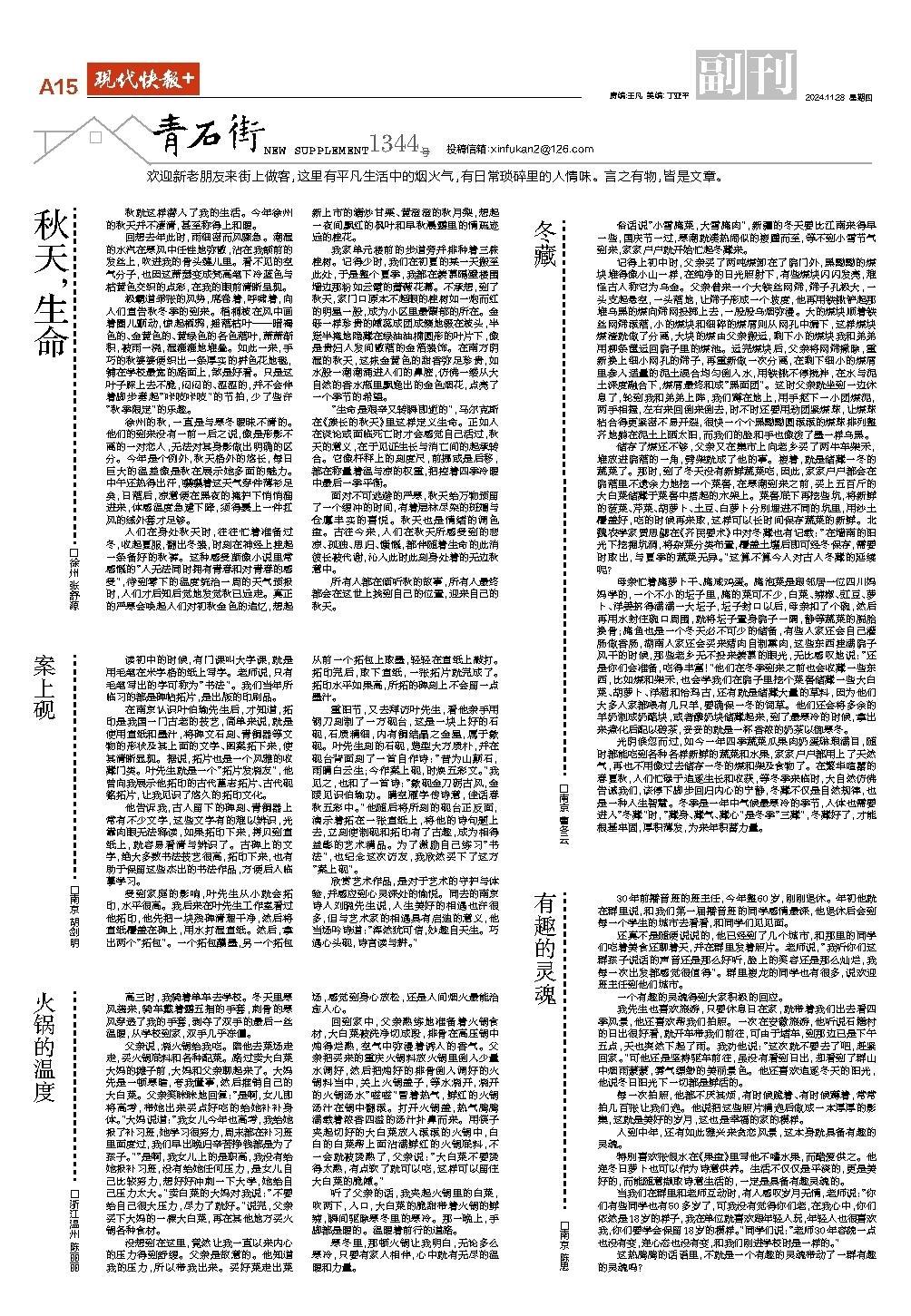□徐州 张舒源
秋就这样潜入了我的生活。今年徐州的秋天并不凄清,甚至称得上和暖。
回想去年此时,雨细密而风骤急。潮湿的水汽在寒风中任性地弥散,沾在我额前的发丝上,吹进我的骨头缝儿里。看不见的空气分子,也因这萧瑟变成梵高笔下冷蓝色与枯黄色交织的点彩,在我的眼前清晰呈现。
极霸道乖张的风势,席卷着,呼啸着,向人们宣告秋冬季的到来。梧桐枝在风中画着圈儿颤动,惊起栖鸦,摇落枯叶——暗褐色的、金黄色的、黄绿色的各色落叶,萧萧渐积,被雨一浇,湿漉漉地堆叠。如此一来,手巧的秋婆婆便织出一条厚实的拼色花地毯,铺在学校最宽的路面上,煞是好看。只是这叶子踩上去不脆,闷闷的、涩涩的,并不会伴着脚步奏起“咔吱咔吱”的节拍,少了些许“秋季限定”的乐趣。
徐州的秋,一直是与寒冬暧昧不清的。他们的到来没有一前一后之说,像是形影不离的一对恋人,无法对其身影做出明确的区分。今年是个例外,秋天格外的悠长,每日巨大的温差像是秋在展示她多面的魅力。中午还热得出汗,嚷嚷着这天气穿件薄衫足矣,日落后,凉意便在黑夜的掩护下悄悄溜进来,体感温度急遽下降,须得裹上一件扛风的绒外套才足够。
人们在身处秋天时,往往忙着准备过冬,收起夏服,翻出冬装,时刻在神经上挂起一条备好的秋裤。这种感受颇像小说里常感慨的“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待到零下的温度统治一周的天气预报时,人们才后知后觉地发觉秋已远走。真正的严寒会唤起人们对初秋金色的追忆,想起新上市的糖炒甘栗、黄澄澄的秋月梨,想起一夜间飘红的枫叶和早秋晨露里的情疏迹远的桂花。
我家单元楼前的步道旁并排种着三株桂树。记得少时,我们在初夏的某一天搬至此处,于是整个夏季,我都在羡慕隔壁楼围墙边那粉如云霞的蔷薇花幕。不承想,到了秋天,家门口原本不起眼的桂树如一炮而红的明星一般,成为小区里最馥郁的所在。金砾一样珍贵的嫩蕊成团成簇地缀在枝头,半遮半掩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片下,像是贵妇人发间散落的金箔装饰。在南方阴湿的秋天,这抹金黄色的甜香弥足珍贵,如水般一潮潮涌进人们的鼻腔,仿佛一缕从大自然的香水瓶里飘逸出的金色烟花,点亮了一个季节的希望。
“生命是艰辛又转瞬即逝的”,马尔克斯在《族长的秋天》里这样定义生命。正如人在谈论或面临死亡时才会感觉自己活过,秋天的意义,在于见证生长与消亡间的起承转合。它像杆秤上的刻度尺,前挪或是后移,都在称量着温与凉的权重,把控着四季冷暖中最后一季平衡。
面对不可逃避的严寒,秋天给万物预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与仓廪丰实的喜悦。秋天也是情绪的调色盘。古往今来,人们在秋天所感受到的悲凉、孤独、思归、慷慨,都伴随着生命的此消彼长被代谢,沁入此时此刻身处着的无边秋意中。
所有人都在倾听秋的故事,所有人最终都会在这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迎来自己的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