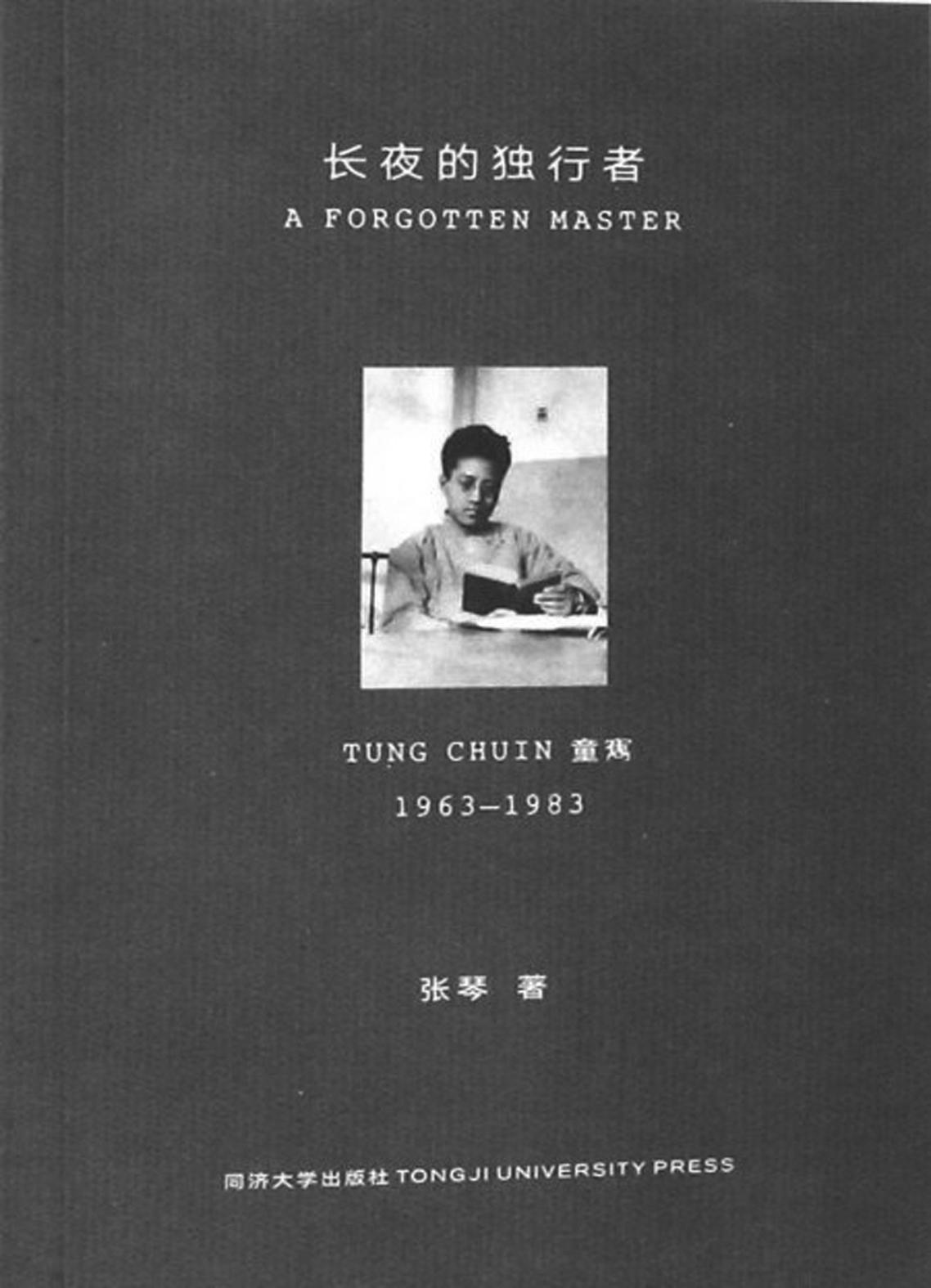□陆远
生命中最后的30多年,童寯教授一直住在南京文昌巷52号,白墙内是一幢英式两层小楼,庭院花木扶疏。我曾很多次在小院门前驻足,遥想小院主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中的升沉宠辱,也曾折服于他论述江南园林的那些经典著作,但这些似乎都不足以拼出一副童先生相对完整的人生图像,直到读了学者张琴的著作《长夜的独行者》。
张琴是建筑学者,也是童寯的孙媳妇,不过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家族长辈,已在他去世多年之后。那一晚,穿过走廊走进客厅,张琴看到老人在墙上的镜框里瞪着自己。从那以后,张琴花了将近30年去了解童寯,与他的亲友、学生聊天,读他留下的那些文字——书信、日记以至交代材料,她的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童寯心灵深处的窗。
童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未必能简单作答。他以研究建筑、设计建筑为毕生志业,却始终是个“非典型”建筑师,中国传统文人那一套情趣、价值和追求,在他的精神世界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在清华读书时,名师云集,童寯私心最仰慕的精神导师是王国维。王先生亲手开列的那张书单,被他随身珍藏多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童寯日后课徒的第一要义。80年代初,童寯成为中国建筑学科首批四名博导之一(另外三位是杨廷宝、冯纪忠和吴良镛),研究中国建筑史已小有名气的日本学者田中淡慕名投考,童寯的考题是:把《古文观止》中柳宗元的《梓人传》先译成汉语白话,再译成英文,田中淡铩羽而归,而熟读《古文观止》则成为童寯门下弟子的必修课。童寯自己能诗善画,常常沉浸于元代绘画与晚明文学中。1977年,阔别数十年的清华同室林同济教授来访,童寯拾起多年荒废的画笔,以一幅山水立轴相赠,笔下分明有倪云林的气韵。学生吴良镛来看他,他把自己的旧画一张一张翻出来共同欣赏,“建筑就那么一点事,画画才是大事”,他亲口对吴良镛说。
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又在童寯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记。他从中学开始研习西洋美术,在清华技艺不断精进,留美期间又受到严格的专业训练。他青年时代旅欧期间留下的水彩画中,“一点看不到中国的东西,完全是西方文化激情横溢的产物”。后来担任过中国书协主席的美术家邵宇偶然中看到童寯的作品,惊讶“真不知道中国还有人水彩画画得这样好”。1978年夏天,童寯在后院葡萄架下用打字机写了一封英文长信给长子童诗白郑敏夫妇,郑敏是著名的“九叶派”诗人,她用“震惊”形容初读此信的感受,说这是她读过的最罗曼蒂克的写作,完全是19世纪西欧小说的笔法。
童寯是良师。1931年他临危受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3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倾囊相授帮助学生逃难,又号召上海建筑业同仁为这批流亡学生义务补课两年,梁思成称他是“国破家亡之际的一线曙光”。
童寯是挚友。他与杨廷宝两度同学,长期共事,一生缓急可共生死相托,从无“文人相轻”的芥蒂。在童寯心目中,“(我和杨廷宝)在学术、技术、艺术各问题上,没有争论过,不是由于客气或虚心,而是由于看法一致。研究室内在处理问题上,只要是他说过的,我就不重复,完全同意”。1982年童寯因癌症复发前往北京治疗,不想却接到杨廷宝去世的讣告,他挣扎着在病榻上写下悼文。回南京后,他不顾沉疴在身,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童林夙教授骑三轮车看望杨夫人陈法青。
而童寯的精神底色,是名士。从世俗角度看,中国现代“建筑四杰”(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中,童寯大概是“名头”最小的一位,既无院士头衔,更无一官半职,这多少给他的现实生活带来一些困窘。不过在童先生自己,这是主动选择,是他出世价值观的体现。梁思成说过,童寯“在学问上和行政上的能力,都比我高出十倍”,却一辈子“逃名鄙利”。1949年后,童寯也曾多次收到“出山”的邀请,从大学院长到建设厅长、政协委员,却一概回绝。他的孙子童文清楚地记得,祖父的桌上曾放着学部委员(院士)的评审表格,不过只字未填。终其一生,这个“白身”教授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心里却有整个家国。晚年他集毕生学养写成英文著作《东南园墅》,小叩而发大鸣,起因是他接待来访的欧洲代表团,对方竟认为中国园林艺术源自日本。老先生坚持用英文写作,就是要在更多的海外读者中消除这种本末倒置的影响。
1983年初,童寯先生在北京拍了最后一张照片,面无表情,静默深沉,像老农,也像高僧,仿佛洞穿一切。张琴说,“隔着岁月,一些人和事会越来越清晰,而另一些会越来越混沌”,而她记录童寯,“也许可以让人在历史的迷雾中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