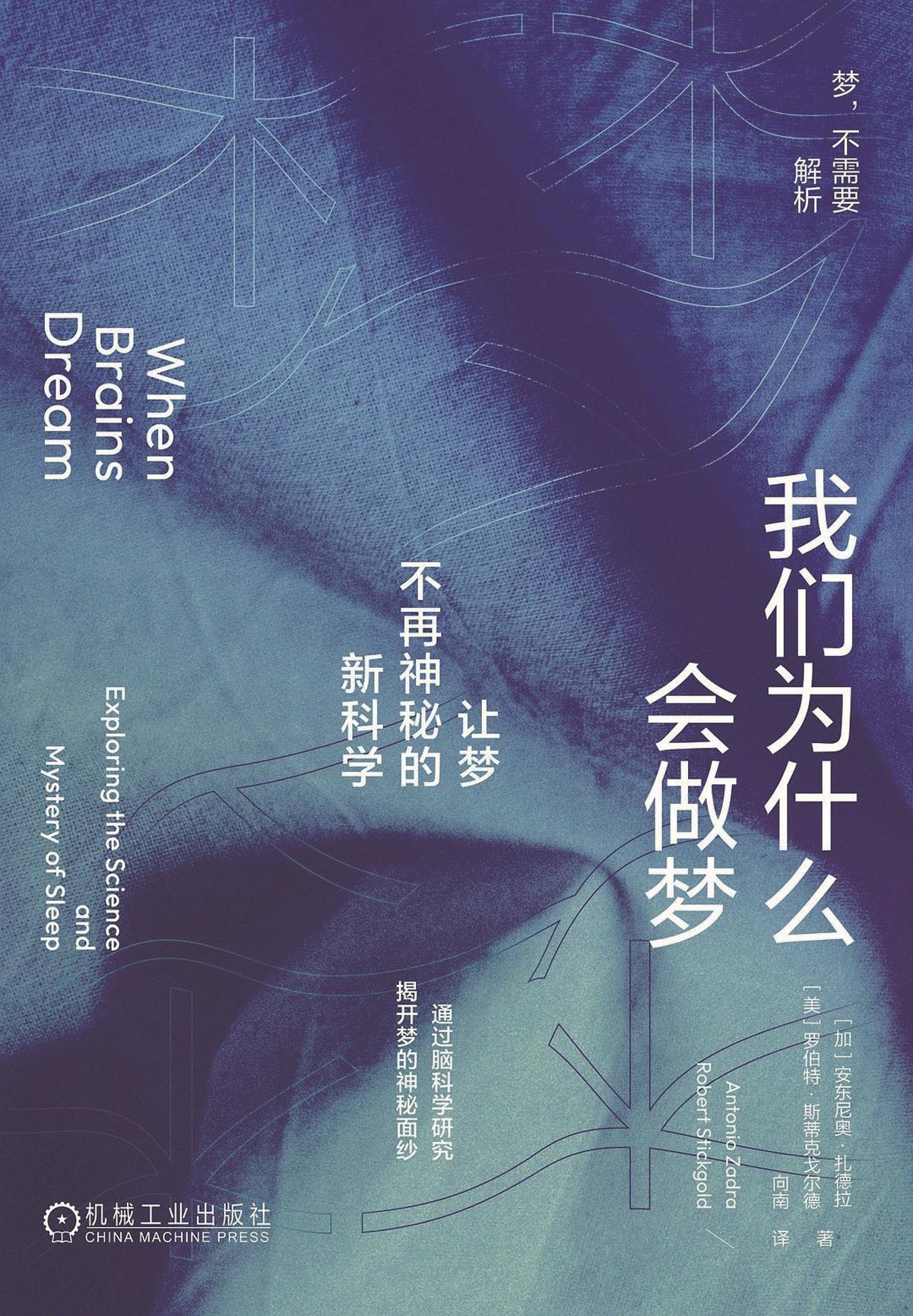□思郁
我做过很多奇怪的梦——这句话就挺奇怪的,大部分的梦其实都挺奇怪的,违背常识,奇幻恐怖,鬼魅出没。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电影是造梦的艺术,反过来其实也是成立的,梦就是各种类型的电影。恐怖片、科幻片、悬疑片、剧情片,有的梦甚至像一出电视剧,只不过大部分的梦境都是无头无尾,不像电影那样有个圆满幸福的结局。梦是无解的,反而我们对探索梦境有着无尽的好奇心。
比如,我们会说,我今晚做了一个梦,或者做了两个梦,或者说,我们今晚没做梦。但是根据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只要睡觉就会做梦,平均下来八小时睡眠有六小时都在做梦,甚至整晚都在做梦,但是如果你的睡眠质量好,能迅速入睡,整夜酣睡就不大可能回忆起自己的梦,充其量早晨醒来就会记得一个梦的模糊的场景。更科学的统计表明,一个成年人平均下来每月都只能回忆起大约4到6个梦。
有两位心理学家,也是著名的睡眠医学教授安东尼奥·扎德拉和罗伯特·斯蒂克戈尔德,为了研究梦境的产生,专门提出了一个新的梦功能模型,简称为NEXTUP,意思是“对可能性理解的网络式探究”。根据这个模型,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的研究,最后提出“做梦是一种独特的睡眠依赖性记忆演化形式,通过发现和加强以前未曾探索过的弱关联,从现有的记忆中提取新知识”。这个定义有点绕,简单说就是,睡眠做梦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大脑创作素材就是利用我们白天经历的信息,以及从记忆深处挖掘出有关联的记忆片段,进行加工和创作。他们最终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本书叫《我们为什么会做梦》。
这本书没有什么枯燥复杂的学理性探讨,两位研究者不但整理了研究梦的历史上的很多先驱者,还有对我们日常对梦的理解和误解的答疑解惑,非常有趣实用。比如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提出过梦的很多经典理论,比如梦是内心潜意识的表露,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实现等等,但其实这些理论并非他的原创,有很多更早的研究者都提出过,弗洛伊德“借用”了其他人的研究,化为己用,好像他才是原创者,这很显然是不公平的。
当然,这本书更多的是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展示,有用的东西很多,比如梦之所以有时候难以辨认,就是因为它会探索脑在清醒时通常不会考虑的关联,那些被遗忘或者扭曲的片段会出现在梦里,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们会寻找并在发现后加强新奇的、有创意的和有洞察力的关联,而脑计算出这些关联有可能在未来使用”。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好像生活中的某个场景似乎在梦中出现过,但是又不敢确认。现在你不用怀疑,它确实在梦中出现过,你忘记了而已。
根据两位学者的研究,失眠的时候,脑中一幕幕的场景快速闪现,停不下来。答案非常简单,这是因为“脑正在利用睡眠开始的时间来标记当前的关注点,也就是未完成的过程,以便在睡眠期间进行加工”。
每个人每晚都会做梦,而做梦也需要对一天接受的信息进行筛选、加工、标记,选择梦中使用的材料,形成一个梦境的叙事,也就是做梦的过程。但是由于现代人一天的时间都被塞满了,长期处在一种焦虑、压力和担忧的过程中,我们白天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会让大脑对一天的信息进行标记,但是如果你忙碌得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尤其是现在忙了一天之后,晚上睡觉前都想刷个手机,看个电影,听个音乐,这就意味着睡觉前唯一让大脑进行信息标记的时间又被剥夺了,如果这些白天的信息无法标记,也就意味着做梦做不成了。于是大脑只能剥夺你一部分睡眠的时间,紧急加班加点,进行标记,这就是失眠的解释。换句话说,你白天公司加班也就算了,晚上睡觉前大脑还得加班标记,它比你的身体还惨。也许想要好好睡觉,就别玩手机。
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我感兴趣的小问题,解答了非常多的疑惑。小猫小狗会做梦吗?快速眼动与做梦什么关系?人做噩梦是怎么回事?基本上,对梦的理解都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支撑。最关键的是,读一本关于做梦的书,让我的睡眠质量更好了。
■好书试读
尹芒的丈夫孙澍是罗克这辈子所遇见的品质最优秀的穷学生。别看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却娶了位秀色可餐的新娘。此君的墨水一直灌到了嗓子眼,稍稍一张嘴,冒出来的全是金玉良言。对待世间万物他有着一种独特的连缀法——尼采、尼克松、尼古拉二世、尼日利亚、尼尼微、尼桑警车——使他的学识通过如簧之舌得以体现。听他说话着实是一种享受,那忽高忽低、跌宕起伏的舞台腔,既可以使人联想到疯人院老大不高兴的门卫,也可以令人想起吱吱叫唤的发情的骡子。他的体型和容貌是一种合成体,它的配方是:韶华已逝的诗人,足球队备受冷遇的替补队员,怀才不遇的暴徒和喋喋不休的能工巧匠。概而言之,是当今世界极难寻觅的精英人物。据他本人透露,尹芒与他相遇之时,正是他一生中最艰难最痛苦最危急的时刻(尹芒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时刻说来就来,完全是家常便饭)。自杀的念头自头到脚制服了他。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拉扎勒斯女士》一诗风行一时,各种不同的译本在各种不同的怨男忧女的手中传阅。热衷于死亡和热衷于谈论死亡成了同一件事。
——《呼吸》 孙甘露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明代江南的造园风潮中,上海最起码出现过11处令人瞩目的园林,每一处都有其标志性的艺术景观。通常,这些特色会在园林的名字中被点出来,例如梅花源和桃园。但即便是那些名字不具有明显描述性的园林,其装点、格局也是围绕着极具审美性的事物或景观展开的。豫园是唯一现存的晚明园林,以各种各样的奇峰怪石为特色;南园内有一条清溪暗通浦江,当江水随着潮汐涨落时,园内便能听到隐隐涛声;半泾园内则花树成林,满园飘香。由此观之,明中期的不少上海园林都符合柯律格研究苏州园林时所描述的那种“审美功能与生产功能脱离”的范式。至于后来培育出令上海声名大振的水蜜桃的露香园,其早期也是本着这种审美至上的指导思想建成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露香园逐渐背离了这个宗旨。——《饮食的怀旧》[美] 马克·斯维斯洛克 著 门泊舟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