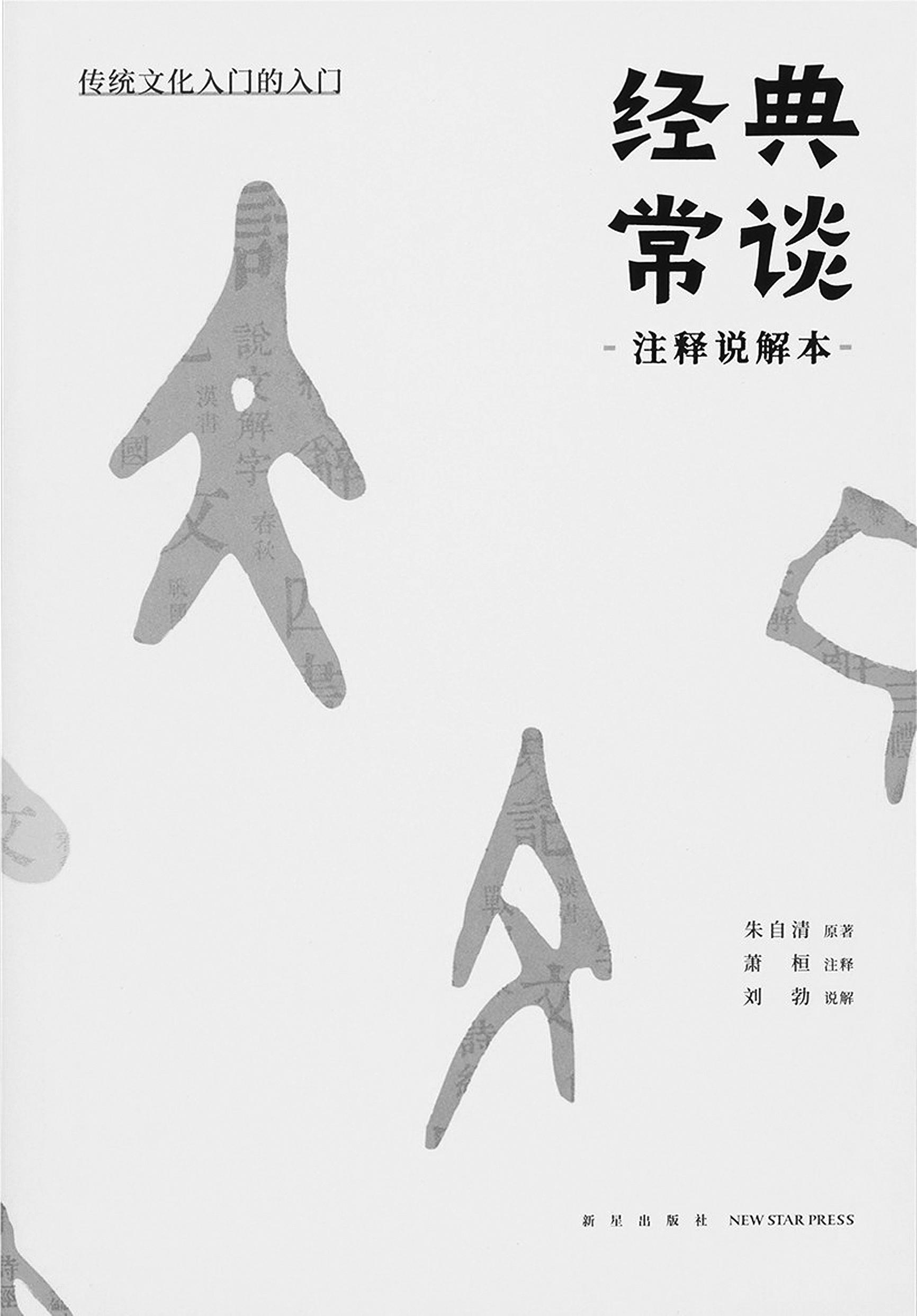□陆远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曾对他身处的时代充满焦虑,因为“过去的遗产被认为是讨厌的累赘,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不过希尔斯坚信这种肤浅的社会潮流终究会得到纠正,在著作《论传统》中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尽管充满了变化,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几乎同时,中国教育家叶圣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历史不能割断,文化遗产跟当今各条战线上的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牵连,所以谁都一样,能够跟经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叶先生的这番话,是为了表彰一位亡友在传承与普及文化经典方面作出贡献:朱自清先生与他撰写的《经典常谈》。
《经典常谈》分十三篇,概括性地介绍了中国传统典籍“经史子集”各部代表性作品,是朱先生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揭橥作品背后的人文意涵,数十年来滋养了几代中国读书人,去年又入选部编初中语文教材推荐必读书目,老树新花,再一次受到读书界和教育界瞩目。如果把《经典常谈》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中解读,就会发现,品读这本薄薄的小书,其实更有几番深意值得发掘。
如何对待传统经典,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聚讼纷纭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周围的“新派”知识人,擎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大多对传统文化秉持否定态度。批评态度激烈者如鲁迅先生,直到1925年还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钱玄同更是认定汉字“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朱自清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1920年加入新潮社,属于不折不扣的“新文化”阵营。在现代文学史上,他主要也是新诗和散文闻名,《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都是白话名篇。不过朱先生内心的自我期许,与他的外在形象,多少还是有些差异,他曾说过,“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在清华教书20余年,他所开课程也大多围绕中国古典文学展开。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化的世界,是许多像朱自清这样“一新一旧”的一代知识人毕生志业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五四”新人到了三四十年代要倡导“重读经典”了。
朱先生倡导常谈经典,并不仅仅出于提升国民语文素养的考量,他再三呼吁“古典的训练”是“中等以上有相当教育的国民”应尽的义务,不是为了“教学生练习文言的写作”,而是试图通过古书古文的阅读,“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经典常谈》的写作时间是1938年至1942年,正处于抗战最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样的艰难时世,不失去对本民族的信心是“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当有的精神底线。用作家刘勃的话说,国难当头,朱自清花大力气写一本“不在实用”的著作,“正包含着一种凝聚国族信念、一致抵御外侮的深切用心”。烽火连三月之际,读经典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对本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认同。“价值认同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但是有了价值认同,群体内部才能有效协作,才不至于为一点眼前的利害,争得头破血流或者拆家散伙。这是经典训练的‘无用之大勇’。”
经典固然重要,但经典教育却并非易事,在这方面,朱自清先生以博采众长的学术视野,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和切实浅明的语言风格,使《经典常谈》成为传统文化基本训练当之无愧的典范。他想以这本小书为媒介,将自己青年时代接受经典教育的成功经验“金针度人”,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代读者。平易近人的“常谈”蕴含着他对教育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叶圣陶说,“现在正在编撰百科全书,朱先生这本书里的十三篇可以作为十三个条目收到百科全书里去”,吴小如也说这本书里朱先生最得心应手的那些篇章(比如谈“诗”和“文”的两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学史,比那些粗制滥造的整部文学史还好”。
《经典常谈》首次出版是在1942年,至今已超过80年。朱先生自己也说,“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80多年来信息更迭日新月异,读者的知识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当年的“文化常识”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很陌生,不少当年公认的学术观点今天也在被重新审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身已成为“经典”的《经典常谈》,也有了被“常谈”的必要。学者萧桓提纲挈领,对书中的知识点进行了详细注释,作家刘勃阐幽发微,对每一篇章进行了适度解说,与朱先生的文章合璧为这部注释说解本《经典常谈》,读一部书等于三次浸润经典,真是我辈读者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