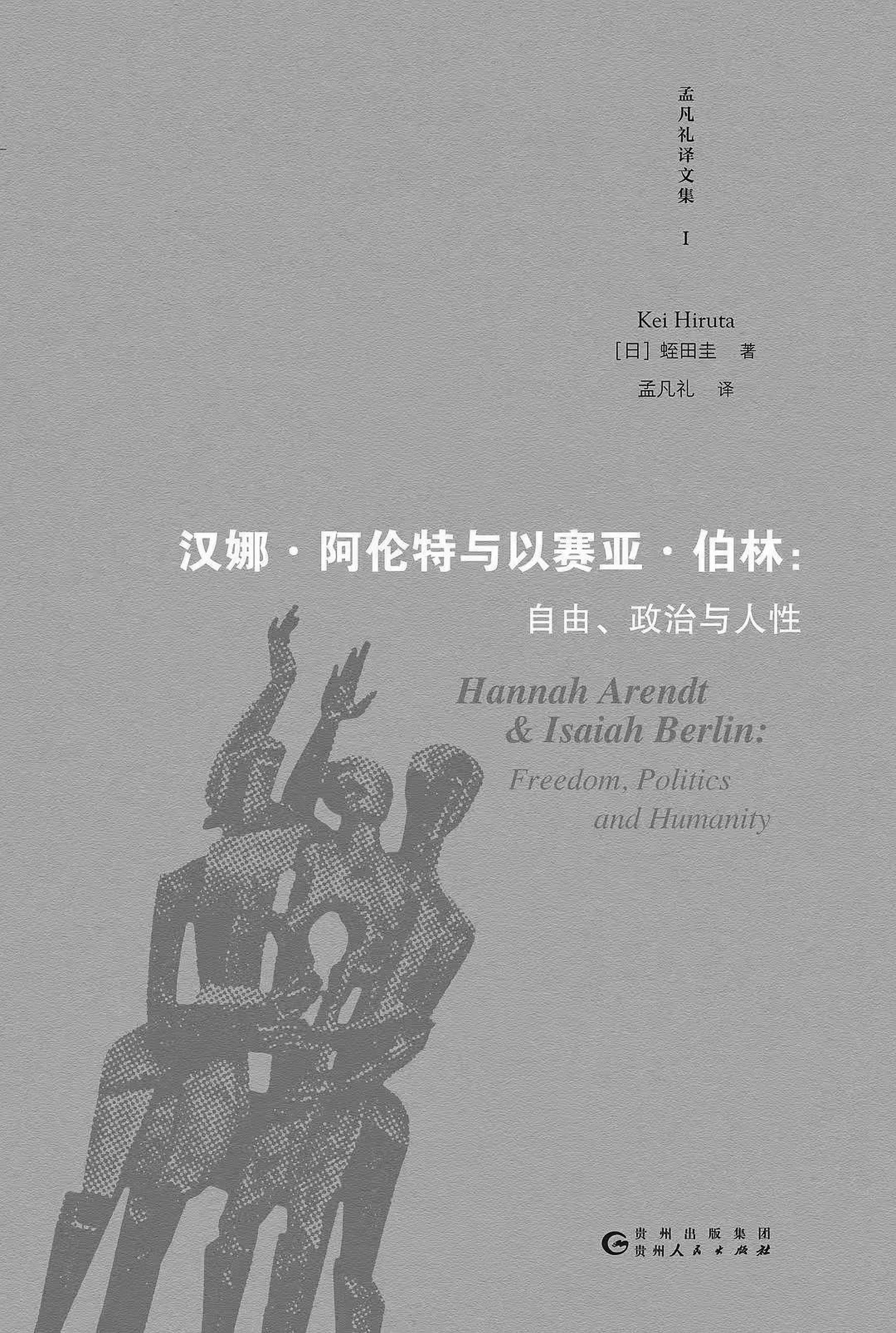□思郁
最早得知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非常不喜欢美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时候,我还是挺意外的。在我的阅读谱系里,这两位思想家的影响力不分伯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都滋养了我不同成长时期的思想启蒙。只不过,我早年更喜欢伯林,对他的消极自由和多元价值的理论非常推崇,现在我喜欢阿伦特更多。阿伦特是个思想的宝矿,跟当下有着神秘的关联,尤其是她后期关于思考、责任与判断的文章,都可以适用当下这个甚嚣尘上的语境。而伯林的思想慢慢隐匿不显了。
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非常大。在《伯林谈话录》中,他还是比较克制地表达了对阿伦特著作的批评,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关于俄国的部分全都是错的,《人的境况》是一堆自由的形而上学的联想,《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荒谬的,这还算是学术批评。此后随着阿伦特的辞世,这种敌意并未消失,反而愈演愈烈,他甚至形容阿伦特“对我来说一个真正的眼中钉——无论是活着,还是在她死后”,还说“她真的是我厌恶的东西”。
但是从事实上看,伯林对阿伦特的厌恶毫无缘由,他们的一生没打过几次照面,而且基本也没有任何深入的交流。更值得玩味的是,对伯林非常情绪化的言辞,阿伦特大概也有所耳闻,但基本没有什么回应,她对他的评价就是,伯林甚至都不算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而且从他们一生留下书籍看,阿伦特几乎不读伯林的书籍,伯林虽然讨厌阿伦特,但是却一直都在读她的书,然后读完就狠狠批判。所以,这种敌意和厌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日本学者蛭田圭据此写了一本书叫《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这大概是今年最好看的一本学术八卦书了。从伯林对阿伦特的厌恶入手,分析了他们不同的成长和思想形塑的生涯,分析精准,学术的评价也到位,关键写作也没有学究气,非常好看,可以作为了解他们两人思想的入门书。中文的翻译也很加分。是2024年学术书的一本翻译佳作了。
其实从他们互相的经历看,两人的相似之处更多,比如基本是同龄人,都是犹太人,阿伦特出生在1906年,父母都是完全归化的中产阶级;伯林出生于1909年一个富裕的说俄语的犹太家庭。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后,全家移居到英国伦敦,伯林进入到牛津大学,二十二岁就成为全灵学院的研究员。他的学术生涯非常稳定,基本没什么波折,二战还作为英国的情报分析专家参与到决策层,认识很多大人物。战争结束后,继续回到大学教书写作。
阿伦特前半生的生活比他惨多了,纳粹上台后,全家开始流亡到法国,差点被送入集中营,而后辗转多难,1941年才到了美国,重新学英语,找工作,努力进入学术圈,逐渐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总之,这两人之间,看起来相似性有,但是总归学术道路是不同的。
蛭田圭在书中着重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比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术传统,阿伦特师从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伯林更信奉英国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传统互相看不顺眼。还有他们对自由的认知有差异。后期最大的争议点就是阿伦特在《纽约客》上连载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后,伯林对阿伦特的批评。
在蛭田圭的书中提到了他们两人之间互相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来自跟阿伦特与伯林同时交往,也曾帮助他们牵线搭桥,想让他们互相理解的阿瑟·小施莱辛格。小施莱辛格认为,对伯林来说,阿伦特太严肃,太自命清高,太黑格尔化了;而对阿伦特来说,伯林太轻浮,又不够严肃。所以他们短暂地会面之后也留下了不佳的印象。这次见面是不是意味着加深了各自的偏见呢?那到底为什么伯林始终对阿伦特充满这么大的恶意呢?这里面是否存在一种性别主义的偏见?阿伦特的好斗属性,或者在一个男性为主的世界里,偏偏表现出来更多的男性气概,这种故意为之的傲慢,是否也激发了伯林更多的反感?这些我们都无法得知。
蛭田圭在书的结论部分中,也并未特意将两人强行和解,他只是分别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仰,毕竟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性格不同,学术志趣也相异,但都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扬名寰宇。他尊敬他们都践行了苏格拉底的名言,真正的哲学根植于激情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