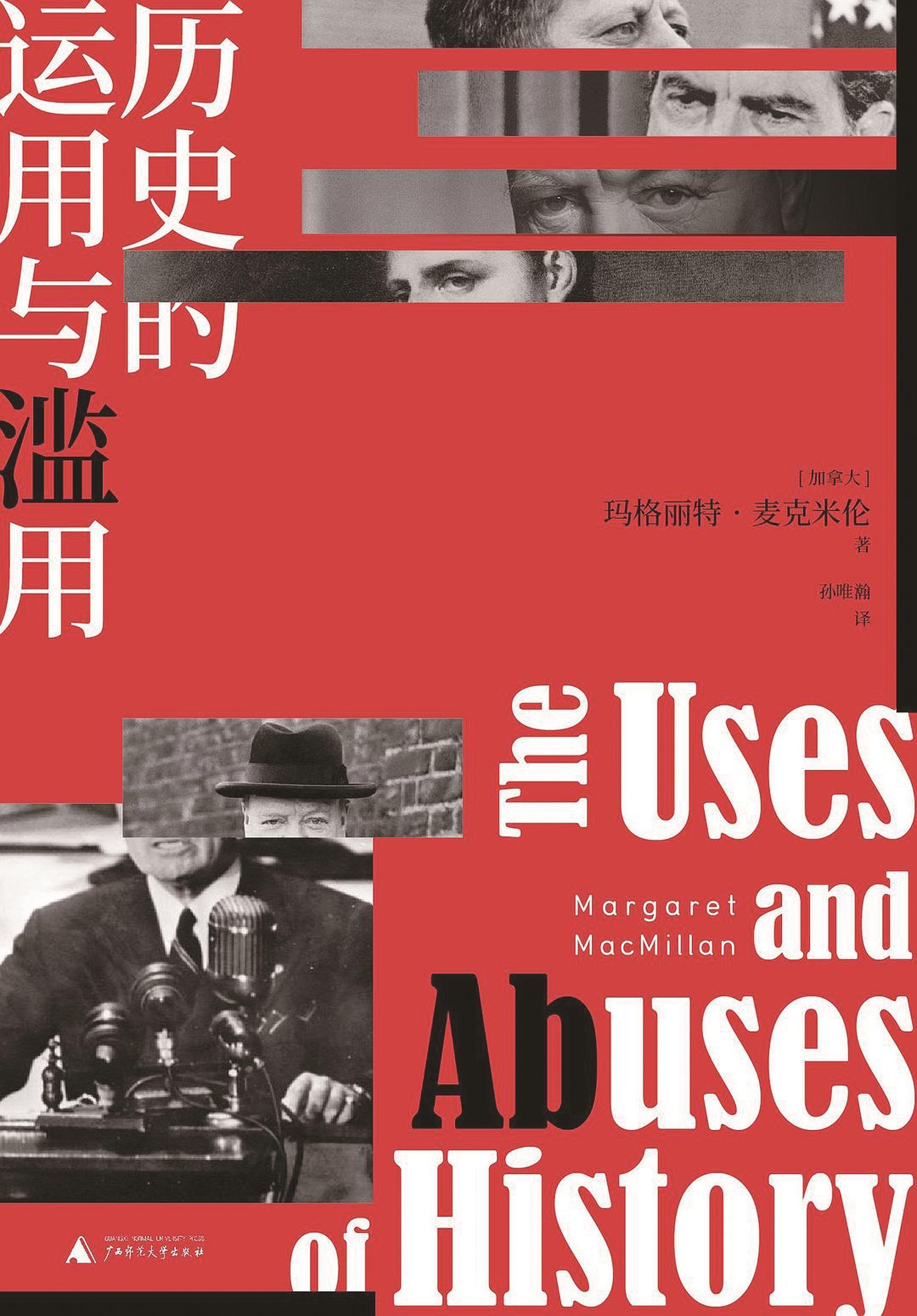□陆远
这些年,各种题材的历史书写常常成为坊间出版热点,然而以研究历史为志业的作者们,依旧免不了直面这样的尴尬——在不少人心目中,历史作品当然能让人增长知识或者带来乐趣,但是其价值大约也仅限于此,因为再英明伟大的人物,再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旦成为过去,就很难对当下产生什么“实际的”用处。不过,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显然并不这么看,在著作《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麦克米伦试图全面阐释“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她反复申明,历史与我们很近,对当下的日常生活而言,它发挥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的效能,既为我们每个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以凝聚的精神纽带。唯其如此,我们更要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叙事保持警惕,因为稍不留神,也许就会落入常见的思维陷阱,甚至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麦克米伦家族的许多成员是那些影响人类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她的曾祖父劳合·乔治在一战期间先后担任英国陆军大臣和首相,是巴黎和会代表,也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人;她的祖辈和父辈,分别深度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特殊的出身背景不仅为麦克米伦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一战史专家提供了独特的条件,也赋予她从家族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双重视角考察20世纪战争史的能力。麦克米伦时刻不忘从“当下”理解历史,在她看来,一战是对人类文明永难磨灭的嘲讽,即便时光穿越百年,依旧能让我们借以反观自身的缺陷,对人类理性的限度有所警醒。
正是从对战争与暴力史的反思出发,麦克米伦从正反两个方面解读历史中蕴含着的巨大力量。
一方面,麦克米伦特别强调“历史的效能”。所谓历史的效能,指的是历史对当下的价值与作用。它可以成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动员手段,也可以成为宣誓合法性的途径;它为弱者和边缘群体提供抵抗的武器,也形塑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如暴风雨中的航标灯一样为我们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揭示善恶与美丑;它建构了我们的身份认同,让我们拥有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进而形成稳定的民族文化传统,抚慰现代世界或者空虚或者焦躁的心灵——麦克米伦说,“在我们中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来世的时候,所属群体的长存给予我们一种永恒不朽的承诺”,我想,写下这句话时,教授一定如菩萨低眉,温情脉脉。
另一方面,让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也许是作者金刚怒目之下的冷峻思考,她提醒我们,人类往往“只会选择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欢的历史叙述”,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动下,大量历史叙事在“记忆”和“遗忘”的反复拉扯之间变得暧昧模糊以至面目全非。二战时期成立的维希傀儡政权是法国人无法抹去的屈辱记忆,右翼分子将其美化为法国高层的“忍辱负重”之举,更将其附庸为对犹太人的保护;西班牙甚至出台了名为“遗忘协议”的文件,让国家与民众自行删除关于法西斯分子弗朗哥政权的历史记忆;更加无耻的行径在于通过霸凌历史而控制现实,比如希特勒对《凡尔赛和约》与“一战”事实的扭曲与篡改不仅没有终止战争,反而造成更大的灾难。
麦克米伦通过一个例子告诫人们,务必审慎地处理历史记忆,即便出于温情和敬意。2005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为法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举行国葬,他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先贤祠或者荣军院。此举却受到当时健在的一战老兵拉扎尔·蒙蒂塞利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相较于那场让无数人殒命的战争,国家不应该只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因为这对前面逝去的战友们来说,是一种侮辱,也不会让最后一个逝者感到任何荣誉”。很显然,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更多是出于活着的人们意愿的”国葬设想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历史亲历者之间,有着大相径庭的情感体验,这既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更彰显出历史与现实强大的张力。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关系既是政治家的工作,也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由此看来,历史学家不仅承担着求真的责任,更有着深思的品性,让“真实”超越实证与考掘的要求,向伦理与价值的层面挺进,让历史学科成为与个体的精神成长与人类整体的幸福生存紧密相关的生命之学。这样的历史学恰恰起步于我们历史观的转变与矫正,并进而成为一种邀约,请我们回望过去看清自身,并由此迈向心性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