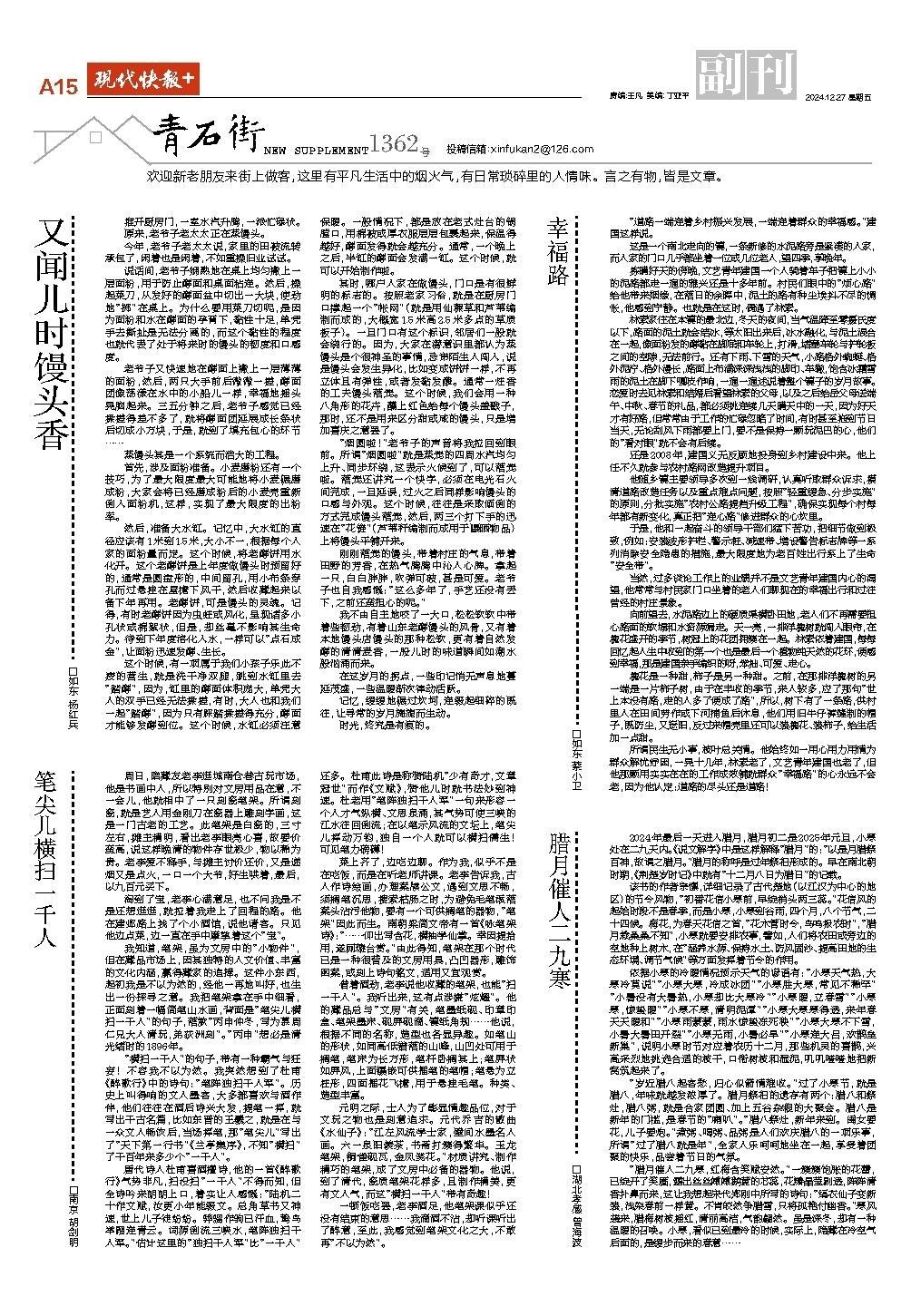□如东 杨红兵
推开厨房门,一室水汽升腾,一派忙碌状。
原来,老爷子老太太正在蒸馒头。
今年,老爷子老太太说,家里的田被流转承包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重操旧业试试。
说话间,老爷子娴熟地在桌上均匀撒上一层面粉,用于防止酵面和桌面粘连。然后,操起菜刀,从发好的酵面盆中切出一大块,使劲地“掷”在桌上。为什么要用菜刀切呢,是因为面粉和水在酵面的孕育下,黏性十足,单凭手去撕扯是无法分离的,而这个黏性的程度也就代表了处于将来时的馒头的韧度和口感度。
老爷子又快速地在酵面上撒上一层薄薄的面粉,然后,两只大手前后微微一搓,酵面团像荡漾在水中的小船儿一样,幸福地摇头晃脑起来。三五分钟之后,老爷子感觉已经揉搓得差不多了,就将酵面团延展成长条状后切成小方块,于是,就到了填充包心的环节……
蒸馒头其是一个系统而浩大的工程。
首先,涉及面粉准备。小麦磨粉还有一个技巧,为了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将小麦碾磨成粉,大家会将已经磨成粉后的小麦壳重新倒入面粉机,这样,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出粉率。
然后,准备大水缸。记忆中,大水缸的直径应该有1米到1.5米,大小不一,根据每个人家的面粉量而定。这个时候,将老酵饼用水化开。这个老酵饼是上年度做馒头时预留好的,通常是圆盘形的,中间留孔,用小布条穿孔而过悬挂在屋檐下风干,然后收藏起来以备下年再用。老酵饼,可是馒头的灵魂。记得,有时老酵饼因为虫蛀或风化,呈现诸多小孔状或棉絮状,但是,却丝毫不影响其生命力。待到下年度溶化入水,一样可以“点石成金”,让面粉迅速发酵、生长。
这个时候,有一项属于我们小孩子乐此不疲的营生,就是洗干净双腿,跳到水缸里去“踏酵”,因为,缸里的酵面体积庞大,单凭大人的双手已经无法揉搓,有时,大人也和我们一起“踏酵”,因为只有踩踏揉搓得充分,酵面才能够发酵到位。这个时候,水缸必须注意保暖。一般情况下,都是放在老式灶台的锅膛口,用棉被或厚衣服层层包裹起来,保温得越好,酵面发得就会越充分。通常,一个晚上之后,半缸的酵面会发满一缸。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制作啦。
其时,哪户人家在做馒头,门口是有很鲜明的标志的。按照老家习俗,就是在厨房门口撑起一个“帐网”(就是用仙稞草和芦苇编制而成的,大概宽1.5米高2.5米多点的草质板子)。一旦门口有这个标识,邻居们一般就会绕行的。因为,大家在潜意识里都认为蒸馒头是个很神圣的事情,忌讳陌生人闯入,说是馒头会发生异化,比如变成饼饼一样,不再立体且有弹性,或者发黏发酸。通常一炷香的工夫馒头落笼。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八角形的花卉,蘸上红色给每个馒头盖戳子,那时,还不是用来区分甜或咸的馒头,只是增加喜庆之意罢了。
“烟圆啦!”老爷子的声音将我拉回到眼前。所谓“烟圆啦”就是蒸笼的四周水汽均匀上升、同步环绕,这表示火候到了,可以落笼啦。落笼还讲究一个快字,必须在电光石火间完成,一旦延误,过火之后同样影响馒头的口感与外观。这个时候,往往是采取倾倒的方式完成馒头落笼,然后,两三个打下手的迅速在“花链”(芦苇秆编制而成用于曝晒物品)上将馒头平铺开来。
刚刚落笼的馒头,带着村庄的气息,带着田野的芳香,在热气腾腾中沁人心脾。拿起一只,白白胖胖,吹弹可破,甚是可爱。老爷子也自我感慨:“这么多年了,手艺还没有丢下,之前还蛮担心的呢。”
我不由自主地咬了一大口,松松软软中带着些韧劲,有着山东老酵馒头的风骨,又有着本地馒头店馒头的那种松软,更有着自然发酵的清清麦香,一股儿时的味道瞬间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在这岁月的拐点,一些印记悄无声息地蔓延茂盛,一些温暖渐次律动活跃。
记忆,缓缓地碾过坎坷,连缀起细碎的既往,让寻常的岁月旖旎而生动。
时光,终究是有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