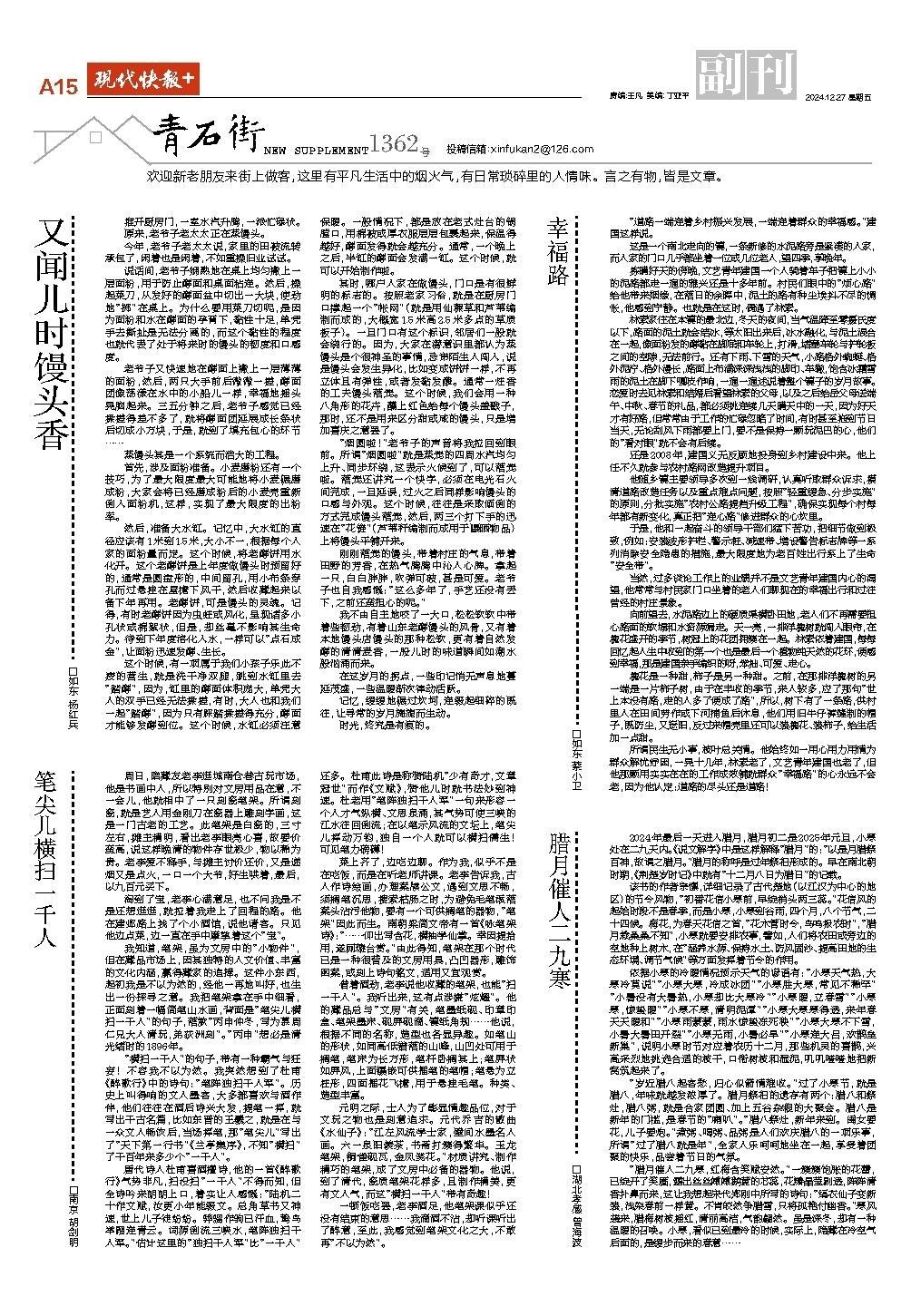□南京 胡剑明
周日,陪藏友老李逛城南仓巷古玩市场,他是书画中人,所以特别对文房用品在意,不一会儿,他就相中了一只刻瓷笔架。所谓刻瓷,就是艺人用金刚刀在瓷器上雕刻字画,这是一门古老的工艺。此笔架是白瓷的,三寸左右,摊主精明,看出老李眼亮心喜,故要价蛮高,说这样晚清的物件存世极少,物以稀为贵。老李爱不释手,与摊主讨价还价,又是递烟又是点火,一口一个大爷,好生哄着,最后,以九百元买下。
淘到了宝,老李心满意足,也不问我是不是还想逛逛,就拉着我走上了回程的路。他在建邺路上找了个小酒馆,说他请客。只见他边点菜,边一直在手中摩挲着这个“宝”。
我知道,笔架,虽为文房中的“小物件”,但在藏品市场上,因其独特的人文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赢得藏家的追捧。这件小东西,起初我是不以为然的,经他一再地叫好,也生出一份探寻之意。我把笔架拿在手中细看,正面刻着一幅简笔山水画,背面是“笔尖儿横扫一千人”的句子,落款“丙申仲冬,写为慕周仁兄大人清玩,弟荻洲刻”。“丙申”想必是清光绪时的1896年。
“横扫一千人”的句子,带有一种霸气与狂妄!不容我不以为然。我突然想到了杜甫《醉歌行》中的诗句:“笔阵独扫千人军”。历史上叫得响的文人墨客,大多都喜欢与酒作伴,他们往往在酒后诗兴大发,提笔一挥,就写出千古名篇,比如东晋的王羲之,就是在与一众文人畅饮后,当场挥笔,那“笔尖儿”写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不知“横扫”了千百年来多少个“一千人”。
唐代诗人杜甫喜酒擅诗,他的一首《醉歌行》气势非凡,扫没扫“一千人”不得而知,但全诗吟来朗朗上口,着实让人感慨:“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总角草书又神速,世上儿子徒纷纷。骅骝作驹已汗血,鸷鸟举翮连青云。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估计这里的“独扫千人军”比“一千人”还多。杜甫此诗是称赞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而作《文赋》,赞他儿时就书法妙到神速。杜老用“笔阵独扫千人军”一句来形容一个人才气纵横、文思泉涌,其气势可使三峡的江水往回倒流;在以笔示风流的文坛上,笔尖儿挥动万钧,独自一个人就可以横扫儒生!可见笔力磅礴!
菜上齐了,边吃边聊。作为我,似乎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听老师讲课。老李告诉我,古人作诗绘画,办理案牍公文,遇到文思不畅,须搁笔沉思,搜索枯肠之时,为避免毛笔滚落案头沾污他物,要有一个可供搁笔的器物,“笔架”因此而生。南朝梁简文帝有一首《咏笔架诗》:“……仰出写含花,横抽学仙掌。幸因提拾用,遂厕璇台赏。”由此得知,笔架在那个时代已是一种很普及的文房用具,凸凹器形,雕饰图案,或刻上诗句铭文,适用又宜观赏。
借着酒劲,老李说他收藏的笔架,也能“扫一千人”。我听出来,这有点涉嫌“炫耀”。他的藏品总与“文房”有关,笔墨纸砚、印章印盒、笔架墨床、砚屏砚滴、镇纸角规……他说,根据不同的名称,造型也各显异趣。如笔山的形状,如同高低错落的山峰,山凹处可用于搁笔,笔床为长方形,笔杆卧搁其上;笔屏状如屏风,上面镶嵌可供插笔的笔帽;笔悬为立柱形,四面插花飞檐,用于悬挂毛笔。种类、造型丰富。
元明之际,士人为了彰显情趣品位,对于文玩之物也是刻意追求。元代乔吉的散曲《水仙子》:“江左风流学士家,壁间水墨名人画。六一泉阳羡茶,书斋打簇得繁华。玉龙笔架,铜雀砚瓦,金凤笺花。”材质讲究、制作精巧的笔架,成了文房中必备的器物。他说,到了清代,瓷质笔架花样多,且制作精美,更有文人气,而这“横扫一千人”带有奇趣!
一顿饭吃罢,老李酒足,他笔架课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滴酒不沾,却听课听出了醉意,至此,我感觉到笔架文化之大,不敢再“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