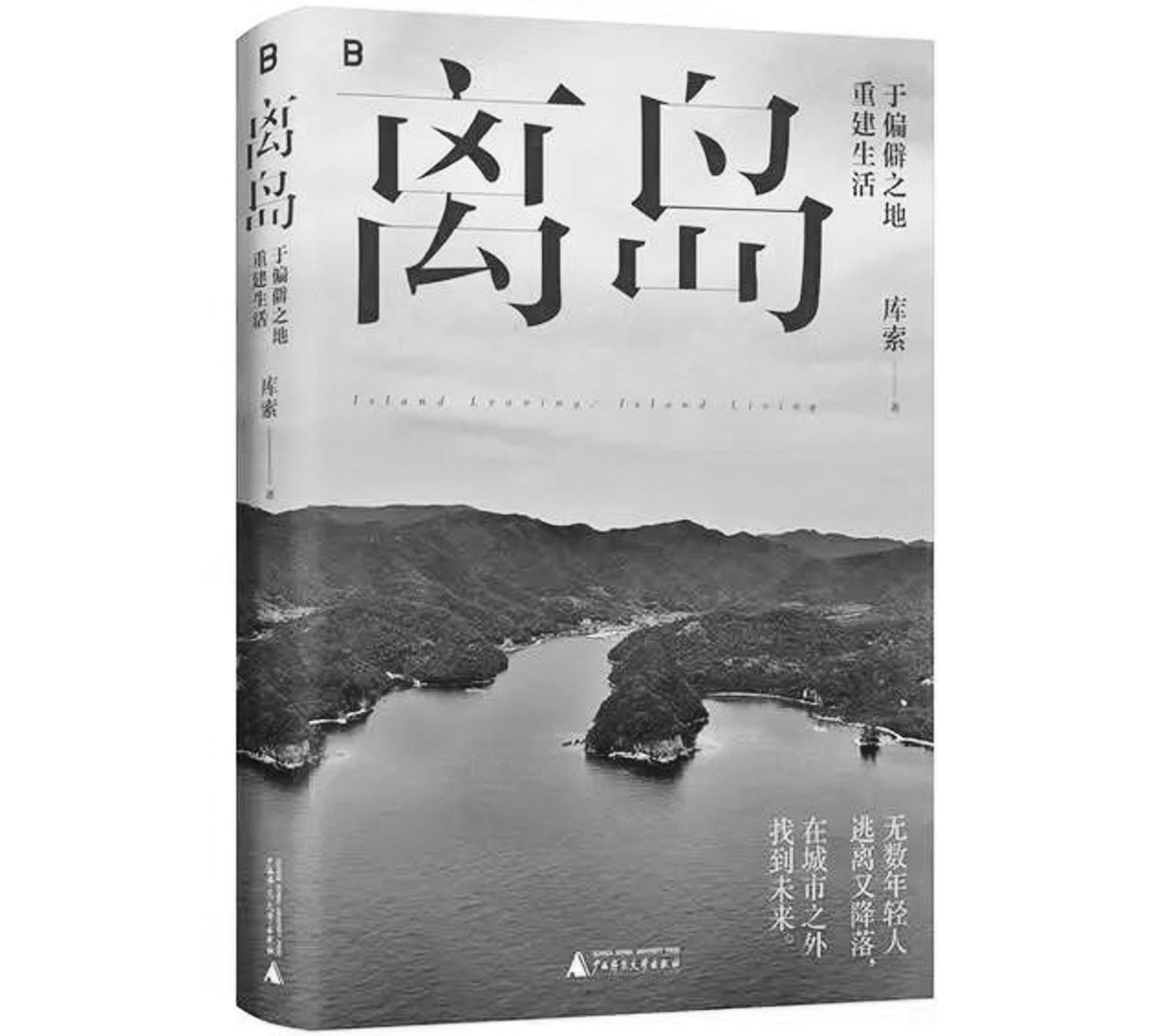□陆远
想象这样一个地方:透明的海水、松软的沙滩、美味的海鲜,以及一种缓慢悠闲、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对于大都市那些被生存压力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逃离,或者只为了喘一口气,这样的地方无疑是最理想的“远方”。十年前,旅日作家库索在旅行时,觉得自己发现了完全符合浪漫想象的“世外桃源”,在日本,它们被称作“离岛”。
所谓离岛,指的是远离本土的岛屿。在日本版图上,除了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和冲绳五个主岛外,其余岛屿都被视为“离岛”。全日本有近7000个离岛,大多地处偏僻。其中的一些历史上曾被作为贵族的流放地,见证了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们郁郁而终的后半生。不过,也正因为其在国土上的边缘性,不少小岛一度成为日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前沿:它们曾是日本遣唐使们告别故乡晋谒华夏的离岸之地,也曾是亚洲海上贸易繁盛的港口,江户海禁时期又曾作为基督徒的藏身之所。时至今日,依然有大约400座离岛常年有人居住,人口总数60万,差不多每200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离岛。而最近这些年,更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离开城市去离岛生活。
人们为什么愿意待在远离都市与现代生活的偏僻小岛?他们是主动选择背离主流成功观的“逆行者”,还是被时代车轮抛下的弃儿?离岛究竟象征着精神乌托邦,还是处处布满生活的暗礁?带着这样的疑问,库索花了3年时间在几座离岛旅行,也试图打开指向不同生活意义的窗口。
库索发现,离岛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之间游走。一方面是严峻的社会现实: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人口老龄化严重、居民收入微薄、传统文化与艺术无以为继……在上了年纪的原住居民身上,那种视野狭窄,气量褊狭的“岛民性格”显露无遗。但另一方面,在这些保守贫瘠的土地上,库索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里生活着许多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年轻人,共同的特点是“不按套路出牌”:从海外归来试图在小岛上寻找日本文化之根的高材生,专为观光客定制独特旅行路线的美国亚裔,从零开始种植葡萄的法国金牌酿酒师夫妇,世界名校毕业却拒绝高薪offer的80后爸爸,让非遗传统艺术重获新生的庶民表演者……他们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当下社会结构充满怀疑,正在尝试重建“真正想要的生活”实践。
从小在岛上长大的川本,是一个典型。二十年前,川本在岛上念小学,从课本里知道了东京、大阪这些陌生而遥远的地名。放了学,他跟爷爷去养牛——在这个偏僻的小岛上,他家和邻居们一样,世世代代都靠养牛为生。
他想去东京。
接下来的剧本人们都很熟悉:升学,考试,升学,考试,升学,面试。
终于,“川本”成为了记录在东京大企业人力资源系统里的一个名字。但他不开心。“我渐渐意识到了,企业的上班族生活恐怕不适合我。”东京比想象中还要大,大到他觉得自己如此渺小。如果说,日复一日地学习是为了来到这里的话;那么如今,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做着无意义的工作,又是为了什么呢?
终于,川本回到小岛上,靠经营咖啡店谋生,店招上写着一句话:“顺其自然”。
库索并不认为像川本这样的选择是一种“逃离”,离岛不是桃花源,它并不是都市人逃离现代生活压力的安乐窝。相反,移居离岛,其实是一种主动选择。这里就像一场大型的人类生存实验,离岛仿佛包容一切的容器,正在酝酿未来生活方式的某种可能性。
现代人对生活的追求,大抵是要“寻找更多可能性”;生活在离岛的人们恰恰相反,他们选择在更少可能性、狭窄受限的环境中生活。坐落于隐岐群岛的一家酒店会送给每个住客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岛上的一句名言:“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其中,既包含着接受和适应“没有”的态度,也包含“已经拥有一切重要的事物”的意识。在一个没有便利店、麦当劳、电影院的地方,“重要的东西”就是与自然朝夕相处的恩赐、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完全被自己想做的事填满的时间……对离岛上的人来说,这些就是人类所需要的一切。
库索说,在城市里,她遇见很多“飘在空中的人”,而在离岛上,她遇见的是“扎根于土地的人”,他们展示了一种“充满养分的人生”。在城市里,人们早已默认成为机器上的一枚齿轮,努力获取更多物质来适应生活,去离岛的人,人们从雏形和轮廓上改变生活,恰恰不是为了“躺平”,而是为了不在城市里随波逐流打发人生,为了自己定义生活而不是被生活定义。他们真的在建设一种“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生活。